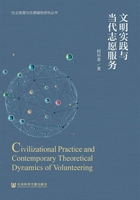
二 价值理念与社会情境:志愿精神的历史阐释
对志愿精神历史起源与流变的理解,在社会科学领域,一般可以概括为文化阐释和社会阐释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侧重追溯精神理念或者价值的历史,它通过挖掘文化传统中蕴含的志愿精神成分,追寻当代志愿精神的历史根源,为志愿精神寻找历史与文化的基因;第二种方法则侧重社会维度的解释,在认识论上强调志愿精神是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可以激发与培育志愿精神的发展,乃至形成志愿精神的独特品格。
两种方法在对象与解释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它们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前所述,志愿精神是规范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志愿服务的精神、价值和理念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性,它们的形成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思想理念,其形成与发展、传承与发扬,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与文化历史的结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志愿精神中具有普遍主义的成分,如利他主义、互助和奉献等价值内涵,但是它在地方化实践中吸收了许多情境性特点,进而塑造了一些地方化或者本土化的志愿精神。另一方面,志愿精神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国家和文化传统之间,也会在组织和社会部门之间出现。这种差异甚至会出现在志愿服务领域,不同类型、导向和目标的志愿组织,其对志愿精神的理解与实践会有所不同。从历史发展来看,志愿精神并不是一组固定的理念或者价值,它会在历史发展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表现新的形态。并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志愿精神作为一种理念在全球传播,与地方文化的相遇和互动,使得地方文化对志愿精神的吸收、消化、融合与拓展成为可能。
在美国,志愿精神与国家历史进程交织在一起。各种类型的志愿组织在历史上大量兴起,并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游历美国时,很快便发现这一与欧洲大陆不同的社会现象。他认为19世纪美国志愿组织的数量之多、目标之广,在世界中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美国的个体主义也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个体主义”(group individualism)(Olson,1964)。对于这种个体与组织化辩证结合的社会生活,加拿大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表达,即“整体的个体主义”(holist-individualism)(Taylor,1989:163)。日常生活中的组织化志愿参与,为美国民众的道德和伦理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来源,在社区建设、社会问题解决等方面,提升了民众的效能感与社会归属感,志愿精神也成为美国伦理的一部分(Ogilvie,2004:1)。
美国独特的国家和社会历史孕育和培育了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的发展,乃至它们被理解为一种美国价值和美国精神的构成要素。在论及美国志愿精神的时候,布莱恩·奥康奈尔(Brian O’Connell)认为,相比于其他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历史并不长,建国之初虽然缺少基础,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会背负沉重的历史与思想包袱,人们通过积极的合作互助,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参与者”。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志愿和社会组织为人们的社会化和共同活动提供了基础性的社会网络与空间(O’connell,1998:10)。换言之,美国的国家建设由志愿者所完成。
事实上,志愿精神蕴含在美国精神的起点之中。在17世纪早期,移民自英格兰普利茅斯出发,进入美洲大陆所缔结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1620),公约的内容和确立表现了在新环境中相互帮助与团结协作的志愿精神(潘静,2011)。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公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被当作了美国精神的起点。
毗邻美国的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情况,互助的志愿精神根植在加拿大的社会土壤与传统文化价值中。研究者认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加拿大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在地广人稀和冬季气候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本地居民与欧洲移民意识到个人的不足,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将无法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只有通过团结合作才能战胜生存困境。这种为了生存和延续的互助培养了加拿大人的志愿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邻里和普通市民的责任感与道德关怀(Lautenschlager,1992:1)。
在历史悠久与宗教文化积淀深厚的欧洲,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的兴起则呈现与美国不一样的面貌。在英国,志愿服务的历史发展与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的演进相互交织。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志愿者潮”(volunteer boom),志愿服务的兴起以对彼时英国公共服务的失望为背景(GHK,2011)。就志愿精神而言,它远比现代志愿服务制度化的历史要长久。英国的志愿精神有着深厚的宗教和慈善背景,救济贫困与帮助弱小是实践宗教理念的方式之一。在12和13世纪的时候,英格兰至少有500家针对贫困人口和病人的“志愿医院”(voluntary hospital)。[7]显然,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在英国的历史,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面貌与发展路径。
可以看到,社会情境的不同,志愿精神的历史和样态也可能存在不一样的情况。以亚洲的日本为例,学者对日本志愿服务实践的考察,认为日本缺少志愿精神的传统,自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当代,都属于一种“政府驱动”(governmental driven)的产物(Bothwell,2002:132)。事实上,对志愿服务的认知、社会认同与志愿服务参与率在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志愿精神的地方化特征与价值属性。
在中国情境下,对志愿精神的考察,需要面对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中国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其中的积极和进步要素,为当代中国志愿精神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亦构成了中国志愿精神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密切关联,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情境为志愿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制度支持。同时,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志愿精神的积极内涵相契合。
首先,中国学者对志愿精神的考察,在概括普遍特征的定义中,会突出志愿精神的实践属性与行动属性。丁元竹从实践性的角度来理解志愿精神,认为它是一种不计报酬自愿参与推动社会进步和社区发展的精神。并且,志愿精神的精髓在于集体化与个人化的统一。在集体的维度,它具有奉献社会的公益精神;在个体的维度,它又是个人意愿和偏好的选择。因而,志愿精神可以概括为“它是以私人化的方式参与社会化工作的一种信条,一种价值观的实践”(丁元竹,2005:302)。佘双好等学者概括了“志愿精神”的基本特征,作为志愿服务中的价值引领和价值支撑,志愿精神的四个特征包括:实践性、无偿性、公益性和组织性(佘双好,2013:49-50)。
此外,还可以从思想史和文化角度对中国志愿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考察。中国古代慈善观念盛行,先秦各家思想中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儒家思想的“仁者爱人”、墨家思想的“兼爱非攻”,以及“兼济天下”和古代的宗教慈善思想,奠定了中国志愿服务的思想基础(巍娜,2018:90-92)。概而言之,“仁”、“义”、“信”、“善”等传统思想是中国志愿精神传统观念因素与文化基因(丁元竹、江汛清、谭建光,2007:9)。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志愿服务精神并不是僵化与刻板的概念,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积极要素完善自身。从发展历程看,颜睿(2013)概括了中国志愿精神的文化渊源与现代价值,认为志愿精神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同时孕育在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土壤中,并在现代文化中汲取精华开花结果。
历史与文化视角的阐释与前一种方法相比,更能突出志愿服务精神和思想中的中国意涵与特色。另一方面,中国的志愿精神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史传统,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密切关联。志愿者助人为乐、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和乐善好施的优良品德,结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志愿精神,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功能(丁元竹、江汛清、谭建光,2007:7-8)。事实上,通过志愿服务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依然是今天我们践行志愿精神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