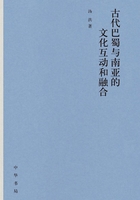
二 从1655年卫匡国《中国新图志》到1912年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
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首倡“ ”为“秦”说,自伯希和唱和之后,此说风行一世,学术界围绕此说展开几百年的论争,拥护者甚众,批驳者亦夥。
”为“秦”说,自伯希和唱和之后,此说风行一世,学术界围绕此说展开几百年的论争,拥护者甚众,批驳者亦夥。
其一,“ ”为“秦”之音译。1615年,金尼阁神父整理利玛窦日记遗稿,并译为拉丁文刊布,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认为:
”为“秦”之音译。1615年,金尼阁神父整理利玛窦日记遗稿,并译为拉丁文刊布,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认为:
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Sina,那在托勒密的时代即已为人所知……今天交趾人和暹罗人都称它为Cin,从他们那里葡萄牙人学会了称这个帝国为China。日本人称它为唐,鞑靼人称它为汉,而生活在更西边的撒拉逊人(Saracen)则称之为Cathay。(14)
利玛窦没有说明“Cin”即为“秦”,但从后文之“唐”、“汉”揣测,交趾人和暹罗人所称“Cin”似应为“秦”。明清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655年出版《中国新图志》(又译《中国新地图集》),在释名中第一次正式将“支那”(Sina)称为“秦”(15)。清末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卷六亦主张“ ”为“秦”之音译:
”为“秦”之音译:
欧洲各国,英谓中国人曰“采宜斯”,法谓中国人曰“细纳爱”。其称中国之名,英人曰“采衣纳”;法人曰“细纳”,又曰“兴”;义人曰“期纳”;德人曰“赫依纳”;蜡丁之音曰“西奈”。问其何所取义,则皆“秦”字之译音也。“西奈”之转音为“支那”。日本之称中国为支那出自佛经,盖梵音又实与西音相通者……揆厥由来,始皇迫逐匈奴,余威震于殊俗。匈奴逐水草而居,其流徙极远者,往往至欧洲北境;今俄、奥、日耳曼、土耳其诸国,未必无匈奴遗种。匈奴畏秦而永指中国为秦,欧洲诸国亦竞沿其称而称之也。(16)
葛方文《中国名称考》亦认为,法国、英国、意大利称中国为“支那”,其名称来源同出于Chin和Thin之声转,再加“a”,“a”者,国土之义,犹言秦国。古代印度和罗马人,均称中国为“Cina”“Thin”和“Sinae”,皆“秦”的外文对音(17)。清末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四亦主张“秦”音之说,但他却认为此秦非赢秦,而为姚秦:
今欧罗巴人称中国为氊拿,或为占泥,皆支那之转音,近时言译语者以支那当为秦字之合音。中国惟秦威烈最盛,故西人至今以称中土。余则谓若作秦音,正当是姚秦之秦,非始皇也。姚秦译经最多,天竺人以支那译其国名,西洋又从印度译之,故展转不可知耳。(18)
文廷式认为欧洲人所谓“China”并不是秦始皇之“秦”,而是翻译佛经最盛的南北朝之姚秦。此名称源自印度人的音译,而后辗转传入欧洲。
其二,“ ”为“秦”之梵语音译。利玛窦、卫匡国之说实为“
”为“秦”之梵语音译。利玛窦、卫匡国之说实为“ ”语源为“秦”之梵语音译之肇端。鲍梯(M. Pauthier)追根溯源,进一步申张利、卫之说,鲍氏认为“支那”称名源于梵语,梵语“支那”由中国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西元前1000年时,已建国于陕西。英国贾儿斯赞成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Sin”“Chin”,皆因“秦”而成,今China末尾之a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19)。1894年,黄庆澄《东游日记》载:“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20)日本高桑驹吉1912年发表《中国文化史》也有相同观点:
”语源为“秦”之梵语音译之肇端。鲍梯(M. Pauthier)追根溯源,进一步申张利、卫之说,鲍氏认为“支那”称名源于梵语,梵语“支那”由中国古代秦国而来,秦国于西元前1000年时,已建国于陕西。英国贾儿斯赞成此说,谓古代印度、波斯及其他亚洲诸国所用之“Sin”“Chin”,皆因“秦”而成,今China末尾之a字,则由葡萄牙人所加(19)。1894年,黄庆澄《东游日记》载:“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20)日本高桑驹吉1912年发表《中国文化史》也有相同观点:
支那一名,原为外国人所呼的名称,固非中国人自加之名。寻绎这名称的起源,却有种种异说,难于决定。但最通行的一说,以为或者是秦始皇帝威势振于四境,其附近的人民称其地曰秦(Chin),后遂转讹而为支那(China),乃由海陆两方面传于印度、中央亚细亚、波斯、西亚细亚以至欧罗巴,复经佛教徒之手而入中国本国。(21)
1911年,德国雅各比(Herman Jacobi)著文《从考铁利亚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文学史料》(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术报告汇刊》1911年第44期)反驳此说,谓西元前300余年,印度栴陀罗笈多王时期,其臣考铁利亚(Kautiliya)《政论》一书中载有“Cina”产丝,秦朝开始于西元前247年,而《政论》成书于西元前300余年,故“支那”不可能为“秦”(22)。
1912年法国伯希和撰文《支那名称之起源》,驳雅各比之论,力主“秦”说。伯氏主张有四:(一)《政论》成书年代不确,不能以之否定支那起源于秦。(二)汉时匈奴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汉书·李广利传》记秦人为汉人。《汉书·匈奴传》载:“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书·西域传》载:“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汉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至唐及国朝则谓中国为汉,如汉人汉儿之类,皆习故而言。”(四)《穆天子传》所言旅行中亚之人是西元前7世纪之秦穆公(23)。美国劳费尔对伯氏之说先存异议,后又以语音学知识补充伯氏秦说,劳氏认为,中国在印度语、伊朗语和希腊语里的名称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这个名字或许可以到中国国内去找,伯希和所举汉朝中国人在中亚被称为“秦人”并不足以证明čina、čen等外国名字都是根据这个“秦”字,伯希和没法从语音上证明这种转生语的可能性。“秦”字古音是当头带有齿音或颚音的din、dzin、džin(jin)、džin,汉语当头的dž音到了伊朗语里成了无声颚音č是可能的,且合乎语音规律。一方面是语音上的一致,另一方面是梵语、伊朗语、希腊语里对中国的称法相同,因此“秦”字语源有其合理性(24)。伯希和为西方极具影响力的汉学家,自伯氏之后,中、西学者大多赞成此说,诸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和中国权威辞书《辞海》等皆采此说。
张星烺力赞“秦”说,其论据有四:(一)雅各比和贾儿斯皆不知秦之建国始于西元前700余年之周平王时代,至西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秦已强大,称霸西戎,早于印度《政论》约350年。西戎边界,可达今喀什噶尔、帕米尔高原,则秦名传于印度不难。汉以前之交通可由沙漠北道经哈密、吐鲁蕃、阿克苏、喀什噶尔至西方,即使秦穆公时秦之势力未及帕米尔高原,仅至安西敦煌附近,秦之威名由商贩而传至印度、中亚也极为容易。(二)秦惠文王(西元前338年即位)灭巴蜀,其时在印度考铁利亚《政论》成书之前。《史记·大宛列传》所载蜀身毒道以及《汉书·西南夷传》所记中原与云南昆明滇越之交通,皆可证明从古即有商道至西南,可以接触印度商贾。秦国在先而甚长久,其名已成商贾口中习惯,不易改变,且汉初武帝之前,为时甚短,诸帝皆不勤远略,以守成为务,故秦之名由巴蜀、滇越而传至印度。(三)西元前177年,匈奴击败月氏,驱之西迁。大月氏自甘肃西徙时,汉朝不知之,而月氏亦不知有汉。秦自穆公时,月氏所居之地已臣属于秦,西徙之时必以为中国皇帝仍为秦之后裔。西方康居国(Sogdia)等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以及希腊人、罗马人之秦国(Thin)、秦尼国(Sinae),皆自月氏得之。春秋战国时,秦与西方交通极繁,至汉初乃完全断绝,至汉武,乃重兴交通。(四)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人及匈奴人在汉武帝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中亚各地在汉初皆隶属匈奴,中亚土人称呼中国皆来自匈奴人之口(25)。向达《中西交通史》亦主印度最古《摩奴法典》和《摩诃婆罗多》所载“ ”因“秦”得声,但向氏认为希腊古书中提到东方出产丝绸的赛里斯(Serice)乃是丝国之意(26)。方豪《中西交通史》探讨《支那名称之起源》亦赞同伯氏所论(27)。饶宗颐《蜀布与
”因“秦”得声,但向氏认为希腊古书中提到东方出产丝绸的赛里斯(Serice)乃是丝国之意(26)。方豪《中西交通史》探讨《支那名称之起源》亦赞同伯氏所论(27)。饶宗颐《蜀布与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亦支持秦说。饶氏认为,司马错灭蜀,在秦惠王时,是时蜀已归安,故蜀产之布,被目为秦布,得以
——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亦支持秦说。饶氏认为,司马错灭蜀,在秦惠王时,是时蜀已归安,故蜀产之布,被目为秦布,得以 称之(28)。季羡林亦赞成此说:“《摩诃婆罗多》,这一部史诗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中国(Cīna)……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中外学者,比较同意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但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间要早一些,总在西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29)杨鹏《诬蔑与辩证:“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一文却认为季羡林主张“Cīna”为丝说(30),似误。
称之(28)。季羡林亦赞成此说:“《摩诃婆罗多》,这一部史诗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中国(Cīna)……我个人,还有其他一些中外学者,比较同意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字来自中国的‘秦’字,但是,比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间要早一些,总在西元前3世纪中叶以前。”(29)杨鹏《诬蔑与辩证:“支那”称谓之源流考论》一文却认为季羡林主张“Cīna”为丝说(30),似误。
韩振华《支那名称起源考释》力驳伯氏之论,认为“Cina”在唐时为“Ci-na”,不作“Cin-na”,而“秦”为N收声的阳声,又对伯氏所举证据作一一辩驳:(一)大秦为译音,并非译意,不能据此认为中国自称为秦。(二)《大方广大庄严经》有3世纪月氏竺法护译本《普耀经》,其中有“秦书”“大秦书”之称,而唐时天竺地婆诃罗重译此经时改为“支那书”“叶半尼书”,可见前者之译已不见重于唐世。而大秦一名始见于《魏略》(三国魏鱼豢撰),因此不能以后见国名附会于佛陀在世时的国名,所以竺法护译支那为秦实有未是。(三)匈奴人及日本人称中国人为秦人不能超过秦始皇以前百年,与《政论》“Cina”之名无关。(四)对于《穆天子传》之穆天子即秦穆公之说,世人也多表怀疑,因此不能引用秦穆公西征事以作秦国国名远播西方之凭据(31)。苏仲湘《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亦反对“秦”说,他认为,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政事论》以及古波斯弗尔瓦丁神赞美诗和《旧约·以赛亚书》中有关“支那”的记载皆早于统一的秦王朝。先秦背景下的秦国,除了后来的百年内外,并没有显著的文治武功,从而也没能对四邻发挥长久影响,加之月氏、匈奴的遮阻,那种认为因秦之影响远传域外而产生“支那”名号的意见,只是揣测之词。匈奴称“秦”和印度称“支那”各有根源,不能混为一谈(32)。汶江(33)、林剑鸣(34)和陈得芝(35)皆著文反对苏仲湘,申张“秦”说。
李志敏《支那名号原音证》亦反对“秦”说,他认为,“秦”说论者提出月氏、匈奴、丝货商人传报秦国之名于印度,但月氏和匈奴进入西域的时代较梵文典籍记述丝绸运销印度的时代迟了大约一个半世纪,而且截止现在还找不到月氏匈奴传报秦名的文字记载和其他较为可靠的线索。西元前4世纪之《政事论》虽有“ ”一词,但其是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
”一词,但其是以复合词的形式出现,“ ”是丝之名物词,而不指中国专名“支那”。佛经所载“震旦”应指雪山(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与“秦”无关,《大唐西域记》等典籍之“至那”为新疆喀什噶尔一带(36)。李志敏《“支那”名号起源时代考——再谈古疏勒支那地名》一文又特别重申早在西元前2世纪古中国之外即已存在“支那”地名,“支那”原为雪山以北包括于阗、蒲犁和古疏勒一带诸种之名,普林尼《自然史》之“赛里斯”与梅拉所述之“赛里斯”以及阿奴比由斯《驳异教者论》之“赛里斯”当同指中亚前部一带,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赛里斯”,“赛里斯”之为中国名号,不会早于西元4—5世纪(37)。此外,李志敏还撰文《“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进一步证明“支那”(秦)地名广泛分布于自中国至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主干线及支线上,是许多地方的泛指称名。从中国中原直至非洲埃塞俄比亚皆有“赛里斯”之名,此与“支那”(秦)属于同名之异呼,从而可知梵文“支那”(秦)与“赛里斯国”的“丝绸之国”涵义相同(38)。李氏三文所论,旨在澄清“支那”名号起源、原始涵义及指谓诸问题,批驳“秦”说,为自己所主之“丝”说申说论证。此外,朱文通《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39)亦反对“秦”说。
”是丝之名物词,而不指中国专名“支那”。佛经所载“震旦”应指雪山(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雅鲁藏布江流域,与“秦”无关,《大唐西域记》等典籍之“至那”为新疆喀什噶尔一带(36)。李志敏《“支那”名号起源时代考——再谈古疏勒支那地名》一文又特别重申早在西元前2世纪古中国之外即已存在“支那”地名,“支那”原为雪山以北包括于阗、蒲犁和古疏勒一带诸种之名,普林尼《自然史》之“赛里斯”与梅拉所述之“赛里斯”以及阿奴比由斯《驳异教者论》之“赛里斯”当同指中亚前部一带,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赛里斯”,“赛里斯”之为中国名号,不会早于西元4—5世纪(37)。此外,李志敏还撰文《“支那”名号涵义及指谓问题》,进一步证明“支那”(秦)地名广泛分布于自中国至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主干线及支线上,是许多地方的泛指称名。从中国中原直至非洲埃塞俄比亚皆有“赛里斯”之名,此与“支那”(秦)属于同名之异呼,从而可知梵文“支那”(秦)与“赛里斯国”的“丝绸之国”涵义相同(38)。李氏三文所论,旨在澄清“支那”名号起源、原始涵义及指谓诸问题,批驳“秦”说,为自己所主之“丝”说申说论证。此外,朱文通《历史文献学的考察视角:“支那”词义的演变轨迹》(39)亦反对“秦”说。
其三,“支那”为瓷器。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谓:
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瓷器之谓也。(40)
此说今日甚为流行,然中国瓷器大量远销欧洲已是宋、明后赖海路运输的结果,此显为欧洲用古已存在的“China”名称来代指当下风行一时的中国瓷器,“China”称名是因,以“China”借指“瓷器”是果。世人认为“China”为“瓷器”的说法纯属倒果为因,因而此说不足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