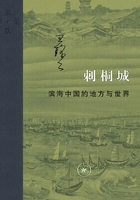
经验与反思
我们之所以在一开篇就揭示出泉州古代开放史辩论的文化政治成因,旨在指出,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历史撰述如何避免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权力结构的制约?如何反映文化过程错综复杂的内在运行逻辑?如何反映人们的具体生活?如何反映这种具体生活在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近年来,社会学对于社会科学学科体制与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论述,人类学对于文化与实践之间关系的争鸣,历史学对于国族和世界通史之外的“另类声音”的挖掘,共同为我们表明,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不仅关系到历史研究本身的前景,而且对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将有着关键影响。
在我看来,解决或部分解决历史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只凭反思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在经验研究和叙述中对以往的理解进行反复检验。这类经验研究近期得到了重视。作为这类研究缤纷多彩的成果的小小局部,此前我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一书 ,试图在具体的地方性研究中叙述文化过程的实践性与社会复杂性。该书叙述一个离泉州不远的家族村落历史上地方性制度的形成与变化,试图借此侧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式的现代性对于地方传统的破坏性影响,及地方传统走向自己未来道路的过程。这项研究与社会史的探讨有若干类似之处,它强调以经验的地方史料为基础来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地方史的具体过程。然而,与一般社会史不同的是,该书追求更直接地面对现代观念形态及其对历史叙述的影响。在写作该书时,我意识到,若要在历史叙述中避免文化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的双重制约,便要树立多线的历史叙述方式,以理解地方。
,试图在具体的地方性研究中叙述文化过程的实践性与社会复杂性。该书叙述一个离泉州不远的家族村落历史上地方性制度的形成与变化,试图借此侧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式的现代性对于地方传统的破坏性影响,及地方传统走向自己未来道路的过程。这项研究与社会史的探讨有若干类似之处,它强调以经验的地方史料为基础来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地方史的具体过程。然而,与一般社会史不同的是,该书追求更直接地面对现代观念形态及其对历史叙述的影响。在写作该书时,我意识到,若要在历史叙述中避免文化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的双重制约,便要树立多线的历史叙述方式,以理解地方。
我的论述可以说是历史批判理论的经验延伸;相关于此,我们可以涉猎的文献很多,而在其中,我感到应提及1995年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这部书是对近代历史观念的批评性研究,它的起点被作者定在启蒙时期,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基本论点是,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因深受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理性历史论影响,它的论述不能脱离西方的历史行进规律,而这个规律本身就是近代民族思想与理性历史思想融合的产物。这个所谓“历史规律”不仅影响了西方中国观,而且也影响了中国政治话语对国家自身历史的理解,甚至影响到近代国家和上层精英的行动。
在杜赞奇的阐述中,近代的、理性的、单线规律性的历史观念,是民族主义和现代性胜利的成果,而并非历史事实本身。杜赞奇没有解说他眼中的历史真相是什么,但他警告历史学家们,不应对历史进行过于理性的想象。
在乡村社区史研究中,我引述了杜赞奇的另一部同样有影响的作品 ,从中吸收了后来才在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充分阐述的观点。
,从中吸收了后来才在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充分阐述的观点。
我承认,杜赞奇的历史话语解构有助于我们认清认识历史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障碍。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不把历史话语放在历史的具体过程中考察,那么,我们的认识便会被局限在观念史的解析里,无以触及观念获得界定、产生效应的过程。
近代理性史观的观念形态力量,既来自西方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学观、历史观与世界观,又来自这种西来世界观在欧亚大陆东部国度中的官方化和主流化。这种观念形态,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其力量的揭露,时常被这种力量所消化,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因而,似乎唯有那些躲开这种观念形态的“另类观念”,才可能发挥挑战性作用。从某个角度看,我自己的乡村社区史研究,可以说正是在寻求这种替代性观念形态中写就的;借之,我意在指出,官方化和主流化的历史观念之所以能够获得说服力,是因为它们以武断的手段将历史的事实分离于它们存在的原本场合之外,把它们变成时间的片段,最终将这些片段重新编织成一幅历史的图像。从而,要对这种武断的史观加以真正的批判,就要将历史放归到演绎历史的地方性场合中去,使其原貌得以尽可能充分的呈现。若是做了这项工作,我们便会认识到,基于村落社区史而展开的历史叙述,本身会面临三种历史发出的拷问:第一种历史就是围绕着地缘和血缘关系而呈现出来的社会史过程;第二种历史是研究者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出发学会被研究者的生活方式与话语方式的过程;第三种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行动者或被研究者的历史观念本身,它反映学者与非学术民间历史观念体系的积极互动。其中,第一种历史可以说是经验的(empirical)历史,即学者依据自身的认识论模式来重新建构的客观历史过程;而第二、三种历史则主要属于反思或反身的(reflexive)历史,即研究者鉴于自身认识论模式的缺陷而展开的观念层面的历史探索及对被研究者历史观念的吸纳。这种种历史,都是“历史事实”,但作为“历史事实”,它们指的并非只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指历史学家借以了解、认识、解释,甚至“发现”历史的文本手段(如民族国家的“通史方法”)。
对于历史学而言,如果说这样的叙述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到目前为止,人类学对于民族志方法的论述,已经不能简单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研究和描述方法了。不过,为了阐明这种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参照性意义,我们不妨以民族志的原初形态为蓝本,借之切入问题。
自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以来,田野工作(fieldwork)长期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功,而这种研究风格就是在批判超地方的宏观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类学学者沉浸于远古的历史之中。19世纪后期,欧美人类学学者受进化论制约,广泛地收集第二手的人文类型素材,依据传教士和冒险家所写的没有被证实的游记,猜测地构造宏观的世界文明史。20世纪初期,德国文化传播论和美国历史具体论的相继出现,在表面上对进化论提出一个理论挑战,而在方法论上仍然没有摆脱旧有宏观人类史的影响。直到20世纪,功能主义出现后,人类学的方法论才开始从宏观人类史意象中分化出来,进入实地研究的时代。马林诺夫斯基是这一人类学方法转变的首倡者之一,他对以前的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方法论批判。他认为,进化论、文化传播论以及历史具体论,或在进化的阶段问题上绕圈子,或在这种或那种文化现象如何传播的问题上索求来龙去脉,而对于界定和联想文化因素在文化事实中的运作没有赋予充分的重视。为了克服这一方法论弱点,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类学学者不应把物质文化、人类行为、信仰与理念分割开来进行分别的排列组合,而应把它们放在“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或所谓的“分立群域”(isolates)的整体中考察,展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学者之所以要展开田野工作,是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当成活着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认为只有将它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进行联想,才能够体现或理解它的意义。具体而言,对于诸如马林诺夫斯基一类的学者,田野工作是对制度的整体面貌、被研究者认识中的制度、风俗和活动、日常生活中的非思索性素材(the imponderabilia of everyday life)以及被研究者的叙述加以总体认识的过程,而民族志则是有关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关联性的经验和理论陈述。
许多批评者指出,这种功能主义的观察和叙述模式,存在着虚伪的一面,它因过于突出人类学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而难以避免地会出现借“科学”之名把研究者自身的主观理论想象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的倾向。
对于现代民族志的这种违背初衷的倾向,我也深有戒备之心,然而,这种戒备之心并没有阻碍我去理解现代人类学学者所提倡的对于被研究者生活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的尊重。在田野工作中,如同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那样,我关注制度整体面貌、被研究者的社会知识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单线的历史观念的“无意识”。出于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我尽力规避发生于地方之外的单线进化史观,沉浸于梳理在地方中共存的多线而交错的历史线条。不过,我的研究不等同于功能主义平面式民族志。人类学在批判西方中心的理性宏观人类史观时,也犯了一个重大的矫枉过正的错误。在正确地反对把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强加在非西方文化身上的过程中,早期人类学学者却错误地否定非西方文化的历史,他们把文化当成人的生活的空间平台,却没能意识到,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着的人们,都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而“创造历史”包含人们现实的社会再生产和发明以及人们在观念的层面上对自己文化的历史见解。要克服功能主义对历史的漠视,新一代人类学学者有必要在他们的民族志文本中重新提出处理历史与他们的研究主题——文化——之间关系的方案。因而,如何在避免否定被研究者的历史生存权利的同时,避免受单线的理性史观的制约,成为人类学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能意识到,现代性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近代以来的文化精英的深刻影响。因此,我在叙述中强调把这种影响放置在经验的描述中作为一种分析的对象来叙述,意在避免把它当成自然而然成立的历史框架,避免以自身的生活和观念来衡量被研究者的生活和观念。
,而“创造历史”包含人们现实的社会再生产和发明以及人们在观念的层面上对自己文化的历史见解。要克服功能主义对历史的漠视,新一代人类学学者有必要在他们的民族志文本中重新提出处理历史与他们的研究主题——文化——之间关系的方案。因而,如何在避免否定被研究者的历史生存权利的同时,避免受单线的理性史观的制约,成为人类学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我能意识到,现代性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近代以来的文化精英的深刻影响。因此,我在叙述中强调把这种影响放置在经验的描述中作为一种分析的对象来叙述,意在避免把它当成自然而然成立的历史框架,避免以自身的生活和观念来衡量被研究者的生活和观念。
这类求索已被称为“历史人类学”。顾名思义,这个研究风格是历史与人类学方法的结合,即“人类学的历史化”(或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的“历史学的人类学化”)。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不满于人类学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学者,已经提出要在民族志的方法内植入历史学的因素。不过,当时他们强调的是在部落社会和地缘性社区的研究中,增加对于地方政治权力演变史的考虑,而没有考虑到“历史”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双关的语汇,它既指历史过程本身,又常常被用来形容对于历史的叙述。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一些不满于人类学的平面史叙述模式的学者,已经提出要在民族志的方法内植入历史学的因素。不过,当时他们强调的是在部落社会和地缘性社区的研究中,增加对于地方政治权力演变史的考虑,而没有考虑到“历史”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双关的语汇,它既指历史过程本身,又常常被用来形容对于历史的叙述。 80年代以后,人类学界再度对历史产生关注。这时,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已经不再是60年代意义上的“小型社会群体政治史”了。8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深受两股潮流的影响。70年代提出的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宏观体系中理解历史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兴起,这对于专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小型非西方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人类学学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何让小型社会群体的民族志描述与对人类学研究对象影响至深的世界体系相联系?如何使二者互为照应?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时成为人类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80年代以后,人类学界再度对历史产生关注。这时,历史人类学的意义已经不再是60年代意义上的“小型社会群体政治史”了。8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深受两股潮流的影响。70年代提出的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宏观体系中理解历史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兴起,这对于专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小型非西方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人类学学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何让小型社会群体的民族志描述与对人类学研究对象影响至深的世界体系相联系?如何使二者互为照应?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时成为人类学界的重要关注点。 从这些问题延伸出来的另一种问题,与人类学的知识形成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以后,人类学学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的研究无非是西方政治经济势力在世界上逐步获得支配权这一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人类学的知识与近代世界权力格局的转变有何种关系?这个问题促使人类学学者回到“表述”(representations)、“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文化霸权”(hegemony)等批判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去反省自身的知识构成,促使“主观历史”(subjective history)的概念与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相结合,引出了“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主要话题。这一话题的含义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的人类学,只不过是近代西方中心的权力格局的一种主观历史想象。
从这些问题延伸出来的另一种问题,与人类学的知识形成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以后,人类学学者猛然醒悟到自己的研究无非是西方政治经济势力在世界上逐步获得支配权这一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人类学的知识与近代世界权力格局的转变有何种关系?这个问题促使人类学学者回到“表述”(representations)、“话语”(discourse)、“意识形态”(ideology)、“文化霸权”(hegemony)等批判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去反省自身的知识构成,促使“主观历史”(subjective history)的概念与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相结合,引出了“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主要话题。这一话题的含义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的人类学,只不过是近代西方中心的权力格局的一种主观历史想象。 比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蔓延稍后,对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批评性研究也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兴起。这一类的研究,促使学者们进一步对历史想象在政治空间单位的营造中的作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它们不仅使学者们意识到象征的表述对于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辅助作用,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叙述可能潜藏着观念形态因素。
比殖民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蔓延稍后,对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的批评性研究也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兴起。这一类的研究,促使学者们进一步对历史想象在政治空间单位的营造中的作用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它们不仅使学者们意识到象征的表述对于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辅助作用,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叙述可能潜藏着观念形态因素。
80年代以来,人类学对文化研究中隐含着的历史意象之否思,逐步推动了三类学术研究的进步:第一类,是至今影响仍然巨大的对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及民族主义的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的直接解构 ;第二类,是在传统研究及叙述风格范围内展开的对于历史话语和叙述之本质的重新考察
;第二类,是在传统研究及叙述风格范围内展开的对于历史话语和叙述之本质的重新考察 ;第三类,则是对于如何在学术文本中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其他声音”(other voices)的激发。属于第一类的,除了类似于杜赞奇那样的现代性与民族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作品之外,还有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产生影响的殖民主义与人类学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属于第二类的,有诸如童金(Elizabeth Tonkin)所著的《叙述我们的过去》之类的作品。这部作品
;第三类,则是对于如何在学术文本中认可、展示、强化权力中心和主流话语范围之外的“其他声音”(other voices)的激发。属于第一类的,除了类似于杜赞奇那样的现代性与民族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作品之外,还有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产生影响的殖民主义与人类学之间历史关系的研究。属于第二类的,有诸如童金(Elizabeth Tonkin)所著的《叙述我们的过去》之类的作品。这部作品
从非洲调查的实例和理论思考并行的新角度出发,考察历史叙述的社会本质,它的雄心在于通过传统人类学的民族志分析,探讨历史叙述的本质性特征。属于第三类的,包括了两类相互之间对话不多的作品,其中一类是在反思人类学的旗帜下展开的对于人类学知识与被研究者知识之间对话的探讨 ,而另一类则一如著名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近作一样,强调世界体系下非西方文化结构在历史创造中的强大能动性。
,而另一类则一如著名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近作一样,强调世界体系下非西方文化结构在历史创造中的强大能动性。
我在《社区的历程》一书里通过一个小地方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所要做到的,便是把人类学近年对于历史的重新思考进行经验的叙述。我的本来旨趣,在于开拓历史、文化、权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空间,从而为历史人类学的运用提供一个具体研究的范例。尽管受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单位的制约,这项研究无法充分展现人类学与历史理论界关注的那些超地方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格局与文化变迁关系的历史深度,但其中力求实现的经验的历史与反思的历史之间的结合,已经为本书的写作设下了潜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