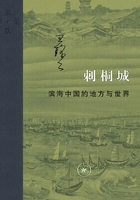
1.引论
本书叙述的历史,是围绕泉州展开的。这座中国东南沿海古城,知名度不如西安、南京、杭州、北京等“帝都”,但其一千多年的历史所留下的旧事,早已为学界所关注。泉州常被称为“中世纪世界第一大商埠”、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古代“东方第一大港”,近期还常被冠以“海上丝绸之路名城”的称号。20世纪70年代初期,泉州宋船的发现(图1.1),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宋元开放港市的存在,而今天到过泉州的人也不难发现,此处宗教文化遗迹异常丰富,表明这座古城曾有世界各大宗教并存,而相关遗存有的依旧在地面上“活着”,有的从地下出土,因为它们的存在,泉州常被誉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

图1.1 1974年泉州宋船发掘现场
一个在历史上兴盛过相当长时间的地方,所能引起人们的感叹复杂多样。有关泉州,在西方中国学界,关注点似乎集中在古代泉州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之限度问题上。这里有一个具有说明意义的例子。1997年,在英国出版了一部叫作《光之城》的著作 ,该书署名原作者是古代意大利的雅各·德安科纳〔Jacob D'Ancona,意为安科纳(Ancona)地方的雅各〕,封面上有这样的文字:“在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国都市,称作光之城。”据称,雅各是位商人兼学者,他于1270年出发来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到达泉州。《光之城》记录了他在泉州的见闻。在雅各笔下,泉州是古代东方的一座大城市,有“一个很大的港口”,城南“整个江面上布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种族、语言、文化多样,来这个城市的商人很多,“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还有中国的商人,以及来自该省乡镇的商人”, “这样一起生活在刺桐城的各种民族、各种教派,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更饶有兴味的是,这里的人们生活自由,有的人本为怀,文化疆界意识淡薄;有的信奉传统,对有别于其他的“道”倍加珍惜。他们到雅各来访之时,已分化为接近于自由派与文化守成派的阵营,其观点表达直白有力,对社会到底该重商开放还是自足,对处理城市内外种族和文化的关系问题,热烈地争鸣着。
,该书署名原作者是古代意大利的雅各·德安科纳〔Jacob D'Ancona,意为安科纳(Ancona)地方的雅各〕,封面上有这样的文字:“在马可·波罗之前,一位意大利犹太商人冒险远航东方,他的目的地是一座中国都市,称作光之城。”据称,雅各是位商人兼学者,他于1270年出发来华,1271年(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到达泉州。《光之城》记录了他在泉州的见闻。在雅各笔下,泉州是古代东方的一座大城市,有“一个很大的港口”,城南“整个江面上布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种族、语言、文化多样,来这个城市的商人很多,“有法兰克人、萨拉森人、印度人、犹太人,还有中国的商人,以及来自该省乡镇的商人”, “这样一起生活在刺桐城的各种民族、各种教派,都被允许按照自己的信仰来行事,因为他们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更饶有兴味的是,这里的人们生活自由,有的人本为怀,文化疆界意识淡薄;有的信奉传统,对有别于其他的“道”倍加珍惜。他们到雅各来访之时,已分化为接近于自由派与文化守成派的阵营,其观点表达直白有力,对社会到底该重商开放还是自足,对处理城市内外种族和文化的关系问题,热烈地争鸣着。
无论《光之城》是珍本,还是后人编凑的“伪书”,对向达的唐长安城研究 和潘光旦的古代开封犹太人研究
和潘光旦的古代开封犹太人研究 稍有了解的人,对其描述的东方城市的种族—文化混杂性,不会有太多惊讶;对古代中国思想“百花齐放”的胜景略有所知的人,对其记述的争鸣,一样也不会有太大意外。
稍有了解的人,对其描述的东方城市的种族—文化混杂性,不会有太多惊讶;对古代中国思想“百花齐放”的胜景略有所知的人,对其记述的争鸣,一样也不会有太大意外。
然而,这部新版古书,却引起了不少相信传统不同于现代的学者的质疑。版本学质疑(只有该书的译者,即在意大利偶然发现该书的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David Selbourne才见过原著,而他拒绝公开原著手稿,因此没有人能够判定《光之城》手稿的真伪),也许不是争论的要点。无论《光之城》是真是伪,它所引起的紧张,更多源于一个事实,即,它与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国观有重大出入:在常见的近现代历史著述中,西方文明的东渐,最早开始于明末耶稣会入华,此前,即使是在东南沿海,古老的东方尚未被先进的西人触及,绝无可能如此开放;而令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光之城》通过零碎的描述,似乎还隐含一种主张,即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远东早已有了种族—文化的兼容并蓄面貌,也有了重商与抑末的政治经济思想辩论。
《光之城》在西方中国学界引起的争论,与马可波罗是不是到过中国这个老问题相延续 ,反映了西人的一种心态——若是让他们发自内心表达观点,那么他们绝不愿承认,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着自己的“世界体系”。西方学者自认的天职,是去发现和解释疑点,激发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事物的重新认识。然而,在历史的论辩中,他们却经常出于个人或社会的原因,有意无意地复制学术研究背后的关系制度,尤其是不平等的跨文化关系制度。
,反映了西人的一种心态——若是让他们发自内心表达观点,那么他们绝不愿承认,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着自己的“世界体系”。西方学者自认的天职,是去发现和解释疑点,激发人们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事物的重新认识。然而,在历史的论辩中,他们却经常出于个人或社会的原因,有意无意地复制学术研究背后的关系制度,尤其是不平等的跨文化关系制度。
当然,必须强调,这一对西方学术的批评,绝对不是为了迎合文化本土主义心态。其实,我也要在此指出,与西方中国学研究一样,国内学界出于个人或社会的原因,也赋予历史特定的价值。兴许正是因此,《光之城》一书出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对于类似于书中描绘的情景之“实在”,早已深信不疑。国内学者对于汉唐的世界开放性之关注,出现得比较早,但似乎停留在对“西域”这个概念的不断诠释上,随着“中西交通史”“海外交通史”之类概念的兴起,人们也逐步意识到,应该到“海洋西域”去发现一个开放而富有启蒙性的文明史。“泛太平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洋文化研究”等等名目,与现代主义文明史观相伴随,来到我们的话语世界。以东南沿海著名古城泉州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强调的正是这种开放而富有启蒙性的文明史在东方历史上的实际存在。或许也是因为存在那种文明史观恰好符合了一个开放古国的叙事,所以,泉州宋元港市的研究,才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声名显赫。在泉州当地,我们能够见识一些拥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声望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集中在泉州港兴盛期这个专门史主题上。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术泉州成果丰硕,堪称辉煌。这里,地方性文史研究极为发达,而比起那些偏向研究与所谓“泉州特色”关系不大的专题的学者而言,他们中那些专注于海外交通问题研究的学者,更早已在国际学界谋得一席之地。即使是在政府的文物保护和文化管理行政中,宋元泉州的景象也被展示得最为突出,而那些偏离这个地方断代史的研究则往往因被轻视而落入冷门。
“别的国家有的东西我们也有!”这个希望应该说是所有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最朴素的表达。而当历史学家努力地试图“证实”在本土文明史上一度存在过西方也有过的“好时光”(或“辉煌时代”),我们同时也会不禁感叹,这样的历史学,追求的不是别的,而无非是在论证“我们也拥有过他们拥有的东西”。
兴许可以认为,一度在中国史学界的话语中占相对支配地位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 ,就是为了证实中国存在过西方有过的“进步”而提出的。
,就是为了证实中国存在过西方有过的“进步”而提出的。
我无意否定泉州历史上黄金时代的现实存在;相反,如我在提及向达和潘光旦的研究时所刻意表露的,我认为,在并不那么遥远的过去,这个时代实际存在过,并且,其令人惊讶的开放性,值得我们这些以为开放社会只与现代性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加以充分重视。我甚至相信,这种古代开放性能引发社会科学革新,其自身含有重大价值。然而,与此同时,我却也感到有责任指出,如上所述,那种以重新发现旧有开放文明时代为己任的历史研究,同样需要我们加以重新思考。
在双重心态下,我深感,就我们这里关注的泉州地方史而言,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二:其一,为什么海外史学界会怀着一种极度猜疑的心态来面对一部叙说古代中国城市中的市民生活开放性景观的古代文献?其二,与海外史学界不同,为什么我们的史学界同行们总是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文明一度也“很开放”“很启蒙”?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的思考,要求我们回到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以来对于“文化”(culture)这个概念的不同界定。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文化”这个概念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的广泛运用,与两个重要的历史场景有密切的关系。其一,在欧洲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文化成为“使现代式的、侵略性的、商业性的以及残暴的都市经验中性化(neutralize)的(手段)” ,它把历史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一个文化的传统时代,后一部分是文化“现代性的”时代。一方面,这个历史的两分法帮助人们在想象中营造出一个认同于作为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它也促使现代式的经验成为人们“可欲”的未来。其二,在欧洲对外的权力扩张中,文化长期被用来形容不同于“现代”的众多非西方民族的历史与实践,它把非西方的历史归结为一个没有时间流动的平台,使之成为西方殖民扩张的整体化对象。
,它把历史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一个文化的传统时代,后一部分是文化“现代性的”时代。一方面,这个历史的两分法帮助人们在想象中营造出一个认同于作为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另一方面,它也促使现代式的经验成为人们“可欲”的未来。其二,在欧洲对外的权力扩张中,文化长期被用来形容不同于“现代”的众多非西方民族的历史与实践,它把非西方的历史归结为一个没有时间流动的平台,使之成为西方殖民扩张的整体化对象。 由于文化的概念与权力的结构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对于人们的认识影响至深,成为人们司空见惯地用来形容那些难以概括的差异和关系的办法。受这样的文化想象之制约,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专家们难以想象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中也存在过与它的启蒙时代一样的文明史。因而,在探索这些社会的历史中,他们有意无意地采用一种文化比较的方法,把被动的非都市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看成不开化的“蒙昧”“野蛮”和“古代”社会,将之与现代的欧洲相比较,从而在其中确立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自信心。
由于文化的概念与权力的结构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对于人们的认识影响至深,成为人们司空见惯地用来形容那些难以概括的差异和关系的办法。受这样的文化想象之制约,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专家们难以想象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中也存在过与它的启蒙时代一样的文明史。因而,在探索这些社会的历史中,他们有意无意地采用一种文化比较的方法,把被动的非都市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看成不开化的“蒙昧”“野蛮”和“古代”社会,将之与现代的欧洲相比较,从而在其中确立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自信心。
对于古代泉州开放史和市民启蒙社会存在的否定,兴许不无证据,却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自信心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尽管“文化”一词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容,却往往吊诡地成为被帝国主义支配的民族自我叙说的凭据。
以中国为例,在近代形成的“世界体系”中 ,它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形态的原创地,也不属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宗主国,因而,它对于文化的想象也处在一个较为被动的地位。在与近代西方势力接触以前,中国倾向于把自己的国土想象成一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形容为“天下”。直到19世纪末,所谓“中国人的文化”这个说法,一直只有从西方东来的传教士话语中才有。19世纪末以后,华语世界开始大量涌现谈论自己文化的潮流。这个时代,中国思想界已经广泛接触了西方文明,从中汲取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和文化观
,它既不属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形态的原创地,也不属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宗主国,因而,它对于文化的想象也处在一个较为被动的地位。在与近代西方势力接触以前,中国倾向于把自己的国土想象成一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形容为“天下”。直到19世纪末,所谓“中国人的文化”这个说法,一直只有从西方东来的传教士话语中才有。19世纪末以后,华语世界开始大量涌现谈论自己文化的潮流。这个时代,中国思想界已经广泛接触了西方文明,从中汲取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和文化观 ,而为了抵制外来影响,学人和政客还把这一观念贯穿于政治话语的实践中,通过类似于欧洲的想象来营造民族的历史认同。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不能说只有一种,然而众多不同看法均具有两个共同的关注点,一是关注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史界定,二是关注作为独特体系的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差异。为了对这两个共同的关注点进行阐述,学人和政客不仅引用了大量西学论点,而且还表现出对于上古时代以至宋明理学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的思想史的高度兴趣。这就在思想界造成了一个影响至深的后果:尽管中国的文化论述属于文化接触的被动产物,但这些论述的推行者却与文化论述的原创者一样,积极把想象中的“文化”与国家的内外格局相联系,从而创造一种扭曲历史本相的历史表述。针对西方文化概念的权力背景,一位西方人类学家反思说:“我们务必记住,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出现的。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某些欧洲国家试图为自己创造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只好为争取各自的认同和独立性而斗争。把每个斗争中的国家比拟成占有一个由其文化的特殊精神所激励的独特社会,目的正在于为各民族营造自立的国家提供合法性解释。”
,而为了抵制外来影响,学人和政客还把这一观念贯穿于政治话语的实践中,通过类似于欧洲的想象来营造民族的历史认同。在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不能说只有一种,然而众多不同看法均具有两个共同的关注点,一是关注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的思想史界定,二是关注作为独特体系的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差异。为了对这两个共同的关注点进行阐述,学人和政客不仅引用了大量西学论点,而且还表现出对于上古时代以至宋明理学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的思想史的高度兴趣。这就在思想界造成了一个影响至深的后果:尽管中国的文化论述属于文化接触的被动产物,但这些论述的推行者却与文化论述的原创者一样,积极把想象中的“文化”与国家的内外格局相联系,从而创造一种扭曲历史本相的历史表述。针对西方文化概念的权力背景,一位西方人类学家反思说:“我们务必记住,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出现的。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某些欧洲国家试图为自己创造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国家则只好为争取各自的认同和独立性而斗争。把每个斗争中的国家比拟成占有一个由其文化的特殊精神所激励的独特社会,目的正在于为各民族营造自立的国家提供合法性解释。” 这段话,针对的是欧洲文化概念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角色。然而,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探讨,似乎也没有超越为“营造自立的国家”提供合法性解释的地位。百年来中国学人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就是在对于世界体系中的国族主权的追求中展开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开化文明史探索的基本话语基础。
这段话,针对的是欧洲文化概念在民族国家形成中的角色。然而,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探讨,似乎也没有超越为“营造自立的国家”提供合法性解释的地位。百年来中国学人的文化研究,可以说就是在对于世界体系中的国族主权的追求中展开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古代开化文明史探索的基本话语基础。
诸如此类的主流文化观,与特定的权力格局有着某种关系,它们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赢得了明显的或潜隐的认识论支配性,它们的支配性,使我们的观察、解释和想象充满着吊诡。对文化的概念体系加以反思后,不难发现,主流观念几乎可以说“天然地”含有严重缺陷。与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主权性相联系的文化概念,多半是在毫无反思的思想状态下提出的,因而也不能够充分自觉地体现其自身的真实含义。事实上,现存文化理论大多注重权力的揭示,注重如何运用文化的符号来营造不同民族、社会群体及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逻辑,于是,这些理论本身反映的并非文化的运行逻辑,而是其他。因此这种主流文化“理论”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文化本身是在不同因素的互动和结合过程中形成的,并非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均质的静态体系。出于同一原因,主流文化“理论”基本上是在脱离生活中的人和社会之关系体制的状况下被提出的,其所表述的文化在表面上具有一种反映“民族精神”(ethnos)的功用,而在实质上却否定了“民族精神”的真实含义在于社会群体中的人的具体实践及人对周围环境认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定了人们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经验对于文化理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