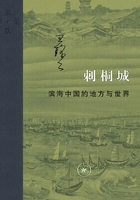
历史、文化与权力
我对泉州的研究,开始于1985年。为了完成学位论文,我在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的指导下,从人口史的角度探讨了唐宋时期泉州港市的成因。这篇习作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地方人口的饱和迫使泉州在唐以后对传统的农业生计做出重新选择,转向符合地方地理环境特色的海外贸易业。到了明清时期,在朝廷“海禁”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泉州港市贸易业衰落,但由于人口压力依然存在,因而出现了海外移民的潮流。 在完成这篇学位论文之后,我曾因学习需要从泉州研究转向人类学和东南民族史研究,直到1990年重新回到泉州从事人类学田野考察时,才有机会对这座古城再次展开调研工作。
在完成这篇学位论文之后,我曾因学习需要从泉州研究转向人类学和东南民族史研究,直到1990年重新回到泉州从事人类学田野考察时,才有机会对这座古城再次展开调研工作。
1987年10月,我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两年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准备之后,我必须按照学位论文的要求选择一个地点从事田野工作。对我而言,当时的选择,若不是去印度、非洲之类的异乡,最好就是家乡泉州了。这部分是因为作为一个位于“边陲”的城市,这个地方在一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类学学者当中已经小有名气,可以成为一个有学界基础的研究基地;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人类学的过程中,已形成一定的研究旨趣。我当时觉得,通过家乡式的研究来叙说“文化”这个人类学的关键词所含有的政治意义,在我从事的学科中是有紧迫性的。1990年5月至1991年4月间,我从英伦回到家乡,从事了一年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依据我对泉州的体验式的认识,当时我计划把自己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年度周期仪式上。在开始田野工作之前,我提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性假设,准备拿到田野考察中验证。这个理论解释性假设的核心概念,就是仪式时空(time-space of ritual)。按照象征人类学的立场,任何年度周期仪式首先象征一套时间的概念,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对于时间加以象征切割的结果。但是,单说年度周期仪式是时间的象征界定还不够,因为任何一套象征性的时间界定都反映了社会中人们对于空间范围及其神圣性的确认,并且中国社会力量分化清晰,不同的“势力”均可能拥有各自的社会空间,也因此拥有各自对时间的象征表述。
在泉州,存在三套主要的年度周期仪式。其中第一套就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被宣布为“法定节日”的那套仪式,这套仪式在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动,但总的来看与新确立的单位行政制度、传播(宣传)制度、日常生活的控制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民族国家空间的地方性展示。第二套就是由地方文化管理部门创造的以地方文艺类型的展演为核心内容的周期性“艺术节”。在我展开田野工作期间,泉州的这些艺术节庆有南音大会唱、国际木偶节等等,主要内容都在于展示地方戏曲文化的丰富性,但因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故常与国家对内、对外的形象塑造和政治经济操作有莫大关系。除了上述两套官方组织的仪式之外,泉州城区还存在另外一些民间周期性的仪式活动,大致包括如下三类:(1)以家为中心的传统节日和祖先祭祀仪式;(2)以土地公每月二度的诞辰庆祝为周期的仪式;(3)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区地缘社区分类为中心的所谓“铺境”仪式。 若把这三大类仪式看成当地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便不难发现,这一文化景观的多元组合与当地社会空间中的权力格局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第一套仪式显然并非铁板一块,它经历了几度历史变迁:从20世纪50至70年代,其主要的形式表现为所谓“群众文化活动”、宣传媒体与单位制的机构的活动节奏的结合;80年代以来,随着单位制的部分弱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这一套仪式已经逐步出现向不同部门的工作节奏、家庭生活和传播媒介的节目安排综合蜕变的趋势。不过,尽管有这些历史变化,这一套仪式总体而言是民族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动员的重要渠道。第二套仪式在文化特征上属于地方性的,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地方文化的演示。这些仪式都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的宣传和文化管理部门的组织安排下展开的,他们演示的地方文化与地方民间的文化形式构成巨大差异,成为官方化的文化活动。因为组织这些活动的地方官员在身份上介于超地方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权力之间,所以他们组织的活动难免具有一定“综合性”。也就是说,这些活动既具有国家控制地方文化活动的色彩,又具有一定的地方中心主义色彩。第三套仪式被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称为“迷信活动”,它们在组织上有的以家庭为核心,有的以非官方的社区民间组织机构为核心,在内容上有强烈的非正统色彩,显然与近年民间力量的“解放”有着密切关系。
若把这三大类仪式看成当地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便不难发现,这一文化景观的多元组合与当地社会空间中的权力格局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第一套仪式显然并非铁板一块,它经历了几度历史变迁:从20世纪50至70年代,其主要的形式表现为所谓“群众文化活动”、宣传媒体与单位制的机构的活动节奏的结合;80年代以来,随着单位制的部分弱化及大众传媒的发展,这一套仪式已经逐步出现向不同部门的工作节奏、家庭生活和传播媒介的节目安排综合蜕变的趋势。不过,尽管有这些历史变化,这一套仪式总体而言是民族国家的象征,是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动员的重要渠道。第二套仪式在文化特征上属于地方性的,它们的主要活动是地方文化的演示。这些仪式都是在地方党政机关的宣传和文化管理部门的组织安排下展开的,他们演示的地方文化与地方民间的文化形式构成巨大差异,成为官方化的文化活动。因为组织这些活动的地方官员在身份上介于超地方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权力之间,所以他们组织的活动难免具有一定“综合性”。也就是说,这些活动既具有国家控制地方文化活动的色彩,又具有一定的地方中心主义色彩。第三套仪式被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称为“迷信活动”,它们在组织上有的以家庭为核心,有的以非官方的社区民间组织机构为核心,在内容上有强烈的非正统色彩,显然与近年民间力量的“解放”有着密切关系。
年度周期仪式不仅通过社会时间的节奏安排来营造权力格局和文化认同的空间象征,而且还表述着特定历史意识。第一套仪式包含传统节日和新发明的“国庆”等节日。久而久之,在一般民众的感知中,这些仪式已转化成了“休息日”或“闲暇经济”。然而,在发明和运用的初始阶段,这些仪式明显带有一种展示民族历史的意味,它们实际上是在演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了近代的沧桑以后,在一个革命力量的集中领导下,走向文化复兴的历史过程。第二套仪式则存在着把泉州地方文化的历史推得越早越好的倾向,它们演示的是地方作为民族国家的细胞如何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一文化内涵又如何反映“地方特色”。在这个“地方特色”背后,其实还包含着对于泉州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唐、五代、宋元)的回顾,在这里泉州的特色不仅表现在文化的独特性方面,更重要地表现在地方史学者常常要去论证的一个旧有开放港市的黄金时代。这些仪式的实践,往往与吸引海外游客及华侨的访问为直接目的,而在口号上,经常宣扬要通过文化的演示来“让世界了解泉州,让泉州走向世界”。仪式的组织机构,显然也带有一种文化复兴的目的,但所要复兴的文化并非整个民族国家的传统,而是介于这个传统与地方中心的文化观之间的那种东西。第三套仪式也代表一种历史的观念,人们把自己安排的活动与特定的历史相联系,但这种历史对于整个民族或整个城市的自传式文化复兴史持淡漠的态度,而把关注点集中在与人的具体生活关系密切的家史和社区史上。其中家史可以推及古代英雄人物,但祭祀活动集中在“公妈”(即五代以内的祖先)上;社区史则随着地方神(当地称“铺境佛”)及其庙宇的历史推及明代以至明代之前的历史阶段。
从本质上说,年度周期仪式就是历史、文化与权力的结合,或者说是不同的权力通过选择历史来选择文化的结果。从三套仪式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国家的周期仪式选择的是民族起源、革命、建国和振兴的历史观念,地方政府组织的仪式选择的历史集中在地方文化的繁荣时代,而民间文化的仪式则趋近于家庭与地缘性社区发展的明清史。
如果说历史只是一个时间流动的社会过程,那么,为什么不同的权力类型会选择不同的历史?对这个问题,我做了初步的解释。我指出,作为历史的再度演示的仪式,服务于对未来的阐释,它们所要论证的是,如何从历史的过去推导出命运的未来。因而,国家的仪式试图推导的,就是一个民族从历史的黑暗中走向光明未来的命运;地方政府的仪式,是为了从过去的繁荣推导出未来的繁荣;民间的仪式则试图在家和社区的延续中,寻求家和个人命运的未来安宁。这也就是说,仪式中的历史大致都是在对过去的虚构中想象未来的产物。不过,这一点绝对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历史真相”,因为正是在“历史的真实”这个蓝本上,各种仪式的历史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效力。
从仪式研究中我认识到,仪式本身是特定权力(如国家、地方精英、民间家庭与个人)通过想象历史来想象自身的认同的渠道;同时,没有历史的蓝本,任何权力的文化想象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是历史的蓝本决定了文化想象的方式和内容。考察三套仪式,可以发现,无论是官方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带有悲壮的意味。民族的文化振兴、地方古代繁荣时期的复归、家庭与社区的安宁,这些通过热闹而喜悦的仪式表现出来的期待,背后都有各自的悲壮。国家的仪式是自其发明之日起才通过政权和传播媒介与地方社会和家庭形成关系的,它们代表的历史截取了“中华民族”历史最早和最迟的两个阶段。诸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大抵形成于汉代前后,是当时的朝廷依据先秦时期民间风俗改造而成的节日;而诸如国庆节等新式节日则庆祝一个“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族国家的成立,其历史仅有数十年。截取这样的历史阶段来构成一个仪式周期,体现的是一个国家象征地克服近代以来内外交困的“民族悲剧”的历史的努力。这个努力是在超地方的场合中展开的,但因为它针对的对象,也一度影响了地方社会的秩序,所以其地方的相关性也时常得到强调。地方政府组织的艺术节之类的仪式,截取的历史阶段是古代泉州的一段辉煌过去。其实,这一段历史时期早已在明清时期内部的政治压制和外部的冲击下消失了。但在仪式的象征表现中,它还是被看成“活着的过去”,似乎泉州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也正在复兴其过去的繁荣。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执行者而言,长期以来受到政权和上层社会蔑视的民间仪式,无非是肤浅的“封建迷信”的反映。对于实践这些仪式的一般民众而言,仪式的历史久远性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历史性,与家庭和社区的密不可分性。这些仪式除了与全国的传统节庆对应的节日之外,内容上大多属于家庭的祖先崇拜和地方神崇拜。这些崇拜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但在实际内容上则与明清时期得到大幅度发展的“铺境佛”信仰和家族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考察,很难看到这三套仪式之间的分立状况。人们可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单位、电视、报纸等等来实践国家的年度周期仪式,同时也可能在闲暇时间里观看地方文化管理部门组织的“艺术节”,或者在家庭的空间内部举办祭祀活动。然而,如果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三套仪式归结为官方仪式和民间仪式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它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互相指责的关系。急于把民心统一到民族国家振兴事业上来的政府机构和地方精英,把那些分散于家庭和地域性社区、分散于祖先和地方神身上的仪式活动看作“现代化的障碍”,是现代文化以前的“文化残余”。可是,对于把关注点主要放在整体的、超家庭的民族国家利益和象征上的官方仪式,民间却时常表现出淡漠的态度,似乎这些东西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祖先和地方神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保护者。
官方仪式与民间仪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的特定文化表现。不过,问题可能还需在历史深处追根溯源:如果没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那么,作为代理民族振兴事务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便不可能有理由给自己人民的文化加上一个“封建迷信”的绰号;同样地,如果没有现代民族国家那种在外来压力下急于“现代化”的动力,那么民间也就不可能感到个人、家庭、社区利益所应付出的代价,也就不可能那么严重地关切自身文化延续的需要。然而,即使把问题追溯到近代世界格局的冲击,我们也无法完全证明,这就是新兴国家与民间文化之间张力的根源。事实上,国家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张力在任何存在权力分化的历史时期和社会中都存在,而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国家力量向来强大而能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度来说,“大小传统”的张力,并不新鲜。
我从泉州年度周期仪式所能想到的,首先是历史、文化与权力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交织、互动和冲突;其次,这种历史、文化与权力的交织、互动和冲突,受一定的历史过程的限定,而这个历史过程绝对不是一般想象中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本身的流动,而是家庭、地方社会、国家与更大空间范围中的世界之间的权力和文化的不断互动的流动。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流动为当今的仪式性活动和其他类型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历史的意义,也正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流动依然制约着正在与历史形成断裂关系的生活。从仪式中的历史、文化与权力,向历史中的历史、文化与权力转向,使我们能够把被反思的历史(如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放在经验的历史中反思,也能够把经验中的历史与被反思的历史相联系,从而使我们的历史理解真正趋近历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