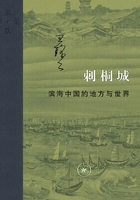
致谢
我之所以可能将对泉州城市史的业余爱好化作这项我界定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是因为得到过一些学术前辈的教导和帮助。我在厦门大学学习过考古学、人类学及民族史,其间,除了聆听各位老师的课之外,还得到过庄为玑、陈国强、蒋炳钊、叶文程、吴绵吉、李家添、苏垂昌、辛土成等老师的悉心指导。我从庄、叶、苏诸先生的泉州考古学研究中获益良多,从陈、蒋、辛先生的东南民族史志研究中,得到诸多教益,其中,庄先生的教导尤有启发,他出版后即赠予的著作《晋江新志》(泉州: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印行)、《古刺桐港》(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集半个世纪的研究之功而写成,一直是我理解泉州的导引和主要依据。
我于1987年赴英留学,受益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David Parkin、Stuart Thompson等老师讲授的课程和给予的指导及师友Stephan Feuchtwang教授的私交。本书显然是对“无历史”的英国人类学的一项批判,但它的一部分基础却是我向这些国外老师学到的知识、方法和理论。本书明显是我给国内外老师上交的一份作业。作业是交出去了,但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并无法穷尽国内外的老师们传递的知识(尤其是对国内老师教给我的东南考古、民族史没有充分把握,对国外老师教给我的民族志和比较文化研究未能充分领悟),而需要继续回味老师们的教导,反复思索到底我能从这些教导中综合出何种认识。
我曾在1985年从事短期的地方史文献调查,又曾于1989年起在泉州从事田野工作和地方史文献搜集。这些研习活动,是我写作本书所凭靠的基础。
在泉州研习过程中,我频繁就教于许多地方史研究前辈,包括陈泗东、傅金星、王连茂、吴幼雄、黄炳元、陈垂成、郑国权等,更从我的高中班主任陈日升老师那里得到了珍贵的鼓励、帮助和指导。此间,我也常与厦门大学郑振满、加拿大访问学者丁荷生(Kenneth Dean)等学兄相见,得益于其言谈与论著。
1996年之后,我与老一辈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先生成为忘年之交,相互之间有过多次对话和交谈,我也阅读了他的许多作品。萨林斯从文化理论研究和南太平洋历史民族志研究中引申出的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对宇宙观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诠释,对我的这项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虽并不完全同意他那种过于强调结构稳定性的观点,却大大受益于他的结构—历史看法。
本书原稿,经汪维玲女士善意组稿、审校,于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写作本书初稿的过程中,曾带着第9章所采用的文献,就教北大中文系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夫妇,后来夏教授不惜费心费时订正了我在文本点校上的错误,令我感动。
从初版之时算起,17个年头过去了,个人学术兴趣随时间推移而产生了变化,我在研究上对西部民族学更加关注,未能继续我的东南研究,丧失了继续阅读、学习众多地方文史与民族志的机会。不过,细想后我却发现,这些年来,自己还是频繁出没于泉州。除了回家办事,没少去参加和组织学术会议,更没少带着学友前往“访古”。国外学友方面,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之外,2007年以来,弗吉尼亚大学的Frederick Damon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的Michael Rowlands教授,多次同游泉州城乡地区。此间, Frederick的区域研究旨趣,从美拉尼西亚转向了泉州,而本来研究非洲的Michael,也对中国研究产生了兴趣,他们多次参与我们的考察和研习活动,给予我不少帮助和启发。2008年我也带萨林斯先生和他太太同去,在泉州参观了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及一些古迹,萨林斯先生感叹说,“这里的文物,足以颠覆西方人写的世界史”,令我十分喜悦。国内我先是带学生去调研,后也邀约汪晖、和少英、石硕、霍巍、杨正文、渠敬东、周飞舟等等学友,到泉州参会讨论、访问古迹。从他们有关帝国与区域、东南与西南、经与史的言谈中,我学到了很多。
在出没于泉州期间,我有不少机会同一些前辈和老朋友相聚,如师友王连茂先生及同学王珊等。去年在泉州考察期间,我到文庙拜见陈日升老师,在其办公室偶遇多年未见的几位前辈,其中有杨清江、林胜利等先生,他们仍在披阅古籍、谈天说地,士大夫风采依旧;我还随一位友人去拜见吴幼雄先生,他已满头银发,但依旧言必学问。这些情景让我难以忘怀。过去十多年,我在泉州也一直得到一些新朋友的帮助,如泉州的陈健鹰、丁毓玲、张明、连真、吴翠蓉、陈敏红、蔡颖等,安溪的谢文哲等,他们各异的成就让我向往,友情让我难忘。
在本书再版过程中,舒炜、冯金红两位朋友,给予难得的鼓励和帮助,而他们的不弃,更让我心存感激。
作者,2016年7月于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