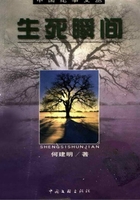
第3章
“我……我要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为新世纪祖国建设而读书!”李骏终于激动地掉泪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真的进了大学,而且在代表复旦万余名大学生向祖国倾诉衷肠。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刊出了李骏在复旦校园的大幅照片,这回“状元”真的露脸了。
李骏的“状元”没白当。但像他这么幸运的人毕竟不多。赵永均就比李骏的命运差多了。
赵永均在内蒙古赤峰老家的那块地方,成绩也是响当当的。方圆几十里,哪听说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而且是名牌大学。
可赵永均那天到南京的东南大学报捌时他好心酸。
场面好热闹,他赵永均长这么大还真是头回见:如期的汽车,如潮的人流……赵永均开始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后来反应过来都是家长们成群成队来送新生报到来的!乖乖,车真好!那学生的后面简直是个“运输大队”呀!喷喷,不知哪十地方来的娇小姐,跟爸妈分手时还来个吻别!
好奇。新鲜。目不暇接……但等赵永均清醒过来,他猛然发现自己与这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看看,人家也是新生,却在父母和亲人们的簇拥下各个像进宫殿的小皇帝鄢样趾高气扬,而我赵永均孤单单地穿着一身皱巴也的衣服,手拎两只塑辩旧包,整个就像“流浪汉”,充其量也是被人看作“打工仔”。他顿时脸上火辣辣的,慌乱地低下那颡从不轻易低下的头,像做什么错事似地靠着路边走。兴许因为只顾盯着自己的脚尖而没有注意前面,他突然猛撞了一个与他同年龄的新生。那新生娇滴滴地尖叫了一声,于是旁边的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定是做母亲的,狠狠地朝赵永均白r一眼:“走路怎么不看人哪’”说完,那女人拉起自己的宝贝大学生远远地躲开赵永均,嘴里嘀咕道:“怎么大学里还让叫花子进来吗?”这话赵永均听得清清楚楚,他顿时全身像被触电似地僵在那儿……许久,他那颤动的手不自觉地伸到口袋里没错,是与别人一样的入学通知书!赵永均仿佛一下有了救命的力气,他看看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的人流,张开嘴巴就喊:“我不是叫花于,我也是大学生!”
可他发觉怎么也喊不出声,只有那苦涩的泪像决堤的潮水涌出眼眶……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的这副行当寒酸吗!不就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护送着跟来报到吗!我父母……赵永均一想起在大草原上的父母,再也没了想喊的力气。
赵永均忘不r那天在接到入学通知书后的情景。
“妈、爸,我被东南大学录取了!”赵永均最先把入学通知书给了妈看,然后又绐继父。他想这回得让辛辛苦苦好几年供自己--学的父母大人好好高兴高兴,但却半天不见老两口说一句好听的,继父干脆长叹一声后背着手出门去了。
母亲更怪,躲到一边竞抹起眼泪来。
赵永均一愣,问:“妈你咋啦?”
母亲抬起泪眼说:“孩子,家里哪付得起那么多钱呀!”
儿子听这话,才明白了一一切。父母是被入学通知书上的四千多块学杂费给闹的。赵永均低下方才还是那样骄傲的头颅,泪水一下溢满了眼眶,但他倔强地投让它流出来。他轻声地说道:“我知道这……”
赵永均确实知道父母在哀叹中没有说出的苦处与难处。6岁那年,赵永均的生父去世,当时母亲一个人带着连他在内四个小孩,最大的还不能帮她干活,最小的才剐刚会走路,日子过得非常苦。许多年后,继父才走进了赵永均家。在这片贫困的草原与山丘组成的边远乡村,人们祖辈过着以放牧养畜为生、自给自足的部落式生活,交通的闭塞、信息的落后等等客观条件制约,即便你守着一座金山又能怎样呢?何况赵永均知道自己家连像样的几匹马都没有,家人的生活每年都有三四个月的短缺。如果不是他自己咬着牙坚持上完小学上初中,上完初中又上高中‘他早该跟人去远山相媳妇去了。赵永均心里明白,在他家乡,在他家里,像他这样一门心思想上学的人,除自己想法子外,不会有其它办法。至于家里,能不拖你后腿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第二天开始,赵永均就开妈自己想辙。
他赶了几十里路,先到了乡政府,人家告诉他乡里没地方拿山这笔钱,再说也不能补你一个人。看着人家根本没把他这个“状元”放在眼里,他发誓再不进这衙门。
他还是采用了像上高中时的老办法——上亲朋好友那儿借。
“你怎么老借没见还呀?”朋友早巳生气了。
“我、我不是刚高中毕业嘛。”赵永均每逢此时,总觉自己的底气特不足。
“那就赶快上山里圈个草场啥的,要不出山上南方打工挣大钱去嘛!”
“我都去不了……”
“咋?”
“我考上大学了。”
“嘿你小于,有出息啦!”
“所以想借些钱……”
“多少?”
“学费共四千多块,你看着给借吧。”
“唉!这一借是没个期限啦!”朋友长叹一声,拿出500块钱,“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咱山哩兄弟呀!”
“不会。谢谢了。”
赵永均又跑到亲戚家。
“伯伯、伯母好。我考上大学了,想借……”赵永均刚说到这儿,伯伯、伯母就把门一关,里面传出一句难听的话:“咱家又没菩萨,以后别老来!”
赵永均“扑通”双膝跪下:“伯伯、伯母就是菩萨,侄儿我给你们磕头了……”于是,他的额上留下一片红肿与泥块。
门“吱嘎”一声终于沉重地打开,“苦命的弦子,我们也是投法呀!”
“侄儿知道。等我上完大学了,‘定加倍偿还。”
“你就别嘴上说好听的了,上高中时你不也说过类似的话。”
赵永均顿时无言。
就这样,赵永均用了整整将近…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到亲戚朋友那儿借得了他认为可以上路的钱,于开学报名前来到南……在97级同班同学中,他路程最远,却没有一个家人送他上学,为此他悄悄流过泪。
(赵永均现在是东南大学大二学生。他说学校大概看他独立能力强,一进校就让他当班长。他因上学欠一万多元债款,没让家人知道,学校也不清楚。现在他圭要靠假期打工解决学费和生活问题,日子过得仍极艰难。)今年4月,我到上海采访的第一个学校是华东理工大学,这个学校是上海几十所高校中贫困生最多的一所。学生工作部的老师特意给我介绍了该校化学专业的曾祥德同学。
在我面前坐着的这位瘦小的同学身上,看不到一点点在东方大都市上学的那种特有的上簿大学生风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蛮新的罩衣和很旧的球鞋,以及低着头、搓着手说话的情态,一看便明白地告诉你这是个“山里娃”。
只有知识和语言属于这位著名大学的学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读大学一年多,设上街出去过。只有在香港回归那天学校组织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就回来了。”曾样德同学说。
“老师说你是(19)95年考上大学的,怎么你现在才是96级生呢?”
“我考上大学后整晚了一年才有学籍的。”他说。
“为什么?”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没有钱,我就出去打工,给耽误了。”
“那——你当时没怕失去学籍?那样不就遗憾终身吗!”
“我当然知道。可……当时什么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时,两眼泪汪汪。
“能给我说说吗?”我轻轻端过杯中水,怕触痛他的伤痕。
曾祥德同学稳了稳神,说:“可以。”
下面是他的话: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区,全家6口人,种4亩地,丰年时够吃,能卖点农作物换些抽盐酱醋的现钱,一到灾年就有四五个月靠东借西挪过日子,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一般初中毕业就休学了,不是在家干家活,就到外地打工。我6岁上学,同时也开始帮人家干活。8岁时就能挑水、打猪草.10岁便能下地与大人一起干农恬。父亲在一家窑厂帮活,后来弄伤了身体,花了不少钱,家里因此欠了很多债。中学毕业后,父母让我去广东打工,说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该为家挣钱了。我没听,因为我心里有个“大学梦”,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样结局了。我在家里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挣钱了。家里就剩我是主劳力。记得读高二时,父亲正巧在农忙时把脚扭伤了不能下地,母亲本来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个人干,十四五岁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宝贝儿,可我们不行,不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还得挑起全家生活与劳作的重任。那12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个人又是收割,又是播种。乡亲们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还能说出个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们说二娃将来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披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录取。爸妈对我上大学并不怎么高兴.他们觉得上大学还不如去广东打工。说你上大学四年,一分不能为家里赚钱,还要一年花几千元的学费,这里外里,四年家里要损失多少?就说大学好,可以后毕业了还说不准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还得去打工吗?所以劝我别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穷山沟沟里十几年上学你不知有多苦!我绝对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可是总不能两手空空去上学呀!入学通知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学费和学杂费几项加起来得四千多块!上哪儿弄出这么多钱?亲戚朋友也没富人,自个儿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当时我真觉得走投无路。父母毕竟心疼儿子,晟后悄悄把家里惟一的一头耕牛给卖了。当我从他们手里接过那几百块钱时,我就有自己上大学是一种罪过的感觉。可几百元的耕牛钱与几千元学赞之间还差远着呢!不得已,我流泪告别家人,踏上了漫长而遥远的打工攒学费的艰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车,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选择这儿是希望舅舅能帮我一把,因为我必须在一个多月之内把四千多元的学杂费挣到手。结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里就凉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第二个老婆。那女的太厉害,舅舅干什么事都得看她的脸色。我这么一个外乡人突然进了她的家,吃着住着,她哪会有好脸色嘛!投几天,我已经觉得再不能在舅舅家果了,便决定搬出来。舅舅好心,背着舅娘给我弄了辆三轮板车,说永安城内交通不便,你有个板车可以拉点话能养话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着自己的舅舅,可叉能说什么呢?后来我租了一间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仅够我躺下伸直。住定后,我就开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筑工地搅拌水泥,后来又卖菜。可永安是个小市,啥都不是那么景气,于啥都赚不了大钱。我很着急,超着急则越不灵,人生地不熟的,好挣钱的活也轮不到我呀。于是我又做起收破烂的活,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起床,一直串巷走街到天黑。就这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月,人家说省吃俭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头来也才挣了1400元。这时已到开学的时间了,我原本认为出来打工一两个月就能把学杂费挣回来,然而我千里颠沛、受尽苦雉,仍然计划落空了。当我在永安街头收破烂时见到人家扔下的报纸上说全国的大学已经全部开学时,我呆呆地坐在大街上欲哭无泪……一些新开学的小学生从我身边走过扔下几个“可乐”瓶,说:“收破烂的,送你吧!”然后哈哈哈大笑着走了。我当时真想告诉他们,别搞错了,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学生!可我说得出口吗?说了又有谁信呢?我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继续迈着沉重的步子,凄凉地沿街吆喝着:“有破烂卖喔——!”我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吆喝声,因为我心中仍然编织着“大学梦”。
12月8日,当我怀捕三千元钱,来到上海,找蓟貔心巾久已向往的华东理工大学时,老师惋惜地告诉我由于来得太晚,他们不能再准许我注册入学。我一听差点当场晕倒,好在后来他们说可以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有这话就行,我就开始在学校餐饮服务公司打工,但x有人不让干了,说学校有规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学校打工。我好伤心,因为从情理上我也该算是学校的人呀!无奈,我把三千元钱存在学校的储蓄所,又开始了漫长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门的那一瞬间,我回头向学校默默地说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学……”
1996年9月,曾祥德如愿以偿,成了华东理工大学的正式学牛。只是这一程,他走得太艰难太漫长。其实,在每年近百万的新生中,像他这样的又何止一个!与此同时,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当他们历尽心酸迈进大学门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一个又—个不曾想到的沟谷与坎坷啊……不过比起另一些同学,曾祥德仍算是幸运者。
1998年初,北方重镇沈阳闹市区的街头,突然连续冒出一群从贵州山区来的少男少女在沿街乞讨,引起了不同一般的围观者——“真口丁怜,考上了大学还念不起书。唉!”
“得,把我这下岗翦的最后一次工资也捐给你们吧!”
“谢谢叔叔伯伯、阿姨婶婶们的菩萨心……”
捐助者与受助者这一幕幕场最无不催人泪下。一位退休老工人甚至义务招呼过往的人群:“都过来看一看这些苦孩子们,让我们一起拉他们一把吧!救一个大学生就是为国家植一根建设栋梁呀!”听着这样的鼓动词谁还忍心匆匆离去?
看一眼吧:天,现今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善鏖的沈阳居民们想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她(他)们下岗失业者更苦的人。快看,这些孩子也就十七八岁,胸前一个个挂着一块用硬纸做的牌,那纸牌上是叫人揪心的“乞文”:“我是一个处于山穷水尽的贵州山区农村的学生,很荣幸在1996年考中黔东南州民族师范学院,学制三年,每年要交学费1800元。由于家庭经济来源很差,加上弟弟去年也考上大学,父母只好去富裕人家借钱。在进校的一年里,全靠贷款度日……去年夏季,我家乡受到有史以来的特大水灾,洪水无情地冲走了我家的三间木房和所有财产,如今家中一贫如洗。为了保证弟弟上大学,我只好以泪洗面,沿街乞讨,惟望各位同情者伸出友谊之手,死难相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掏吧,不救这样的孩子救谁!沈阳市民纷纷解囊……但没过几日,报纸上披露一则惊人的消息,原来这些沿街乞讨的少男少女,是个假冒“贫困大学生”的诈骗集团,共31人,全都来自贵州山区。她(他)们在一位叫王勇的人指使下,一路行骗至沈阳。现今这31人中除2人外逃,全部被公安部门关押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