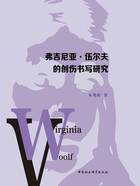
导论
第一节 伍尔夫生平与创作述略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现代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散文家。她生长在伦敦的一个文学世家,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祖父詹姆斯·斯蒂芬(James Stephen)爵士是一名睿智和有才干的行政官员,崇尚文学艺术。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是著名的传记作家、编辑、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博学多才。母亲朱莉亚(Julia)来自高贵的帕特尔家族,颇有文化修养。父亲广泛结交当时的艺术名流,与文坛大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交情甚笃,家里常常成为文人墨客聚集的地方。这种浓烈的文学氛围深深地惠泽着幼小而聪敏的弗吉尼亚。5岁时,她就每晚给父亲讲一个故事,还用她那可爱的小手写了一封信。囿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观念,弗吉尼亚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却有充分的自由徜徉于父亲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在这里,她自学完了英国文学,还阅读了柏拉图(Plato)、斯宾诺莎(Spinoza)、休谟(Hume)等人的哲学著作。1891年,弗吉尼亚与兄弟姐妹们创办了家庭刊物《海德公园门新闻周刊》。1901年,她进入伦敦帝王学院主修希腊语和历史。1904年,父亲逝世,弗吉尼亚随家人从肯辛顿的海德公园门迁居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通过在剑桥大学上学的哥哥索比,每周四晚,弗吉尼亚参加剑桥学子们举行的聚会,和他们在家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逐渐地,家里形成了具有最前卫、最敏锐的审美观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这样一个文化艺术中心。随着影响的扩大,它吸引了一群最具智性的人物,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作家爱·摩·福斯特(E.M.Foster)、哲学家乔·爱·摩尔(J.E.Moore)……1906年,索比(Thoby)病逝,弗吉尼亚接替哥哥主持周四晚会,在谈话中表现得越来越大胆、活跃,有“布鲁姆斯伯里皇后”之称。她与其他成员一起质疑传统,反对定规,追求自由,推崇精神美,探索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同时,她承担起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写书评的工作,显示出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优秀品质。
1912年,弗吉尼亚与剑桥才子,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结为夫妻,改随夫姓。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写出了许多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1917年,夫妻俩创办了霍加斯出版社,出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艾略特(T.S.Elio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等著名作家以及弗吉尼亚本人的作品。出版社不仅为弗吉尼亚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出版社的办公室成了青年作家们的聚集地,为伍尔夫夫妇赢得了一个朋友圈子。
童年时代,来自两个同母异父兄长的性侵犯,严重损害了弗吉尼亚的心理健康,再加上她生性细腻、敏感,导致了后来的神经错乱。1895年母亲的去世,给她以巨大的打击,第一次精神病发作。1897年,异父姐姐斯特拉(Stella)突然夭折。1904年,父亲离世,她又一次精神失常,跳窗自杀未遂。1906年,哥哥索比病逝。“一战”时期,不时传来亲友死于战场的消息,她为此痛心不已。“二战”期间,德国飞机轰炸伦敦,伍尔夫夫妇的住宅也没能逃脱厄运。弗吉尼亚·伍尔夫超常焦虑,预感到自己又要发疯了。1941年3月28日,她给丈夫和妹妹留下永别信,衣袋里塞满石头,自沉于乌斯河中。
伍尔夫创作有9部长篇小说和1卷短篇小说集,是欧美现代小说的开拓者,意识流小说的先锋作家。1915年,处女作《远航》问世。1919年,发表了第二部小说《夜与日》。这两部作品在整体上被认为是传统型的,有传统的故事情节,并且按时间顺序发展,还有生动细致的人物形象。但在《远航》中,已经体现出作者反叛传统写作、探索新的小说艺术的趋向。从标题到内容,小说都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还充满了人物的种种感受和瞬间印象,传统的作品情节被打乱,情绪、感觉和气氛成为重要的结构因素。短篇小说《邱园记事》(1919)与《墙上的斑点》(1919)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尝试,它们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情节与叙事,强调外界事物给人的印象与感受,着意于人物对外部世界的主观反应,表现出作者新颖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成功的实验之作。《雅各的房间》(1922)是伍尔夫第一部长篇意识流小说,仍保留着传统小说的故事因素,但只是框架性的,没有了情节,却充满人物的意识断片。《达洛维太太》(1925)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扛鼎之作,标志着伍尔夫个人风格的成熟完美,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1927年,伍尔夫又推出了长篇力作《到灯塔去》,它也是意识流小说的典范。作品以“窗”、“时光流逝”和“灯塔”三部分再现了女作者本人的童年生活以及父母双亲的形象,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富于象征意义的结构形式,通过多元视角塑造而成的立体多姿的主人公形象,如行云流水般的诗化语言,都是小说突出的艺术成就。它们一起承载着伍尔夫对生死、爱情、人性、宇宙等宏大问题的思索,体现出她对人生意义的探求,表达了她渴望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和谐社会到来的个人乌托邦理想。小说具有浓厚的哲理、象征意味和诗意美,其复杂性超过了作者此前的任何一部作品。
完成《到灯塔去》之后,伍尔夫感到自己过于紧张,有必要写些轻松的东西,于是写下了《奥兰多》(1928)。作品描述的是同名主人公由风度翩翩的少年变成女子的故事,充满了逗乐与幻想色彩,是伍尔夫意识流创作中的插曲。《海浪》(1931)是伍尔夫对意识流小说的又一种全新的尝试。正文内容全部由人物的内心独白组成,没有框架,没有情节,现实主义的因素被彻底抛弃。全书冠以“某某说”的形式,记录了6个主人公从童年到老年的心路历程,体现出作者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切思考和体悟。《岁月》(1937)是一部历史小说,叙述帕吉特家族几代人的生活,涉及了从1880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探讨了许多社会历史、政治问题。小说采用了传统的题材与框架,有回归现实主义的一面;但又有探索性的一面,通过采用诗化、散文化的叙述方式表达作者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幕间》是伍尔夫于1940年写成的小说,也是她最后的小说,还没有修改完,她就自杀了。作品讲述的是1939年6月的一天发生在英格兰中部一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村庄里的故事。作者设置了两条线索,一条叙述拉特鲁布(Trube)女士指挥村民演出露天历史剧的故事,另一条叙述奥利弗(Oliver)一家的故事。两条线索交错而行,构成错综复杂的图景。作者用这种方法把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艺术与人生、舞台戏剧与人生戏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艺术手法上,伍尔夫综合了她以前先锋派的倾向与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倾向,将意识流技巧与小说、诗歌、戏剧的表现手法融为一体。
可见,伍尔夫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一方面执着于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尝试,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学进行反复的掂量,终其一生都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徘徊不定,然而又会取得周期性的突破。她凭借非常自觉的文学意识与锲而不舍的革新精神,为发展20世纪小说艺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愧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
除了小说上的成就,伍尔夫还写有350多篇文艺随笔,是重要的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她的散文创作贯穿于她的整个文学生涯,分为以下集子:《普通读者》(一、二)、《瞬间集》、《飞蛾之死》、《船长临终时》、《花岗岩与彩虹》、《现代作家》、《三枚旧金币》、《自己的一间屋》、《书和画像》。伍尔夫的现代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现代小说》(1919)、《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1924)、《小说的艺术》、《狭窄的艺术之桥》等文章中。她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在批判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小说的“内心真实观”。她认为,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新的题材需要新的表现手段,旧的小说形式已不能反映当今现实,因此,英国小说应该摆脱传统的创作模式;现代小说的创作基础是人物的灵魂而非肉体,是人物的主观感受而非外部客观事物,小说家应该深入人物的心灵世界,表现纷纭复杂的意识活动;作家只有充分反映人物复杂的心理结构,抓住人物的内在真实,小说才显得真实可信,才能真正反映出生活的真实。第二,她提出了“透视方法”,即多角度的叙述方法。她认为,传统的小说创作采用作者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作者的视线集中于外部事件,只能表现客观真实;小说家应该采用多焦点的透视法,透过多个人物的视角来表现主观真实。第三,伍尔夫提出了“诗化小说”的理论,认为未来小说应该是一种融会了诗歌、戏剧、散文等因素的综合艺术形式,而要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必须通过“非个人化”途径。伍尔夫在多部小说创作中成功地实践了她的上述理论。伍尔夫还非常关注妇女问题,她从自身经验出发,在创作中呼吁女性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男女平等。《自己的一间屋》(1929)是体现伍尔夫女性意识和女权思想的重要论著,被后来的女权者们奉为女权主义宣言,也奠定了伍尔夫女权主义领袖的地位。
纵观伍尔夫的人生历程,不容否定的是,创伤,几乎伴随了她的全部生涯。她从小容貌姣好,然而,6岁那年,便开始遭受两位同母异父兄长的性骚扰,一直延续到22岁。她的挚爱亲友,他们却或因疾病,或因战争陆续离她而去。她自幼聪敏好学,却未能像家里的男孩一样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她热衷写作,却发现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自己书写的历史。她热爱和平,追求和谐,所耳闻目睹和感同身受的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暴虐。家的梦魇,死亡的阴影,世俗的偏见,战争的残酷,让伍尔夫伤痕累累,以致神经衰弱、精神崩溃,多次发作精神病。
伍尔夫的一生,也是从事文学写作、追求文学艺术的一生。5岁时,她便表现出创作的天赋。临死前,她还在书桌上留下了未完成的作品《安农》的草稿。她成果丰硕,成绩斐然,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优秀的作家总是无可避免地会从自身体验出发,在其创作中书写生活,充分地表达自身对生活与人生的感悟与思考。那么,精神创伤作为伍尔夫人生经历的重要一分子,与她的文学创作必定存在着关联。精神创伤对其文学创作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怎样的体现?反之,文学创作对其精神状态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