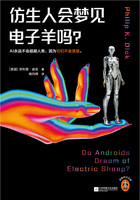
第2章
床头的情绪调节器通过自动警报系统送出一股欢快的小电流,唤醒了里克·德卡德。他吓了一跳——突然被弄醒总会吓他一跳——身穿五彩睡衣从床上起来,站着伸了个懒腰。他妻子伊兰在她的床上睁开灰色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没有任何快乐,她眨眨眼,然后呻吟一声,重新闭上眼睛。
“你的潘菲尔德设得太弱了,”他对妻子说,“我来重设一下,等你醒来就会——”
“你别碰我的设定。”她的声音尖锐而刺耳,“我不想醒。”
他在她身旁坐下,俯身看着妻子,轻声解释:“把电流设得足够高,你就会庆幸自己能醒来,这就是它的原理。设到C挡,它能打破不让你恢复意识的一切障碍,反正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他感觉很好——为了应付外部世界,他设置了D挡——亲昵地拍了拍她露在外面的苍白肩膀。
“该死的警察,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伊兰说。
“我不是警察。”此刻他感到自己很容易生气,尽管他的设定里没有暴躁。
“你比那些警察还坏,”他妻子说,依然闭着眼睛,“你是警察雇用的杀手。”
“我这辈子从没杀过人。”他的气恼已经上升到了直接的敌意。
伊兰说:“对,你只杀可怜的仿生人。”
“但是我发现,我带回家的赏金,你花起来可从来不犹豫,天晓得你在你那些心血来潮的爱好上烧了多少钱。”他起身,走向他的情绪调节器的控制台。“可就是不肯存钱,”他说,“否则咱们可以买一只真羊,换掉楼上的那只电子假羊。我努力往上爬了这么多年,挣的钱却只够养一只电子动物。”他在控制台前犹豫了,不确定该拨什么号码,是抑制丘脑(能消除愤怒的情绪)还是刺激丘脑(能把他变得足够可憎,从而在争吵中获胜)。
“要是你把恶意往高里调,”伊兰已经睁开眼睛,望着他的一举一动,“那我也一样往高里调。我会调到最高,然后咱们可以闹得不可开交,相比之下,以前吵的那些架什么都不是。你尽管去调,看看谁怕谁。”她飞快地爬起来,跳到她的情绪调节器的控制台前,目光炯炯地瞪着他,等待他的反应。
他叹了口气,在她的威胁面前认输了。“我还是按我今天的日程表调参数吧。”他查了查1992年1月3日的日程表,发现今天需要的是公事公办的专业人士态度。“要是我按日程表调节情绪,”他警惕地说,“你能同意也这么做吗?”他等待妻子的回答,他相当谨慎,不会在妻子同意前确定自己的参数。
“我今天的日程表上是六个小时的自责和抑郁。”伊兰说。
“什么?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个?”这完全违背了情绪调节器的设计目的。“我甚至不知道还能这么设置。”他烦闷地说。
“一天下午,我坐在家里,”伊兰说,“当然正在看《老友巴斯特和他友善的好友们》,他正在说他有个重大新闻要告诉大家,然后那个恶心的广告突然插进来,就是我特别讨厌的那个,你知道的,江河郎中[2]铅护裆。于是有那么一分钟,我干脆调了静音。然后我听见了建筑物——这座建筑物的声音,我听见了……”她打了个手势。
“许多空荡荡的公寓房间。”里克说。有时候夜里应该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听见它们的声音。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一座公寓楼有一半住户,就已经算是人口密度很高了。在战前的城郊居住区,很多建筑物从上到下连一个人都没有……反正他是这么听说的。这种信息他只想要二手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对亲身体验不感兴趣。
“我把电视调为静音的那一刻,”伊兰说,“恰好处于382号情绪中——我刚拨出这个号码。因此,尽管我理智上听见了空虚,但我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它。我的第一反应是谢天谢地,我们买得起潘菲尔德的情绪调节器。不过后来我意识到这个状态很不健康:感觉到生命的缺失——不仅是在这座楼里,而是在所有地方,但对比毫无反应。你明白吗?我猜你不明白。总之这个状态曾经被视为精神疾病的症状,人们称这种疾病为‘适当情绪缺失症’。于是我让电视继续静音,正对着情绪调节器坐下,开始做实验。最后我找到了设置绝望的方法。”她原先忧郁精致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就好像她实现了什么伟大的目标:“于是我把它放在我的日程表里,一个月两次。我认为这么长的时间很合理,因为我需要感觉绝望——对一切的绝望,对所有聪明人都已经移民而我还留在地球上的绝望。你觉得怎么样?”
“但是像这样的情绪,”里克说,“会让你沉迷其中,忘记用机器把自己拉出来。像那样对现实的绝望,是不会自己停止的。”
“我设定了三小时后自动重置情绪,”妻子回答得很流畅,“481状态。能认识到未来有无数的可能性在等待我,怀着新的希望——”
“我知道481是什么。”他打断妻子的话头。他设定过许多次这个组合,他对481状态的依赖性很强。“听我说,”他在床边坐下,握住妻子的双手,拉着她在身旁坐下,“就算设定了自动切断,但无论如何,体验抑郁还是非常危险。别管你的日程表了,我也忘记我今天的安排,咱们一起设个104,好好享受一下,然后你保留这个状态,我调回工作需要的一贯态度。这样的话,我会想要爬上屋顶看一眼羊,然后去办公室。与此同时我会知道你不是坐在家里发呆,连电视都不开。”他松开妻子修长纤细的手指,穿过宽敞的公寓,来到还能依稀闻到昨晚的烟味的客厅。他弯腰打开电视。
伊兰的声音从卧室传来:“我受不了在早餐前看电视。”
“拨888,”里克说,等待电视机预热,“无论电视里演什么都想看下去。”
“我这会儿什么都不想拨。”伊兰说。
“那就拨个3。”他说。
“我为什么要刺激我的大脑皮层,让我想要调整情绪?我说了我不想拨号,我最不想拨的就是这个号,因为只要拨了它,我就会想要拨号,而现在我最不想要的就是拨号的欲望。我只想坐在床上,盯着地板发呆。”她的声音变得尖锐,透露出一丝沮丧的意味,而她的灵魂已经凝结,身体停止移动,难以抗拒的惰性落在她的身上,就像一张无所不在的沉重巨网。
他调大电视的音量,老友巴斯特洪亮的声音充满了房间:“嗬,嗬,伙计们。现在来简单说说今天的天气。猫鼬卫星报告说,放射尘在接近中午时格外严重,之后逐渐减轻,因此非要冒着危险出门的伙计们,你——”
她出现在他身旁,长睡袍像轻烟似的拖在背后。伊兰伸手关掉电视:“好吧,我投降,我拨。你要我拨什么都行,忘乎所以的性高潮?……我的心情太差,连这个都能忍受。管他的。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去给咱俩拨号。”里克说,领着她回到卧室。他在她的控制台上拨了594——在所有事情上欣然接受丈夫的超凡智慧。他在自己的控制台上拨了工作需要的锐意进取,不过他其实并不需要,这本来就是他习惯成自然的态度,有没有潘菲尔德大脑刺激科技的帮助都一样。
……
三下五除二吃完早餐——与妻子拌嘴耽搁了他宝贵的时间——他穿上冒险外出所需的各种行头,其中包括埃阿斯级的江河郎中铅护裆,然后上楼去屋顶的天棚草坪看他的电子羊“吃草”。这台精密的机器正在啃青草,伪装出来的满足表情骗过了楼里的其他住户。
当然了,其他住户的动物有一些无疑也是电子赝品。他从不去打探这种秘密,就像他的邻居们也从来不会打探他的羊到底是不是真东西。那是最没礼貌的行为。比起问别人的牙齿、头发或内脏器官是不是原装的,问“你的羊是真的吗?”甚至更加失礼。
晨间的灰色空气遮蔽了太阳,裹挟着放射性尘埃,在他周围喷涌,刺激着他的鼻子。他不由自主地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好吧,这么说似乎有点儿言过其实了,他心想,并走向一块特定的草皮,这块草皮和楼下那套大得不相称的公寓一样,都是他的财产。尘埃是终末大战的遗产,放射性已经变弱。没能熬过来的人多年前就灰飞烟灭了。而对现在这些强壮的幸存者来说,变弱后的尘埃只能干扰一下神智和遗传特性了。尽管他穿了铅护裆,但毫无疑问,尘埃还是会渗入他的身体,他一天不移民,积累的尘埃就会给他一天的辐射污染。到目前为止,月度体检都说他一切正常,还是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繁衍后代的人。然而,旧金山警察局的医生随时有可能会在某个月得出相反的结论。放射性尘埃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把正常人改造成特异人。最近甚嚣尘上的新口号是“要么移民,要么退化!你自己的选择!”,海报、电视广告和政府垃圾邮件里全都在这么嚷嚷。话当然是大实话,里克心想,同时打开小牧场的铁门,走向他的电子羊。但我不能移民,他在心里说,因为我的工作。
隔壁牧场的主人和他打招呼,那是他的邻居比尔·巴伯。他和里克一样,也是一身工作装,同样在上班的路上顺便看一眼宠物。
“我的马怀孕了,”巴伯兴高采烈地指着高大的佩尔什马说,它站在那儿,茫然地望着虚无,“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有两匹马了。”里克说。他已经走到了他的羊身旁。它卧在地上反刍,机警地盯着他,希望他带来了燕麦片。这只假羊有个针对燕麦的激励线路,只要看见燕麦片,就会一骨碌爬起来,慢悠悠地走向他,整套动作既真实又可信。“这只母马怀上了谁的种?”他问巴伯,“过堂风吗?”
“我买到了全加州最优质的公马精液,”巴伯答道,“通过我在州畜牧管理委员会的内部关系。记得上周他们的检查员来这儿检查朱迪的情况吧?他们急着想要它的马驹呢。它是一匹无与伦比的好马。”巴伯亲昵地拍了拍马的脖子,它把脑袋贴在他肩上。
“没考虑过卖掉你的马吗?”里克问。老天在上,他太想拥有一匹马了——事实上,任何动物都行。拥有和养护假动物会让你越来越沮丧,然而从社交的立场说,在搞不到真动物的情况下,你也只能用假动物来充数。他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养下去。就算他本人不在乎,也必须为了妻子着想,伊兰很在乎——在乎得不得了。
巴伯说:“卖马?那是不道德的。”
“那就把马驹卖掉。养两只动物比不养更不道德。”
巴伯困惑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养两只动物,甚至三只、四只,更何况还有弗雷德·沃什伯恩这样的人,他是我弟弟工作的海藻处理厂的老板,他有五只呢。你没看昨天的《纪事报》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的是他的鸭子。据说那是西海岸最重和最大的红面鸭。”他眼神呆滞地说着,想象着能拥有这么一只动物的美妙景象,渐渐坠入了恍惚状态。
里克从外套口袋里翻出《西德尼兽禽目录》的一月增刊,这本书他看了无数遍,已经皱皱巴巴的了。他在索引里查到“马驹”(见马,后代),不一会儿就知道了全国指导价。“我能用五千美元从西德尼公司买到一匹佩尔什马驹。”他大声说道。
“不,买不到,”巴伯说,“你仔细看价目表,那是用斜体印的。意思是他们没有库存,假如有库存,那就是这个价。”
“要么这样,”里克说,“我一个月付你五百美元,连续十个月。按目录里的全价。”
巴伯怜悯地说:“德卡德,你对马一无所知。西德尼没有佩尔什马驹的库存是有原因的。没人会出售佩尔什马驹——哪怕是按目录的价格。它们太稀少了,哪怕是相对较差的那些也一样。”他趴在两人之间的围栏上,用手势加强语气:“我养朱迪已经三年了,这么多年来,我从没见过它这个品质的佩尔什母马。为了买它,我专程飞到加拿大,然后亲自开车把它运回来,以确保它不会在路上被劫走。要是带着这么一只动物出现在科罗拉多或怀俄明附近,他们会为了得到它而干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终末大战之前,曾经有过成百上千——”
“但是,”里克打断他,“你都快有两匹马了,而我却一匹也没有,这违反了默瑟教的基础神学和道德架构。”
“你不是有你的羊吗?妈的,你可以走你自己人生中的登山小道,等你抓住共情箱的两个把手,就能无限接近荣光了。要是你没有那只羊,我还能在你的话里找到一点儿逻辑。是的,假如我有两只动物,而你一只都没有,那我就是在阻碍你和默瑟的真正融合。但这座楼里的每一户人家——我算一算,差不多五十户,要是我没算错,每三套公寓有一户住人——咱们每一户都有一只动物,种类是另一码事。格雷夫森有他的鸡。”他往北指了指。“奥克斯和他老婆有条红毛大狗,一到夜里就叫唤。”他沉思片刻,“我记得埃德·史密斯的公寓里有只猫——至少他是这么说的,但没人见过。也许他只是假装有。”
里克走到羊的身旁跪下,在厚实的白色羊毛里摸索——至少羊毛是真东西——终于找到了他在找的东西:机器羊的控制面板。巴伯眼看着他掀开盖子,露出面板上的元件。“看见了吗?”他对巴伯说,“现在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想要你的马驹了吧?”
巴伯愣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怜的家伙。所以它一直是假的吗?”
“不,”里克说,重新合上电子羊控制面板的盖子,他站起来,转身面对他的邻居,“我以前有一只真羊,我岳父移民的时候送给我们的。差不多一年前——还记得我带它去看兽医的那次吗?那天早上你也在上面,我出来时发现它侧躺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你把它扶起来了,”巴伯说,点点头,表示他想起来了,“对,你把它扶起来了,但它走了一两分钟,就又倒下了。”
里克说:“羊会得各种怪病。或者换个说法,羊会得各种各样的疾病,但症状总是一样的。羊爬不起来了,但你不可能知道情况究竟有多严重,是仅仅扭伤了腿,还是快要死于破伤风了。我的羊就是因为这个死的,破伤风。”
“在这儿?”巴伯说,“屋顶上?”
“草料,”里克解释道,“那次我没有把铁丝从草料里择干净,留下了一小段,结果格劳乔——我的羊就叫这个名字——被钩破了皮肤,就这么感染了破伤风。我带它去看兽医,它死了,我想来想去,最后找了一家制造仿真动物的商店,给他们看格劳乔的照片。他们造了这东西。”他指了指卧在地上的假羊,它还在专注地反刍,警觉地盯着他,等待燕麦的出现。“做得以假乱真。我花在照顾它上的时间和心思不比以前少。但是……”他耸耸肩。
“毕竟不一样。”巴伯替他说完。
“不过也很接近。照顾它的时候,感觉没什么区别。你必须时刻关注它,和你对待真动物的态度一样。因为它们会出故障,到时候楼里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已经送修了六次,都是小毛病,但要是被人看见——比方说有一次,音带坏了,要么就是被污染了,总之它不停地咩咩叫——人们肯定会认为这是机械故障的原因。”他继续道,“修理店的卡车当然标着‘宠物诊所’之类的东西,司机打扮成兽医,穿着白大褂像模像样。”他突然想到打卡的时间,于是看了一眼手表。“我要去上班了,”他对巴伯说,“咱们今晚见。”
他走向车子,巴伯急忙在他背后喊道:“呃,我不会对楼里的其他人乱说的。”
里克停下脚步,正想说谢谢,但就在这时,他感受到了伊兰所描述过的那种绝望,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说:“我也说不准,也许不会有什么区别。”
“但他们会看不起你的。不是所有人,但有些人肯定会。你知道人们怎么看待不养宠物的人,他们会认为你道德沦丧还反对共情。明白吗?尽管现在不像终末大战刚结束时那样,把它算成犯罪行为,但人们还是会对你有看法。”
“上帝啊,”里克无奈地摊了摊手,“我也想养宠物,我一直在找门路买一只。但光是靠我这么一个市政雇员的薪水……”希望我在工作中能再走运一次,他心想。就像两年前那次,我一个月灭了四个仿生人。他心想,要是我当时就知道格劳乔很快会死……但那时候羊还没得破伤风,那时候那一截状如针头的两英寸[3]铁丝还没有从草料里冒出来。
“你可以买一只猫,”巴伯建议道,“猫毕竟便宜,你查一查《西德尼兽禽目录》。”
里克平静地说:“我不想要家养的宠物。我想要我原来的那种大动物。一只羊,要是我能搞到钱,那就养奶牛或公牛犊,或者像你一样:养一匹马。”他算了算,干掉五个仿生人的赏金应该就够了。一个仿生人一千美元,而且是薪水之外的收入。然后我肯定能在某个地方找到某个人,搞到我昼思夜想的东西,就算《西德尼兽禽目录》里的售价是斜体字。五千美元,他心想,但首先,必须得有五个仿生人从某个殖民星球来到地球。这一点不是我能控制的,我没法逼着五个仿生人来这儿,即便我能做到,世界各地还有其他警务机构麾下的其他赏金猎人呢。这五个仿生人必须在北加州住下,而这个区域的高级赏金猎人戴夫·霍尔登必须去世或退休。
“买一只蟋蟀吧,”巴伯打趣道,“或者老鼠。对了,只需要二十五美元,你就能买一只成年鼠。”
里克说:“你的马也会死,就像格劳乔一样,毫无预兆地横死。今晚你下班回到家里,会发现它躺在地上,四脚朝天,就像一只死虫子。就像你说的,一只蟋蟀。”他大步向前走,车钥匙握在手里。
“对不起,我大概伤害了你的感情。”巴伯紧张地说。
里克·德卡德沉默不语,猛地拉开悬浮车的车门。他已经没有话要对这位邻居说了,他的心思全放在工作上,全放在接下来的这一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