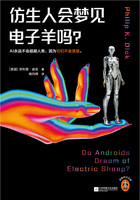
第3章
这座衰败的巨大建筑一度容纳过成千上万人,如今空空荡荡。楼里有一台电视机正在向无人居住的房间兜售商品。
终末大战之前,这片无主的废墟有人照看和维护。此处曾经是旧金山的城郊居住区,从这里乘坐单轨电车很快就能抵达市区。整个半岛就像一棵落满小鸟的大树,叽叽喳喳地充满了生命、看法和抱怨,在乎这个地方的那些业主现在不是死了,就是移民去了殖民星球。前者占大多数。尽管五角大楼和它趾高气扬的智库兰德公司做出了乐观的预测,但那场战争的代价异常高昂。事实上,兰德公司就离这儿不远。与大楼的业主们一样,这家公司也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似乎是永久性的。没人怀念它。
更有甚者,如今没人记得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也没人知道获胜的是谁或有没有人获胜。污染了全地球的放射性尘埃并非来自任何国家,也没有谁——哪怕是战争中的敌方——蓄意制造了它们。最初,猫头鹰怪异地死去。当时人们还觉得挺滑稽的,这些胖乎乎、毛茸茸的白鸟东一只西一只地死在院子里和街道上,而猫头鹰本不会在黄昏前飞出巢穴,因此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死的。中世纪的瘟疫也曾以类似的方式现身,其载体是无数的死老鼠。这次瘟疫却是从天而降的。
继猫头鹰之后,其他鸟类自然也步其后尘,但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已经掌握并理解了其中的奥秘。战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外星殖民计划已经启动,但现在,由于阳光不再照耀地球,殖民就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为了适应这个计划,科学家改造出一种名为“人造自由斗士”的战争武器。这种人形机器人——严格地说,叫有机仿生人——能在外星球上活动劳作,因此就成了外星殖民计划的基础劳动力。联合国的法律规定,每个移民都会分配到一个仿生人,具体亚型由移民决定。就这样,到了1990年,仿生人的亚型已经多得不可思议,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汽车。
移民的推动力最终就是这么构成的:仿生人奴仆是胡萝卜,放射性落尘是大棒。联合国让移民变得简单,让留下变得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在地球上逗留意味着你随时会被突然打上异类的标签:你在生物学上变得不可接受,对人类这个物种的遗传纯正性形成威胁。一旦被列为特异人,即便主动接受绝育手术,也会泯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就结果而言,这个人从此就不是人类的一分子了。然而即便如此,地球上也还是有人拒绝移民。至于原因,就算是这些人本身,也无法用理性解释。从逻辑上说,每个正常人应该都已经移民了。也许是因为,尽管地球已经被毁掉了,但它依然是我们熟悉的家园,受到我们的眷恋。也有可能,不肯移民的顽固分子梦想着漫天尘埃总有一天会自己消散。总而言之,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留在地球上,他们大部分聚集在城市地区,在那里,他们能看见彼此的肉身,从他人的存在中得到安慰。他们算是神智相对正常的个体。然而除了他们,另外还有一些可疑的怪异个体,他们拒绝离开事实上已经荒弃的城郊居住区。
约翰·伊西多尔,客厅电视机喋喋不休的训话对象,此刻正在卫生间里刮脸,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在战后初期一路流浪来到了这个地方。那是个糟糕的时代,没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人们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到处游荡,一时间在一个地方暂时栖身,一时间又去往另一个地方。放射性落尘当时是零散分布的,而且极为多变,有几个州几乎完全没有,还有几个州近乎饱和。人们就像浮萍,随着尘埃移动。旧金山南面的半岛起初没有落尘,于是大量人口在那里安顿下来。后来等尘埃到来,一些人死去,其他人离开,而约翰·伊西多尔留了下来。
电视机在喊叫:“……重现了内战前南方各州的安闲时光!定制的人形机器人可以是贴身仆人,也可以是不知疲倦的农场帮工,专为您和您独一无二的需求而打造,在您抵达目的地时交付,完全免费,装备齐全,您只需要在离开地球前提交规格就行。这个忠诚的伙伴完全用不着您操心,将在现代人类历史最伟大、最勇敢的开拓征程中提供……”它没完没了地唠叨。
不知道上班会不会迟到,伊西多尔一边刮胡子一边心想。他没有还能走的钟表,平时全靠电视报时过日子,但今天显然是太空开拓节。电视里说今天是火星上最大的美国人聚居地新亚美利加成立五(还是六?)周年。他的电视有故障,只能收到一个频道,这个频道在战争期间被国有化了,现在依然如此。华盛顿政府出于殖民计划而成为它唯一的赞助商,因此只能它播什么,伊西多尔就听什么。
“咱们来听听玛吉·克卢格曼太太怎么说,”电视播音员对约翰·伊西多尔说,尽管伊西多尔只想知道现在几点了,“克卢格曼太太刚移民到火星,以下是她在新纽约接受采访的现场录音。克卢格曼太太,你从被污染的地球来到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新世界,你认为在两者上的生活有什么区别?”片刻停顿之后,一个疲惫而冰冷的中年女性声音传来:“我认为我们一家三口首先注意到的是尊严。”“尊严,克卢格曼太太?”播音员问。“是的,”如今家住火星新纽约的克卢格曼太太说,“很难解释清楚。在这个困顿的时代,有个仆人可以依赖……我感到安心。”
“以前在地球上,克卢格曼太太,你是不是也担心有一天会被划为,咳咳,特异人?”
“天哪,我丈夫和我都快要担心死了。当然了,移民之后,这个担忧就消失了,谢天谢地,永远也不需要担心了。”
约翰·伊西多尔在心里酸溜溜地说,我的这个担忧也消失了呢,而且还不需要移民。他被划为特异人已经一年多了,不仅是因为他携带的变异基因。更糟糕的是,他没能通过智力基准测试,因此成了俗称的“鸡脑子”。压在他身上的蔑视足有三颗星球那么重。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活了下来。他有一份工作,是为假动物维修公司驾驶接送车辆。范内斯宠物医院和他阴郁的哥特风老板汉尼拔·斯洛特当他是个人类,他对此颇为感激。正如斯洛特先生偶尔会说的“Mors certa, vita incerta.”[4],尽管伊西多尔听到过很多次这句话,但对它的意思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毕竟,要是一个鸡脑子懂拉丁语,他也就不是鸡脑子了。他向斯洛特先生指出这个事实的时候,斯洛特先生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世上有的是比伊西多尔蠢笨的鸡脑子,他们根本不可能工作,只能待在所谓“美国特异职业技能学院”的托管机构里,而“特异”二字能成为机构名称的一部分,当然是有它的原因的。
“……你的丈夫尽管拥有并持续穿昂贵而笨重的铅护裆,”电视播音员说,“却不觉得受到了保护,我说的对吗,克卢格曼太太?”
“我丈夫——”克鲁格曼太太答道,但就在这时,伊西多尔刮完脸,大步流星地回到客厅里,关掉了电视。
寂静。寂静从家具和墙壁里陡然涌出,以全面压制的可怕力量扑向他,像是来自一台庞大的轧钢机。寂静从地面升起,从铺满地面的破烂灰色地毯里冒出来。它从厨房里损坏和半损坏的电器里析出,自从伊西多尔住进来以后,这些机器就没有运转过。它从客厅里纯粹当摆设的落地灯里渗出来,从爬满苍蝇的天花板空虚而无言地悄然落下。事实上,它从他视线范围内的所有物体里同时浮现,就好像它(寂静)想要取代一切有形的事物。因此,它进攻的不但是他的耳朵,还有他的眼睛。他站在关掉的电视机旁,体验到的寂静不但是可见的,而且具有它自己的某种生命力。它是活的!他常常能感觉到它的肃然逼近,寂静降临时,它会毫不掩饰、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笼罩这个世界的寂静无法控制它的贪婪——它再也控制不住了,特别是现在,事实上它已经胜利了。
于是他心想,不知道还留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会不会以这种方式体验虚无,还是说它仅仅对应于他特定的生物身份,是他受损的感觉器官产生的怪诞体验?一个有趣的问题,伊西多尔心想。但他能去和谁讨论呢?这座颓败的建筑物里有一千套无人居住的公寓,只住了他一个人,与它的无数同类一样,这栋楼每天都在熵增中走向衰亡。楼里的所有事物迟早会彼此融合,变得面目模糊、毫无二致,化作布丁一样的垃圾,从每一个房间的地板堆到天花板。在那以后,无人照管的建筑物本身也会倒塌,埋在无处不在的尘埃之下。当然到那时候,他早就死了,这是另一桩有趣的事件。他独自站在破败的客厅里,感受令人窒息、无孔不入、专横跋扈、笼罩全世界的寂静,期待着自己的死期。
也许还是开着电视比较好。但那些广告让他害怕,它们的投放对象是还留在地球上的正常人。它们用无数种方式告诉他,他这个特异人是不被需要的;他没有用处;就算他想移民,也不可能移民。所以为什么还要听呢?他气恼地问自己。让他们和他们的殖民大业都见鬼去吧。我衷心希望殖民地也爆发战争——毕竟从理论上说,这是有可能的——他们落到和地球一样的田地,而移民统统变成特异人。
好了,他心想,我要上班去了。他伸手抓住门把手,门外是没有灯的走廊,然而等他瞥见占据了楼里其他空间的虚无,就立刻缩了回去。那股力量埋伏在外面等他,他能感觉到它在处心积虑地渗入他这套公寓。上帝啊,他心想,又关上了门。他还没有做好踏上那些咣咣作响的台阶,爬向没有养动物的空旷屋顶的准备。他将只能听见自己往上走的回声——虚无的回声。现在该去握住把手了,他心想,接着穿过客厅,走向黑色的共情箱。
他打开机器,从电源涌出了熟悉的负离子气味。他急切地深吸一口气,已经陶醉了起来。阴极射线管随即亮了起来,就像仿制的、微弱的电视画面,一幅拼贴画渐渐浮现,由看似随机的色彩、线条和图案构成,在你握住把手之前,它不具有任何意义。他做了一次深呼吸来镇定情绪,然后才握住两个把手。
图像凝聚起来,他立刻看见了那个著名的场景。古老贫瘠的褐色山坡,枯骨般的杂草斜伸向昏暗无光的天空。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差不多像是人类,正在艰难地爬上山坡。这是个老人,他身穿朴素的暗色长袍,长袍几乎遮不住身体,薄得像是从充满敌意的虚无天空中抢来的。这个人,威尔伯·默瑟,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而随着约翰·伊西多尔握紧把手,他感觉到他所在的客厅逐渐消失,破旧的家具和墙壁像退潮似的散去,他很快就不再能够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了。他发现自己和以前一样,进入了刚才看见的场景:黄褐色的山坡,黄褐色的天空。与此同时,他也不再是看着老人爬上山坡的旁观者了。他的脚在与地面摩擦,在熟悉的碎石中寻找落足之处,他像先前一样感觉到不平整的粗糙地面硌痛了脚底,闻到了天空中雾霾刺鼻的气味——这不是地球的天空,而是某个遥远的陌生星球的,但通过共情箱的作用,他能够亲身体验到。
他的穿越和平时一样令人眩晕,他再次融合了威尔伯·默瑟的身体,并伴随着精神和心灵两方面的归一。此刻握住把手的其他人也是如此,无论他们在地球还是在某个殖民星球上。他体验到了其他人的存在,融入他们思绪构成的集合,在他的大脑里听见诸多个体发出的纷乱噪声。他们(还有他)只在乎一件事,精神融合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导向山坡本身、攀爬的动作和上山的欲望。这种欲望一点一点发展,缓慢得几乎难以觉察,但它确实存在。脚下的石子在往下滑,他心想,再高一些,我们今天比昨天更高,而明天……他,无数人复合构成的威尔伯·默瑟,抬起头眺望前方的登山小道。太远了,不可能看见尽头。但迟早会走到的。
一块石头扔向他,打中他的胳膊。他感觉到了疼痛。他侧过身子,与另一块石头擦肩而过,没有被打中。石头落在地上,发出的声音惊吓了他。是谁?他心想,眯起眼睛寻找攻击者。还是同样的敌人,在视野边缘隐约可见,它(或它们)跟着他一路爬到这儿,还会继续尾随他,直到山顶……
他回想起山顶的情形:山势突然拔高,爬山到此结束,下一个阶段开始。他体验过多少次了?已经记不清,过去和未来已经模糊,既有的体验和终将有的体验彼此融合,于是只剩下了此刻。此刻他站住了,正在休息,揉着胳膊上石块划破的伤口。上帝啊,他疲惫地心想。这一切的公平何在?我为什么要孤零零地来到这儿,被某些我连看都看不见的东西折磨?但紧接着,在他的意识里,融合中的其他所有人的喧闹打破了孤独的假象。
你们也感受到了,他心想。是的,那些声音在回答,我们的左胳膊挨了一石头,疼得要命。好的,他说,咱们还是继续爬吧。他重新抬起脚,其他所有人立刻跟上。
他记得以前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是诅咒降临前,是他更快乐的前一半人生。他的养父母弗兰克和科拉·默瑟发现一个充气橡皮救生筏载着他浮在水中,那是在新英格兰的海岸边……还是在墨西哥的坦皮科港附近?他已经不记得具体情况了。童年很美好,他热爱所有生命,尤其是动物,有一段时间甚至能让死去的动物活过来。他与兔子和昆虫生活在一起,既在地球上,也在殖民星球上,但其中的细节他同样不记得了。不过他记得那些残杀者,因为他们逮捕了他,说他是异能人,比其他特异人更特异。因此,一切都改变了。
当地法律禁止使用让死者复活的时间倒流术。他十六岁那年,他们向他阐明了这个规定。但他在残存的树林里又偷偷地施行了一年,直到一个他从没见过和听说过的老妇人举报了他。未经他父母的同意,他们(残杀者)用放射性钴破坏了他大脑里形成的独特结节,结果将他投入了另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而他从没想象过这个世界的存在。那是一个深渊,填满了尸体和骸骨,他挣扎了许多年,才从底下爬了上来。驴子和蟾蜍——尤其是蟾蜍——这两种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动物已经消失或灭绝,剩下的只有腐烂的碎尸:这儿一颗没眼睛的脑袋,那儿几根手指。最后,一只到那儿等死的鸟告诉了他那是什么地方。原来他坠入了坟墓世界。只要散落于他周围的骸骨不长出血肉,重新变成活生生的动物,他就不可能离开。他已经与其他生命的新陈代谢合而为一,在它们复活之前,他不可能独自复活。
他的那一段生命持续了多久?他现在并不知道。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因此时间变得无法度量。但终于,骸骨重新长出了血肉,填满了空荡荡的眼窝,新生的眼睛见到光明,与此同时,复原的长喙和嘴巴发出声音:嘎嘎、汪汪、喵喵。有可能是他的作为,也许他大脑里的超感官结节又长出来了。也可能不是他的功劳,非常有可能完全是个自然过程。总之他不再沉沦,他开始上升,与其他人一起上升。很久以前他就看不见他们了。他发现他显然是在单独爬山。但他们依然存在,他们依然伴随他左右。说来奇怪,他能在他的灵魂里感觉到他们。
伊西多尔站在他的公寓里,握着两个把手,在自我体验的同时也把其他一切活物囊括进自己的灵魂,然后他不情愿地松开了手。一如既往,这一切必须结束,再说胳膊被石头击中的地方也很疼,正在流血。
他松开把手,查看手臂,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向卫生间,去清洗伤口。这不是他第一次在与默瑟融合的时候受伤了,很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有不少人(尤其是老人)都死掉了,特别是后来到了山顶,等折磨真正开始之后。擦拭伤口的时候,他心想,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次熬过那一关。有可能会心脏骤停,还是省省吧,他心想,假如我住在城里,有医生拿着那什么电刺激机器守在一旁,倒是不妨一试。但我一个人住在这个鬼地方,那可就太冒险了。
不过他知道他会去冒这个险,就像以前一样,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哪怕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
他用纸巾吸干手臂上的水。
同时听见电视机发闷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楼里还有其他人,他的大脑疯狂地运转,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肯定不是我的电视机,我的电视机没开,而且我能感觉到地板在共振。声音来自楼下,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楼!
他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人了。又有一个人搬了进来,占据了另一套无人居住的房间,而且离我很近,近得我能听见他的声音。肯定是二层或三层,不可能更低了。要去看看吗?他的思绪在飞转。新邻居搬进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去拜访一下,借点儿东西,是这样吗?他想不起来了。这种事从没在他的身上发生过,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其他地方。人们搬走,人们移民,这是第一次有人搬进来。你可以拿点儿东西去送给他们,他决定了。比方说一杯水或牛奶,对,牛奶,或者面粉,甚至是一枚鸡蛋——更确切地说,鸡蛋的人造替代品。
他打开冰箱——压缩机早就罢工了——找到一块天晓得放了多久的人造黄油。他心潮澎湃,激动地拿着人造黄油走向底下的一层楼。我必须保持冷静,他心想,不能让他知道我是个鸡脑子。要是他发现我是鸡脑子,就不会和我说话了,事情总是这样的,天晓得为什么。我很想知道原因。
他沿着走廊快步走向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