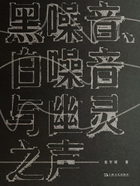
三、“节奏”与启蒙理想的音乐性
在卢梭那里,偏向人性与语言根源的旋律和偏向人为(“约定”)的技术形式的和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旋律与和声都旨在建立音乐的统一性,但旋律的统一性最终实现的是不同个体之间的真实“联结”,因而是至关重要的(49);而和声的统一至多只能实现音乐内部的形式秩序,因而仅仅是空洞而苍白的:“即使花上一千年的时间来计算音的关系和和声的法则,这一艺术又怎能转变为一种模仿的艺术?”(50)
对旋律在音乐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在音乐理论之中本来不存在太多争议。(51)难点在于和声。我们已经看到,当卢梭提出语言和音乐是“同时”诞生的论断、并从而将旋律在音乐中置于首要地位之时,他恰恰是要将自然与文化作为“同时”的维度(无论二者的关联怎样复杂难解)纳入到“起源”之处。旋律从根本上来说当然亦是声音,但它在起源之处就已经打上了语言的烙印,二者是难解难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反观和声,则显然不同。在和声及相关的调性体系之中,自然(声音)与文化(规则,约定)极为明显地处于分裂的关系。当代著名音乐哲学家布里安·K.艾特在其代表作《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西方音乐文化与秩序的形而上学》中一开始就围绕贯穿20世纪音乐史的新/旧、古/今、先锋/传统等等难解争端提出问题:“音乐是所有经过组织的声音?还是在一个特定传统中的艺术创造?”(52) 从自然本性上说,音乐当然就是声音及其种种“组织”形式,因而就是一个纯粹的、自足而自律的形式系统,而其他的种种“外部”的功能(表象、描绘、叙事、教化等等)都是衍生和附加的作用和效应。
不过,即便此种从达尔豪斯到基维的所谓“纯音乐”的立场向来占据着晚近音乐哲学的支配地位,但它显然无法对音乐本身的运动、变迁、发展的过程给出恰当而充分的阐释。根据此种立场,所有的音乐变革(比如从古典音乐向现代主义的变迁)归根结底都是偶然的,只是音乐体系内部形态的随机更迭而已。诚如索绪尔所言,就一个结构体系而言,历时性的联系只能是偶然性的。(53)确实有很多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音乐的调性“革命”:“西方的和声体系不是本来就有的东西,不是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新和弦’在被作曲家‘意外发现’后,就从‘潜在性’中脱离而成为现实。在这些‘新和弦’的周围,旧和弦仍然存在,是故和声之‘网’注定日益膨胀。音乐体系自身能够引发新奇性,这项能力不是通过与外部发生联系,而是源于其自己的本质。”(54) 显然,和声的自然本性和文化特征之间的关联只能是偶然的:选择何种调性体系,遵循何种和声规则,这都是作曲家的“意外发现”而已。而更进一步说,其实作曲家的地位也远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他亦只是和声体系内部从“潜在”的可能性到现实形态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
然而,这样一个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却恰恰缺乏历史的普遍性。换言之,将音乐视作一个纯粹的声音—乐音的系统这样的立场,本身就仅仅是西方音乐发展进入现代阶段的产物。艾特将形而上学史与音乐史相结合的思路固然别开生面,但毕竟最终落入基维所着力批判的“深层再现”的理论窠臼,因为他最终将调性体系视作宇宙秩序的“表现”或“隐喻”:“如果把调性体系看做具有内在潜能的存在,那么它就是目的论的一个隐喻。这就是说,调性体系既是宇宙本性自身的表现,也是世间万物之中美好事物的表现。”(55) 在某种意义上说,此种深层再现的立场的解释力甚至还远不及“纯音乐”学派。艾特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中对勋伯格的冗长阐释就是明证。对灵知学和神秘主义文本的大段援引反倒是让我们越来越疏离于勋伯格那本来宏大而深刻的音乐世界。将无调性和十二音仅仅当做个体生命的隐喻(绝望的感情生活)或时代状况的再现(传统目的论秩序的丧失导致了无序和迷惘),这些都难以打动用心的听者。
然而,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绝非简单的隐喻或再现,亦决不能仅仅作为某种形而上学体系的注脚。诚如阿多诺在其音乐哲学代表作《新音乐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1949)中所述,“个体与社会、作品的内在结构与外部条件”之间既非表象、更非从属,而理应是“断裂的关联”(fractured relationship)(56)。何为“断裂”?一方面它强调音乐体系的自律性这个起点(“真正的作品展现其真实内容,在一种时间的维度之中,通过它的形式法则,它超越了个体意识的范域”(57)),从而反对一开始就将音乐和社会的关系置于某种总体性的框架之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音乐的自律并不意味着全然的封闭性,而更是意味着它与外部社会之间存在着动态、开放而多元的关联。阿多诺以“规范”(convention)和“表达”(expression)这双重性的辩证运动来克服卢梭所陷入的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的窠臼。在卢梭看来,所谓历史无非自起源处的不断堕落,音乐亦是如此,越远离它和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原点,它也就越偏离了自己的生命本源。而根据阿多诺,真相则正相反:音乐的自然和文化这两个方面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彼此推动、转化乃至融汇的辩证关系。音乐的起源是异质的(heteronomy)(58),指向的是“非音乐的”(extramusical)(59)种种外部要素—尤其是那些与“姿势”(gestures)(作为肉体的“表达”)密切相关的戏剧、舞蹈等等。(60)此种起源处的异质和多元状态虽然随后逐步被音乐形式的倾向自律的纯粹化运动(“规范”)所遮蔽,但它们并非完全消失,而是作为潜在的“残余”(residual gestures)(61)仍然隐藏于纯粹音乐的形式之下(62):它是音乐得以向着外部开放,从而保持“断裂”关联的潜在缺口。正是因此,音乐的趋向规范化和形式化的运动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卢梭所谓的“语言化”倾向。从根本上来说,音乐的“逻辑”既不同于概念性的逻辑(“判断”),亦不同于语言的规则(“语法”)(63),而是一种“无判断的综合”(judgementless synthesis):“它全然自它的要素的星丛(constellation)之中构成自身,而非对这些要素进行述谓、统摄和包含。”(64)这也是为何音乐几乎可说是最具矛盾性的艺术形式:它的那种看似极端而纯粹的形式性总是让它不断沦为种种意识形态的附属和傀儡;但它内在的那种不可还原的差异性和异质性又总是蕴藏着“转化”(transfiguring)和“解体”(disintegration)的真正契机。
不过,他仍然以概念思辨为主导(黑格尔的幽灵)的思索和写作方式使得他难以真正揭示此种契机的真正机制及其与人类生存的内在关联。这或许亦是因为,卢梭和阿多诺实际上都忽视了音乐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节奏”(rhythm)。而与历时性的旋律和共时性的和声相比,节奏似乎更能体现出音乐内在的时间性维度,尤其是差异性维度。在20世纪的音乐理论和哲学之中,节奏和时间性之间的关联成为一个核心的主题,而其中的要点即是节奏和节拍(meters)之间的本质差异及关联。借用斯克鲁顿的精辟概括,节拍是对音乐的时间性运动的同质性度量和划分,而节奏则是此种运动本身。(65) 或借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敏锐洞见:“差异—而非产生差异的重复—才是节奏性的。”(66)简言之,正是在节奏这个充满原初差异的“内在性平面”之上(67),方才形成种种节拍的重复模式。诚如爵士乐大师温顿·马萨利斯所言:“现实的时间是一个恒量。你的节拍是一种感知。而摇摆的节拍是集体动作。爵士乐队的每个人都尽力创造出一个更灵活并能替代现实时间的节拍。”(68) 这不再是一个旋律或调性的统一性空间,而是一个节奏的“星群”,在其中,个体与个体之间最为真实地联结在一起。(69)这又何尝不是启蒙的理想?“新文化史”大师丹尼尔·罗什在浩瀚绚烂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中描述“启蒙运动之都”巴黎时曾深情写道:“城市本身就是个时光元素的组成体,是由人建构而成的。在城市里,时间镌刻在石头里,空间也因各种经历和活动而形态各异。”(70) 启蒙的空间,或许正是这样一种音乐性的空间,其中个体之间在多元开放的时空维度中自由互通。若果真如此,那么音乐,以及对音乐的哲学思索,或许会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未完成的启蒙理想的一个美妙途径。
(1) Terence E. Marshall, “Rousseau and Enlightenment”, in Political Theory, vol. 6, no. 4, Special Issue: Jean-Jacques Rousseau, Nov., 1978,pp.421-455.
(2) 同上,p. 431.
(3) 同上,p. 424.
(4) 同上,p. 424.
(5) 较早的关注如Eric Taylor的文章“Rousseau's Conception of Music”(in Music & Letters, vol. 30, no. 3, Jul., 1949, pp. 231-242)。而卢梭的音乐思想近年来激发出学者们越来越浓厚的研究兴趣。
(6) 马丁·杰:《阿多诺》,瞿铁鹏、张赛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7)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修订第3版,第31页。
(8) Christopher Bertram,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Rousseau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Routledge, 2004, p. 98.
(9)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20页。仅根据本文的语境将“代表”统一译作“表象”。下同。
(10) 他们援引的是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对“在场(presentment)/在场性(presentness)”的著名区分(译法取自《艺术与物性》中译本:张晓剑、沈语冰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前者仅指示一种事实性的状态,而后者则指向更深层的当下即永恒的时间性样态。无独有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同样将这一点作为其对卢梭的阐释的核心线索(尤见第二部分第三章)。德里达所重点依据的文本恰好是我们下文即将重点讨论的《论语言的起源》。
(11) C.N. Dugan &Tracy B. Strong, “Music, Politics, 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usseau, edited by Patrick Ri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p.331.
(12) C.N. Dugan & Tracy B. Strong, “Music, Politics, 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 p.332. 斜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13) “我们之所以有钦佩正直和厌恶邪恶之心,其根源在我们自身,而不是来自戏剧。没有任何一种舞台艺术能使我们产生这种心理;舞台艺术只能表演它。”(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7页。)这样的说法更妙:“只干巴巴地空流几滴眼泪,一点真情也没有。”(同上书,第48—49页。)
(14) “戏中的种种表演不仅没有缩短我们与剧中人的距离,反而使我们与他们远离。”(同上书,第50页。)
(15) “试图在戏剧中忠实地展现事物的真正关系,是办不到的,因为剧作家往往会改变这些关系,以迎合观众的口味。”(同上书,第52页。)实际上,在卢梭的笔下,封闭的剧院的场景与《理想国》中那幽暗洞穴的场景又是何等相似。这也是他更为赞颂那种在开放空间“上演”的生活“戏剧”的原因。由此他才会嘲讽达朗贝尔说:“你无疑是第一位公然撺掇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撺掇一个小城市,一个穷国耗资修建一座剧院的哲学家。”(同上书,第37页。)
(16) “舞台上情意绵绵的表演,将使我们陷入意志消沉的境地,……我们虽向往美德,但结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付诸实行。”(同上书,第90页。)
(17) “有些人以为一进了剧场,彼此就亲近了。然而,恰恰相反,人一进了剧场,就会忘记他的朋友,就会忘了他的邻人和亲人,只对剧中瞎编的情节感兴趣。”(同上书,第39页。)
(18) C.N. Dugan &Tracy B. Strong, “Music, Politics, 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 p.335.
(19) 卢梭:《起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另,从十二章到十九章后来又有吴克峰的译文:《卢梭论音乐》,《人民音乐》2012年第7期,第55—60页。
(20) 卢梭:《起源》,第22页。
(21) 同上书,第25页。
(22) 同上书,第22页。
(23) 从这个音乐与语言混沌未分的源头来看,正可以用卢梭所偏好的那个含混多义的词“voix”来描摹(第二章)。
(24) 卢梭:《起源》,第32页。同样,“在自然发展中,一切字母语言必然变化其特征,在获得清晰性的同时,它们丧失了力量”(同上书,第44页)。
(25) 这本不奇怪,因为卢梭的《起源》本来就是构想为《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的一部分。
(26) 卢梭:《起源》,第62—63页。
(27) 同上书,第53页。本文作者对译文有所修正。
(28) 同上书,第85页。
(29)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30) 卢梭:《起源》,第95页。
(31) 同上书,第92页。
(32) 同上书,第96页。
(33) 同上书,第100页。
(34) 彼得·基维:《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徐红媛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35) 卢梭:《起源》,第86页。旋律与语言的密切关联在《论法国音乐的信》(Lettre sur la musique française)中亦十分明显,那里卢梭区分了音乐的三要素:旋律、和声与小节(measure),而其中“小节之于旋律,恰似语法之于话语”(转引自 Eric Taylor,Rousseau's Conception of Music, p.235)。
(36) 卢梭:《起源》,第85页。楷体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37) 在卢梭提到所谓“纯器乐音乐”的寥寥数语中,要么将其起源归结为人声音乐(vocal music),但这并没有什么艺术史上的依据;要么就索性断言“纯器乐几乎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并没有表达语言文字”,参见Eric Taylor, Rousseau's Conception of Music,p. 241。
(38) 伊凡·休伊特:《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孙红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39) 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个时间不早于1755年(参见Downing A.Thomas, Music and the Origins of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84)。这个时期,古典主义虽然方兴未艾(莫扎特[1756—1791],海顿[1732—1809]),但巴洛克音乐(尤其是巴赫的那些纯器乐作品)的影响却仍然是巨大的。当然,按照休伊特的说法,音乐的真正独立是自18世纪(海顿和莫扎特的年代)逐渐开始,而巴赫的器乐作品仍然未彻底摆脱“社会功能”的附庸。
(40) C.N. Dugan & Tracy B. Strong, “Music, Politics, 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 p.349.
(41) 这两个说法转引自C.N. Dugan & Tracy B. Strong, “Music, Politics,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 p.345。就此点而言,德里达从“替代”和“补充”的角度来理解音乐的“摹仿”或“复制”就显得尤其不得要领(德里达:《论文字学》,第294—295页)。
(42) “音乐不直接表现这些事物,但它会在灵魂中激起亲眼看见这些景物时的同样的情感。”(卢梭:《起源》,第114页)
(43) C.N. Dugan & Tracy B. Strong, “Music, Politics, 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 p.350.
(44) 参见休伊特对西方古典音乐的五个基本特征的划分:《修补裂痕》第20—22页。
(45) 彼得·基维:《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第144页。
(46) 同上书,第84页。
(47) 卢梭:《起源》,第127页。
(48) “正如贝多芬在《庄严弥撒》的题献页上所作的表达—音乐可以径直地‘从心灵到心灵’。”(休伊特:《修补裂痕》,第17页。)
(49) “在我看来,旋律的统一性是一个必需的法则。”(卢梭:《论法国音乐的信》,转引自Eric Taylor, Rousseau's Conception of Music,p. 236。)
(50) 卢梭:《起源》,第100页。
(51)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是音乐的基础。……旋律将许多音乐基本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的统一体。”(李重光:《基本乐理简明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52) 布里安·K.艾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李晓东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6页。
(53) “历时事实是个别的;引起系统变动的事件不仅与系统无关,而且是孤立的,彼此不构成系统。”(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第136页。)
(54) 休伊特:《修补裂痕》,第59页。楷体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
(55) 布里安·K.艾特:《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第70页。结合西 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艾特细致缕述了调性体系的诞生如何呼应着从柏拉图的超越之善、经历莱布尼兹的兼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内在目的性、再到黑格尔的理想美的最高综合的运动过程。
(56) Max Paddison, “Authenticity and Failure in Adorno’s Aesthetics of Music”,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orno, edited by Tom Huh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99.
(57) 转引自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orno, edited by Tom Huhn,pp.202-203。
(58) Ibid, p.210.
(59) Ibid, p.209.
(60)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起源》的一开始,卢梭就明确将“动作”与“声音”对立起来,并将语言和音乐的起源最终归于后者。
(61)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orno, edited by Tom Huhn, p.209.
(62) “所谓最纯粹的形式(比如传统的音乐形式),甚至是它们那些最微小的程式化细节亦可以回溯至像舞蹈这样的内容。”(Adorno, Aesthetic Theory, translated by Robert Hullot-Kentor,Continuum, 2002, p.5)
(63) “虽然艺术作品既非概念性的,亦非判断性的,它们仍是有逻辑的。”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p.136).
(64) 转引自Andrew Bowie, “Adorno, Heidegger, and the Meaning of Music”,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orno, p.257。
(65) Roger Scruton, Understanding Music: Philosophy and Interpretation, Continuum, 2009, p.59.
(66)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拙译,上海书店2010年版,第447页。
(67) 同上书,第446页。
(68) 温顿·马萨利斯、杰夫瑞·C.沃尔德:《这就是爵士:马萨利斯音乐自述》,程水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69)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组成和声的方式。”(同上书,第47页。)
(70) 丹尼尔·罗什:《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杨亚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2页。托多罗夫在回顾、总结“启蒙的精神”时亦将政治空间的多元性作为一个关键特征(《启蒙的精神》,马利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