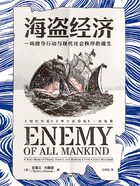
第二章
制造恐怖气氛
尼罗河三角洲·公元前1179年
在现代人眼中,哈布城拉美西斯三世陵庙西北门外墙上的象形文字宛若天书,当今,只有一小群埃及古物学家能够读懂。而印在陵庙墙上的浅浮雕图像却很容易辨识,它们描绘的是一场残忍的大屠杀:身着爱琴海地区重型盔甲的战士们一边手握投枪和匕首,一边用盾牌抵挡箭雨;敌方一名士兵倒下了,眼看一位戴埃及头盔的军官就要将其头颅砍下;血淋淋的尸体堆积成山,很明显,入侵方遭遇了惨败。这些图像及一旁的象形文字所展现的是古代的一场世界顶级海战,交战双方分别是埃及军队和一群四处游荡的强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上民族。历史上,拉美西斯三世所属的埃及王朝给我们留下了鲜活的印象,他们创造了拉美西斯三世陵庙和金字塔这样的考古奇迹,更有图坦卡蒙的宝藏,就连小学生都能随口讲两句法老的故事。而海上民族却没有留下这样的遗产,大体上是因为他们生命中的大多数宝贵时光都是在海上度过的。所以,他们死后3 000年并没有震惊世人的庙宇或是墓碑留存于世。他们没有开创新的农业形式,也没有什么哲学造诣,连任何文字形式的记录都没留下。不过,论起现代人对古代世界中这两类人的印象,海上民族的形象应该更突出一些,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是第一批海盗。
关于海上民族的地理起源问题,史学家们各持己见。主流观点认为,他们是来自希腊迈锡尼的难民,在青铜时代末期首次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文化群体。有的是士兵和雇佣兵,其余都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之前一直作为廉价(近乎奴隶工资的标准)的劳动力受雇去建造标志着迈锡尼鼎盛时期的大型基础设施与防御工事: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公路网或者皮洛斯的深水港口。所以,这一族群的起源必然是模糊的,因为“海上民族”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多民族的群体,就像后来的许多海盗族群一样,无法依据他们效忠哪个城邦或哪位君主来进行溯源,而是由他们选择效忠的已形成的漂泊部落决定的。地中海就是他们的家乡,海上的船就是他们的家。部落之间为了区分,都有着各自的风俗与规定:他们会戴不同的角盔——从拉美西斯三世陵庙那些浅浮雕图像就能明显地看出来——船上饰有鸟的头像。不过,最为与众不同的还是族群这种居无定所的性质,给人感觉他们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乡土,处于一种永远漂泊、永不扎根的状态。
这种无根性暗示着一种政治立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极端激进的海盗就会采用这一立场。对于环地中海陆地的当权机构,海上民族一向采取无视的态度,他们完全不受陆地国家法律的约束。这是海上民族用以向世人展现自己海盗身份起源的主要方式之一。海上民族出现之前,开阔的海域上无疑有海盗行为——其实,一旦人类开始用船运送值钱的货物,就一定会出现劫持船只、掠夺货物潜逃这种蓄谋性的犯罪行为。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海盗可不仅仅是像银行抢劫犯或者小毛贼那样类别的罪犯。在我们印象当中,大多数犯罪分子虽然做出了违法的行为,但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还是会遵守法律的。他们考取驾照、缴纳税款、投票选举,他们会把自己当作公民,只是不完全守法而已。然而,若换成真正的海盗,他们对法律制度的认可度就更低了。至于那些空间距离较远的国家或帝国当局,海盗是完全不予承认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如今小学生们眼中的海盗旗——数世纪前迎风飘扬,蕴含着如此丰富的象征性意义。海盗们会按照自己道上的规矩行事。“都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海上莽夫,”荷马在《奥德赛》中曾这样描述,“这些人活着就是为了鱼肉他人。”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海盗都会背叛自己的国家。(在亨利·埃夫里短暂的海盗生涯中,很多事都是他在公开叛国与忠君爱国之间左右为难才引发的。)不过,海盗们意欲触犯国家政权的法律与领土安全底线,更不用说他们痴迷于掠夺了,这使得他们经常成为集权当局的敌对方。海盗们行事灵活,且不受法律、道德与国家官僚机构的制约,所以,跟那些比他们强大的对手相比,他们具有诸多优势。然而,若集权政府真想对付他们,他们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公元前1179年,海上民族在尼罗河三角洲区域向拉美西斯军队发动了一次进攻。埃及国王已料到他们会这样做,事先建造了专门的战船,与海上民族精良的海上力量对抗。他部署了一个监视入侵船只的侦察网,并让这支新组建的船队埋伏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多条补给航道之外。从哈布城墙上的图像可以看出,海上民族的战舰里没有船桨,由此可见,他们遭遇了埋伏。这让人想起了诺曼底海滩上的那场血战:凌乱的船只横七竖八地散落在岸边,被海水冲刷着,船上的人正要往海里爬,结果被远处的埃及弓箭手一箭射中。那么多人都死在了浅水区。
终于,海上民族也领教了一次铁血军队的愤怒。“他们被人拖拽着,翻过来,平躺在海滩上;被屠杀之后,尸体从船头堆到船尾,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扔进了水里。”[1]拉美西斯三世陵庙的墙上写着这样的话语。“我们这位国王像一阵旋风一样,出来与他们交战,像驰骋在赛场上的运动员一样在战场上厮杀,”墓前其他的象形文字是,“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畏惧与恐惧,他们自食恶果——心被掏走,魂飞魄散。”[2]
铭文更具预见性,对此,当时刻下这些象形文字的人似乎早已意识到。海上民族在尼罗河三角洲遭遇溃败以后几乎一下子就从人类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至于他们最终的命运,专家们各持己见,就如同他们的起源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尼罗河三角洲之战以后,那些没被处决的人貌似流落到了埃及东部边境,其中一部分人流落到了巴勒斯坦海岸。不过,这群人一向是团结一致的群体,公元前1155年,拉美西斯在一次暗杀中遇害时,他们就彻底消失了。在这方面,海上民族树立了一种传统,被此后数世纪的很多海盗效仿。有些海盗红极一时,有些海盗被送上了绞刑架,而有些海盗则彻底消失了。
此外,海上民族留下了一项重要的传统,可以用它来定义埃夫里时代的海盗文化:对大规模暴力恐怖行动的战略部署。因受海上民族的围攻,乌加里特(今叙利亚境内)国王阿穆拉匹向塞浦路斯的另一位统治者发出一封紧急信函:“我的城市被烧毁了,(海上民族)在我的国家为非作歹……他们派来这里的七艘船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说到海上民族袭击海岸时的场景,拉美西斯三世陵庙的铭文也有过类似的描述:“瞬间,整片土地都淹没在战火之中……他们在阿莫尔的某个地方搭起了帐篷。人们四处逃窜,这片土地仿佛从未存在过。”
公元前13—前12世纪正是海上民族猖獗的时候,他们发动的极端残忍的杀戮对之前青铜时代繁华的地中海文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现如今,我们将之称为青铜时代末期的崩溃阶段,是历史上科技发展呈退步状态的几个时期之一。海上民族将希腊和黎凡特的海岸都城夷为平地之后,两地宏伟的宫殿文化分裂成了乡村文化,如同一盘散沙。如此一来,海上民族给他们与陆地社区之间的交流带来了世界末日般毁灭性的重创,从强度来讲,这种暴力近乎肆意妄为。海上民族入侵他国领土并非想据为己有,也不是为了把那里的财宝或人掠回本土。他们将青铜时代的众多宏伟都城付之一炬,只是为了目睹它们被焚毁而已。虽然他们不具备大陆敌方那样强大的军队和堡垒,但他们的战术是,巧妙地利用人的恐惧心理开展如今所谓的“非对称”战争,即以弱胜强的战争。[3]
从一开始,海盗这一行当就具备恐怖主义现代概念中的诸多关键特征,无论是从二者所引起的公众效应方面,还是从法律对二者的定义方面。英文中最早出现“恐怖主义”一词是在1795年詹姆斯·门罗[4]写给托马斯·杰斐逊[5]的一封信中,紧接着在美国大使写给法国大使的信中出现过。在罗伯斯庇尔[6]被处决一年后,门罗从巴黎寄出了一封信,信中提到雅各宾派又有了“恐怖主义行动与叛变的迹象”。[7]后来,这一术语迅速在美国政界精英圈中传开。继门罗信件之后,[8]仅仅过了几周,约翰·昆西·亚当斯[9]就在另一封信中将“罗伯斯庇尔政党的支持者”称作“恐怖分子”。
从某种程度上讲,恐怖主义是一种工具,也就是说,通过制造针对性的公众暴力事件来推进激进的政治观念,这既是恐怖主义最原始的利用价值,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手段。然而,恐怖主义在一个关键意义的层面上,原始意义与现代定义不再相符。20世纪之前,恐怖主义意识源自法国革命政府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及其他武装机构的行动。也就是说,当时的恐怖主义属于国家机器,是一种政治手段。直到一个世纪后无政府主义者出现,恐怖主义才与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概念联系了起来,它指的是一小撮群体,这类群体会象征性地与规模庞大的政府和军事力量对抗,常用的手段就是残害公民、引爆炸弹,进而扰乱公民的日常生活。罗伯斯庇尔的恐怖行径将具有国家专制性质的合法强制性行为演变为毁灭性的极端行为。这原本是统治政权用来巩固其震慑力的一种方式,而现代恐怖主义的作用则与此完全相反:它使得一小撮叛乱分子和黑暗势力网拥有与自己实力不成比例的影响力。非对称(当代很多军事冲突都具备这一性质)战争的整体概念——在这类战争中,其中一方为超强的政治实体,而与之对抗的敌方,无论是从人力还是从军事力量上讲,都不及其万分之一——其实源自恐怖主义性质的转变。现代的恐怖主义其实是一种影响力的放大器,不需要庞大的常备军或航母舰队就可以在百万民众中间营造摄人心魄的恐惧气氛。只需要安装好几颗炸弹,甚至美工刀都可以,再有一些甘愿为恐怖行动做大规模宣传的媒体网络。
虽然“恐怖主义”一词源自罗伯斯庇尔当政时期,但最初真正践行当代恐怖主义思想的人——诸如实施极端暴力的行为并通过媒体宣传制造强烈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海盗。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如下便是首例实证:通过一些怪诞的野蛮行径,一小撮人就可以有效地挟持一个国家,即1695年幻想号与莫卧儿载宝船之间发生的那场冲突。
当然,早在那次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之前就有类似的先例,这就要从传说中海上民族的那些暴行说起。他们那血腥的历史传统中,出现过这样一个先驱者,她是一名生于14世纪第一年的法国贵妇,名叫珍妮-路易丝·德贝尔维尔。英法百年战争中期,珍妮的第二任丈夫奥利维尔·德克利松因叛国罪被法国国王腓力六世处死,头颅被公开悬挂在布列塔尼地区的南特,离克利松宅邸不远的地方。国王的种种做法激怒了珍妮,为了报仇,她变卖田地、房产,召集了三艘战船,组建起一支小型舰队。为了营造气势,她把船涂成黑色,升起血红的船帆。相传,她潜行于英吉利海峡13年,在两个儿子的协助下,她袭击了数艘法国船,还手刃了腓力六世的支持者。她总会留下几名幸存者,好替她这头“布列塔尼母狮”给大陆传话。
通常,海盗在杀死敌人时给出的正当理由是“死人是不会泄密的”,这是海盗的行事准则,但对于像克利松(及其后人)这类海盗而言,这种说法却有着另一层含义:如果将那些人直接扔进海里,将无法扩大海盗嗜血与野蛮的名声。在所谓的海盗黄金时代,也就是继亨利·埃夫里之后的那一代海盗,他们的常规操作是这样的:将几名幸存者放生,好让他们回去跟人讲讲海上那些恐怖的事情。而生活在前谷登堡时代的“布列塔尼母狮”却只能通过宫廷内的谣言与私人信件向外界传达这些信息。埃夫里及其后辈则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体渠道为自己的暴行做宣传:小册子、报纸、杂志、图书。当时,这在欧洲及其美洲殖民地制造了诸多舆论。就连很多习俗(经常会让人联想到“小报”媒体)也是仓促写的,通常都是胡编乱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最初也是为了从亨利·埃夫里(还有18世纪初那些追随他的海盗)的一些谣传性事件中获利。如果说埃夫里的祖辈真的是像奥德修斯那样的传奇水手,那么在他职业生涯的鼎盛时期,他的存在还预示着另一种传奇人物的出现:通过古怪的犯罪行为吸引一整个国家注意力的杀手,就像约翰·韦恩·盖西[10]、山姆之子[11],以及查尔斯·曼森[12]那样。
我们总以为启蒙运动时期那些撰写小册子的人和早期的记者都是清高的知识分子,在斯特兰德附近的咖啡馆为《尚流》杂志撰写诙谐幽默的新闻素材。然而,在印刷媒体形成初期,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就已经萦绕在人们耳边了。有进取心的出版商会专门针对原始犯罪中那些吸引人的病态细节以及公开处决事件进行一番特别的抨击报道。早在首个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成名之前的近两个世纪,撰写小册子的人就已经开始大肆渲染暴力犯罪事件,进而赚到了快钱。没有哪类罪犯能比海盗更能引起大众的兴趣。
就如今针对最极端的连环杀手的描述来看,其手段的残酷程度不及这一时期媒体报道中的海盗。据说,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罗诺亚的法籍海盗“用手中的弯刀将其中一名俘虏的身体剖开,活生生地把心脏摘出来啃,再扔到另一名俘虏的脸上”。[13]一家名为《美洲水星周刊》的殖民地初期时的报纸转载了一篇有关英国海盗爱德华·罗的报道,尤其令人咋舌:报道中说,商船船长把一小包金子扔进海里,罗就“把船长的嘴唇割下来,当着船长的面烤熟,随后,他又将32名船员全部杀掉”。后来的一个版本[14](跟现代有关汉尼拔·莱克特的小说差不多)是这样描述的,这个疯狂的海盗把船长的嘴唇烤熟之后,又逼着船长吃掉。
为了让故事大卖,很多情节都是被夸大了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庭审记录的确对海盗的暴行有所记载。这类出版物,通常在递交判决结果之后的几天内便可印刷出来,开了媒体放大丑闻性庭审案影响力的先河。这类出版物中,有一段最令人震惊的描述,是关于“布里斯托尔杰恩船长”的,此人因虐待、杀害一名十几岁的船上侍者而被判刑,据说,那孩子只是从他的住处偷了一点儿朗姆酒。出版物的书名叫《残忍至极》,跟书中所讲的内容相比,书名取得似乎轻描淡写。书中描述了男孩儿所经受的痛苦以及受虐至死的经过:被挂在主桅杆上9天,遭受鞭刑,还被逼着喝下船长的尿等诸多暴行。[15]
在海盗们看来,杰恩船长这种暴虐的行径导致他无法善终。他被判了死刑,用的是大众眼中较为残忍的方式——脖子被吊了18分钟后,他才死去。不过,很多时候之所以夸大、虚构海盗的暴行,不只是为了诠释他们那种疯狂的精神状态。如果说伦敦或波士顿那些写小册子的人如此大肆渲染海盗的暴行是为了获取金钱上的利益,那么海盗们也同样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树立这种嗜血狂魔、残暴野蛮的名声之后,海盗这个行当干起来就容易很多。一位商船船长若刚刚听说自己的一个同僚被海盗逼着吃掉自己身上的肉,恐怕这位船长只要一见到挂着黑帆的海盗船,很容易就会缴械投降。也就是说,他们是故意渲染他们这种疯癫状态的。针对海盗所维护的这个异常活跃的经济体系,经济史学家彼得·里森在其研究成果中——标题着实令人印象深刻,名为《海盗经济学》——将海盗的极端暴力行为定义为一种符号行为:
为了防止俘虏们私藏东西……海盗们需要树立这样一种残忍、野蛮的名声。更何况,在这种名声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点儿疯癫的色彩,也糟糕不到哪里去。海盗们将这种残暴、疯狂的名声固化成一种独属于自己的名声,奔驰汽车用的便是同样的方法:口碑与广告宣传。海盗们倒是没有在杂志上刊登光鲜亮丽的广告,但他们的确做到了让自己的暴行与疯狂广为人知,以此来巩固、宣传自己的名声。更重要的是,海盗从18世纪主流报纸那里收获了不错的宣传效果,这些报纸不经意间给他们残暴的名声增添了色彩,也间接巩固了他们的利益。[16]
伦敦、阿姆斯特丹与波士顿那些有进取心的出版商虽然彼此隔着万里海域,却不约而同地与海盗建立了这种共生的关系链:为了让出版物大卖,出版商们需要海盗们那些把人的心脏活生生地从胸膛里掏出来的故事;而海盗们也需要出版商们把这些故事尽可能广地传播出去,好让那些潜在的猎物产生恐惧心理。实际上,海盗黄金时代几乎刚好与印刷文化的兴起时间重合,这绝非偶然。14世纪珍妮·德克利松或许是因为在英吉利海峡潜行了十几年而为自己赚得了名声,但通常来讲,如果没有媒体的宣传,海盗是很难维持自身地位的。如果有谁想以海盗的身份谋生,那么拥有残忍与虐人的本性确实会有所助益,但与之相比,远扬的名声更为重要。
[1]D’Amato, loc. 1095–1097.
[2]Egerton and Wilson, plates 37–39, lines 8–23.
[3]见希契科克(Hitchcock)和马伊尔(Maeir)对海上民族和“黄金时代”海盗的细致入微的比较。
[4]詹姆斯·门罗,美国第五任总统。——译者注
[5]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译者注
[6]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派雅各宾派领袖。——译者注
[7]Quoted in https:// founders.archives.gov/documents/Jefferson/01-28-02-0305.
[8]想了解更多关于恐怖主义演变的信息,见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words-at-play/history-of-the-word-terrorism。
[9]约翰·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译者注
[10]约翰·韦恩·盖西,美国连环杀手。——译者注
[11]山姆之子,美国嗜血狂魔。——译者注
[12]查尔斯·曼森,美国邪教组织领袖。——译者注
[13]Leeson, pp. 113–14.
[14]Ibid., p. 112.
[15]这里需要重述一下书中的完整描述,好让现代的读者明白,其实那种看似无端的暴力行径由来已久:“(男孩儿)被一顿鞭打之后,又被泡在盐水里;后来,他把男孩儿绑在主桅杆上九天九夜,四肢一直大张着;但他依旧不罢休,将孩子松绑之后放到跳板上,用脚踩踏孩子的身体,还让手下也跟着做,手下拒绝了;为此,他越想越恼火(像他这种人,看到大家可怜那孩子很有可能会被激怒),于是,趁那孩子躺在跳板上站不起来,他就使劲儿跺着那孩子的胸脯,跺得那孩子嘴里一直往外喷东西;他气得用两手掐住那孩子的喉咙,几次硬生生地将吐出来的东西塞回去;那可怜的小家伙就这样被折磨了18天,奄奄一息,吃到的食物只够维持生命体征,就这样,还不停地遭受折磨;他每天都会被毒打,尤其是他死的那天;当时,他奄奄一息,说不出话,他那无情的主人抽了他18鞭子;就在要断气的时候,他把手指放到嘴边,这是想要喝东西的信号,紧接着,那个残忍的家伙依旧不依不饶地继续虐待他,从船舱里拿来一只杯子,里面装着他的尿,让那孩子喝下去;据说,那孩子喝下去一点儿,随即就推开了,紧接着就断了气;老天慈悲,他终于结束了痛苦;由于没能尽兴,船长似乎还有些不悦。”Quoted in Turley, pp. 10–11.
[16]Leeson, pp. 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