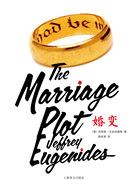
等待
等待(attente)/等待
等待情人引发的难以排遣的焦虑,因情人不经意的拖延(约会、信件、电话、归来)。
……等待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接到了命令不得随便行动。等电话于是就成了编织束缚自己的罗网,此恨绵绵,个中苦衷难以言传:我禁止自己离开房间,不让自己去上厕所,甚至不敢去碰电话(以免占线)……
她听见楼下公寓传来电视机的声音。马德琳卧室正对的州议会大厦穹顶,在夜空的衬托下灯火闪耀。他们无法控制温度的继续上升,暖气片在挥霍似的撞击着,嘶嘶作响。
马德琳对此越是思索便越是理解了:所谓极度孤独并不只是她对伦纳德的感觉,而是说出了她每次恋爱时的感觉。它说出了爱情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或者说,爱情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电话铃响了。
马德琳从床上坐起来。她把正读的那页折了个角,她等到无法再等了(响了三下)才拿起听筒。
“喂?”
“马迪?”
是奥尔顿,从普雷蒂布鲁克打来的。
“噢。你好,爸爸。”
“别那么激动。”
“我在学习呢。”
像平常那样,他没有拖泥带水,而是直奔主题。“我和你妈妈正在讨论毕业计划。”
起先马德琳还以为奥尔顿是指他们正在讨论她的未来,但很快她就意识到其实只是他们来参加毕业典礼的食宿安排。
“现在才四月份,”她说道,“毕业要到六月份。”
“根据我对大学城的经验,宾馆提前几个月就会预订满的。所以我们得事先决定好安排,现在有几个选择。你在听吗?”
“在听,”马德琳回答道,但同时开始走神了。她把勺子插入花生酱罐子,再举到嘴边,这回她只是舔着。
只听见奥尔顿在电话那头说道:“选择一:我和你妈妈典礼前一天晚上过来,住在宾馆里,典礼当天晚上和你一起吃晚饭。选择二:我们典礼当天早上过来,和你一起吃早饭,典礼结束后离开。这两个选择对我们来说都可以,由你决定。但让我来解释一下每个选择的优缺点。”
马德琳正要回答,却听见菲莉达在另一个分机里开口了。
“喂,亲爱的。我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你。”
“我们没有吵醒她,”奥尔顿嚷道,“在大学里十一点钟根本不算晚。尤其是星期五晚上。嘿,星期五晚上你躲在屋里干什么?脸上长痘啦?”
“你好,妈妈。”马德琳说道,故意不睬他。
“马迪,亲爱的,我们在重新布置你的卧室,我想问你——”
“你们在重新布置我的卧室?”
“是的,那屋子需要翻新一下了。我——”
“我的房间?”
“是的。我在考虑把地毯换成绿色的。你知道,漂亮的绿色。”
“不行!”马德琳叫道。
“马迪,你的房间我们已经照原样保持四年了——都让人觉得是一块圣地了!我希望能偶尔把它用作客房,因为带卫生间。你回家来还可以住的,不用担心。它永远是你的房间。”
“那我的墙纸呢?”
“墙纸都旧了。已经开始剥落了。”
“你不能换我的墙纸!”
“噢,好的。我不动墙纸。但是地毯——”
“对不起,”奥尔顿语气强硬地说道,“这个电话是关于毕业典礼的。菲尔,你在扰乱我的程序。你们俩另找时间讨论装修的事。现在,马迪,我来讲讲优缺点。你表哥从威廉姆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毕业典礼结束之后一起吃的晚饭。不过,也许你还记得,吃饭时多茨一直在抱怨说他错过了所有的晚会——后来他吃到一半就跑了。现在,我和你妈妈很愿意待上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如果我们要见你的话。但如果你到时候太忙,那么也许一起吃早饭会更好些。”
“离毕业还有两个月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也是这样跟你爸爸说的。”菲莉达说道。
马德琳突然想到她正在占用电话线。
“让我想一想吧,”她不耐烦地说道,“我得挂了。我还在学习来着。”
“如果我们要待一个晚上,”奥尔顿重复道,“我想得马上预订房间了。”
“回头再打给我吧,让我仔细想一想。星期天再打。”
她挂电话时奥尔顿还没说完,所以当二十秒钟后电话铃再次响起时,马德琳拿起话筒就说道:“爸爸,挂了吧。我们不需要今晚就作出决定。”
电话里没有声音。然后一个男声说道:“你不必叫我爸爸。”
“噢,天哪。是伦纳德吗?对不起!我还以为是我爸爸呢。他已经在为毕业计划过度紧张了。”
“我自己也有点极度紧张来着。”
“为了什么事?”
“为了打电话给你。”
这不错。马德琳将一根手指抵住下唇滑动。她问道:“你平静下来了吗?或者你想等会儿再打过来?”
“我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谢谢你。”
马德琳等着他说下去,但他什么也没有说。“你打电话来是有事吗?”她问道。
“是的。还记得费里尼的电影吗?我希望你也许可以,如果你不是太……我知道这么晚打电话不礼貌,不过我现在在实验室。”
伦纳德听上去是有点紧张。这不好。马德琳不喜欢容易紧张的人,容易紧张的人总有他紧张的原因。到现在为止,伦纳德更像是痛苦型,而不是紧张型。受折磨痛苦型更好些。
“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她说道。
“我漏掉什么了?”伦纳德问道。
“比如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吗?’”
“我很乐意。”伦纳德说道。
马德琳对着听筒皱了皱眉。她有一种感觉,是伦纳德早已设计好了这番对话,就像一个棋手提前想好了八步棋。她刚想抱怨,就听见伦纳德在说:“对不起,很糟糕的玩笑。”他滑稽地清清嗓子。“听着,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吗?”
她没有马上答应。他应该受到一点惩罚,于是她对他施加了压力——又等了三秒钟。
“我很喜欢。”
都已经说出那个字(96)了,她不知道伦纳德是否注意到。而她自己注意到了,不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毕竟,这只是一个字而已。一种说话方式。
第二天晚上,星期六,变幻莫测的天气又突然转冷。马德琳穿着棕色翻毛皮夹克,一边朝他们约定见面的餐馆走,一边冻得瑟瑟发抖。之后,他们一起前往缆车影剧院,在这艺术剧院里的所有不配对的沙发和椅子中找到一张软塌塌的长榻坐了下来。
这电影让她看不下去。故事的线索不像好莱坞电影那样清晰,电影带有梦幻色彩,视觉华美但情节不连贯。观众都是大学生,当出现近乎淫秽的欧洲特色的镜头时——当那个大胸女人将巨大的乳头塞进少年主人公的嘴里,或者当那个老人趴在树上大叫“我要女人!”——他们便爆发出会心的笑声。费里尼的主题似乎与罗兰·巴特的主题一样,都是爱情,不过这是意大利式,关于身体的,不是法国式的,关于心智的。她不知道伦纳德是否已经了解《阿玛柯德》的内容,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让她进入状态的手段。而事实上,她的确进入状态了,但不是因为电影。电影看上去很好,但让她迷惑,让她觉得幼稚而俗气。似乎过于放纵、过于男性化。
电影结束后,他们出了电影院走上南大街。他们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马德琳很高兴地发现伦纳德尽管高大但不是太高。如果穿上高跟鞋,她的头顶可以高过他的肩膀,几乎到他的下巴。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哦,至少现在我知道什么是费里尼风格了。”
城市的天际线在他们左侧,可以看见河对岸“超人大厦”(97)的尖顶直插入城市那造作的粉红色的天空。大街上空荡荡的,除了刚离开影院的其他观众。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形容词,”伦纳德说道,“人们会说,‘那真是班克黑德型。’或者,‘对我来说有一点太班克黑德型了。’”
“班克黑德型听上去有范儿。”马德琳说道。
“比班克黑德式要好一些。”
“或者班克黑德般。”
“什么什么般太难听了。有乔伊斯型、莎士比亚型、福克纳型。但有什么什么般吗?有谁是什么什么般的?”
“托马斯·曼般?”
“卡夫卡式,”伦纳德说道,“品钦式!瞧,品钦已经是一个形容词了。加迪斯(98)。加迪斯会是什么?加迪斯式?加迪斯样?”
“你不能这样处理加迪斯。”马德琳说道。
“是啊,”伦纳德说道,“倒霉的加迪斯。你喜欢他吗?”
“我读过一点《承认》。”马德琳回答道。
他们转到行星大街,开始上坡。
“贝娄(99)式,”伦纳德说道,“稍微改动一下拼写听上去就好听多了(100)。纳博科夫式(Nabokovian)已经有v了,契诃夫式(Chekhovian)也一样,俄国人都搞定了。托尔斯泰型(Tolstoyan)!这个家伙是等着做形容词呢。”
“别忘了托尔斯泰主义,”马德琳说道。
“我的天哪!”伦纳德叫道,“一个名词!我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个名词。”
“班克黑德型是什么意思?”
伦纳德想了想。“属于或关于伦纳德·班克黑德(美国人,1959年出生)的,以过于内省或忧虑为特征。悲观、抑郁。参见无能人条。”
马德琳哈哈大笑。伦纳德立定,抓住她的胳膊,严肃地看着她。
“我带你去我那儿。”他说道。
“什么?”
“我们一直这样走下去?我已经在带你往我那儿走了。没错,我在带你回去。真是可耻,可耻。我并不想这样。不想和你这样。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知道我们在往你那儿走。”
“你知道?”
“我是要点破你的。等我们熟了再说。”
“我们已经熟了。”
“我不能上去。”
“请吧(求你了)。”
“不,今晚不行。”
“汉纳式,”伦纳德说道,“顽固,倾向于坚定立场。”
“汉纳型,”马德琳说道,“危险,不受招惹。”
“我接受警告。”
他们站在寒冷、黑暗的行星大街上彼此凝视。伦纳德从口袋里伸出双手,将长发拢到耳后。
“或者我上去待一会儿。”马德琳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