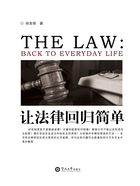
案例二 中、日对偷电案处理比较
日本法院判过一个偷电的案件,一个人因偷电被起诉到法院,这是作为刑事案件起诉的,法院最后以盗窃财物罪判决。这个判决一下,在日本引起轰动,大家说这个判决不对。为什么不对?物在刑法上没有定义,但是民法有定义,《日本民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本法所说的物是指有体物。什么叫有体物?民法学者作了解释,所谓有体物指占据一定空间,人的五官能感觉其存在的物质,包括固体、液体和气体。电不是有体物。因为这个判决受到批评,日本的立法者在明治四十年的新刑法中,在第三十六章盗窃罪及强盗罪中增加了一个条文:关于本章之罪,电气视为财物(第二百四十五条)。在我们国家,偷电可不可以判决为盗窃财物罪呢?刑法关于物没有定义,我们的民法通则关于物也没有定义,这就要看民法学者关于物的定义。按照民法学者一致的解释,我们民法上所说的物是有体物。但民法教材上说了物指有体物之后,增加了一句:包括人力可以支配的自然力。因此,如果我国现在裁判偷电的案件,将其判为盗窃财物罪,是完全可以的。
阅读上述中、日案例处理比较,首先得到的信息是,日本民法规定物为有体物,但法官判偷电为罪,遭到非议;而中国民法没有物的规定,刑法也没有,法官判偷电为罪,没有非议。中国没有规定,判案不受影响;日本有规定,判案反而受影响。看来,有规定不如无规定。这无疑是对大陆法系法典化的一种讽刺。
用电要花钱,偷电相当于偷钱,这是任何一个偷电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的事。那个日本偷电人应该不是查了《日本民法典》发现电不属于物才去偷的,因此,从实质意义上讲,按盗窃罪判处其刑罚并不违背“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的原则。即使他是查了《日本民法典》再去偷的,从另一种实质意义上讲,也可以判处其徒刑。因为他是恶意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但是,是不是漏洞也是见仁见智的事,见下文)去做从基本道德上自己也认为不应该做的事(他查了法律再去做,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理性和懂得判断的人),所以惩罚他就是挽救他。如果人世间没有制定法律,而是由神来断案,相信神也会判其盗窃罪。如果法院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日本法院在不符合民法规定的情况下判偷电者刑罚是否引起日本法律界的普遍反对则不得而知;法官在其判决书中如何解释或者说理也不得而知。笔者相信一定也有支持法官那种判决的人。这里还试图为法官的判决提供一种理由,即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而不是刑事关系的,故法官审理刑事案件可以不依据民法,正如审理民事案件通常不会依据刑法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偷电案件上,日本刑法并无漏洞。后来,日本刑法增加的条款虽然解决了对偷电行为可否判刑的问题,但因其规定不科学,不符合人类理性,可能导致新的问题。“电气视为财物”之前作了“关于本章之罪”的限定,结合学者前面的解释,电气在其他场合都不是财物。至少供电公司应该是不会同意这个结论的。
但是,另一方面,从一般意义上说,无论民法、刑法,还是其他什么法,任何人都不应当违反,尤其是审案的法官。法官审民事案时违反刑法或者审刑事案时违反民法,应该也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在罪行法定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的西方更是如此。既然盗窃罪的对象是物,法律也规定了什么是物,而电不在规定之内,则必然的逻辑结论是偷电不构成盗窃。
可见,日本法院与其反对者各有道理,难说对错。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还可以举两个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 一个是对于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的行为能否依《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定组织卖淫罪?否定者认为,依文义,卖淫专指妇女出卖肉体,法律对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否构成卖淫并无规定,故不应认定为犯罪,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肯定者认为,刑法规定的卖淫的本质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出卖肉体,无论什么性别卖淫,均违反了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将同性卖淫归入卖淫范畴并追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法有关卖淫嫖娼犯罪规定的立法精神。另一个例子是,医院将身份不明、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病人予以遗弃致病人死亡,能否依《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肯定者认为,该条中的扶养义务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亲属间的法定义务,也包括职业道德、职责所要求的义务。否定者认为,扶养关系只在亲属之间存在,像本案中所谓职业道德要求的义务实际上是指救助义务,对不履行这种义务的遗弃行为加以惩治,应另设罪名。
一个是对于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的行为能否依《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定组织卖淫罪?否定者认为,依文义,卖淫专指妇女出卖肉体,法律对同性之间的性交易是否构成卖淫并无规定,故不应认定为犯罪,否则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肯定者认为,刑法规定的卖淫的本质特征是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人出卖肉体,无论什么性别卖淫,均违反了基本伦理道德规范,将同性卖淫归入卖淫范畴并追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法有关卖淫嫖娼犯罪规定的立法精神。另一个例子是,医院将身份不明、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病人予以遗弃致病人死亡,能否依《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以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肯定者认为,该条中的扶养义务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亲属间的法定义务,也包括职业道德、职责所要求的义务。否定者认为,扶养关系只在亲属之间存在,像本案中所谓职业道德要求的义务实际上是指救助义务,对不履行这种义务的遗弃行为加以惩治,应另设罪名。
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会抱怨,法律也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可以”。上述争论给读者的印象是法律似乎很复杂。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是,其实并非如此。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对是否有明确规定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对于开始出现的偷电行为、同性卖淫行为、医院遗弃行为,怎么处理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但都不能说是错误的,当然,要符合一般的法理或者人性。本书案例篇的案例一“许霆恶意取款”也属于这种情况,但法院最初判许霆无期徒刑不符合人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尽量避免不同的法院作出不同的判决,因为同案应当获得同判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公众的期盼;另一方面,立法机关要迅速对司法实践中的争议作出明确规定,但这两方面我们都做得很差。比如,王海式打假索赔案,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判决,立法机关至今也不明确王海们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又比如,同性性交易案件在我国最早案发于1998年年底的成都,由于检察机关向上级请示后也难以作出定论,于是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后者只能撤案。 而在五年之后发生的南京同性性交易案件,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判被告人有罪,必然引起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激烈讨论。
而在五年之后发生的南京同性性交易案件,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法院判被告人有罪,必然引起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激烈讨论。 总之,并非问题复杂,是我们做得不到位。
总之,并非问题复杂,是我们做得不到位。
比较新的问题是网上公共会议式的网络裸聊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点对面式的网络裸聊行为是否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这两个问题与前述偷电行为、同性卖淫行为、医院遗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实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只能期待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让争议早点结束。
这两个问题与前述偷电行为、同性卖淫行为、医院遗弃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实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只能期待最高立法机关或者最高司法机关让争议早点结束。
对于偷电案的处理,在德国和法国也出现争议,经历了不同的处理。 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笔者上面的观点。
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笔者上面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