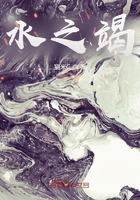
第11章 吴芮(10)
想不到这一走就一路走到了郊外,最后我们在一大片休耕的开阔地前停住了脚步。
张良从怀中拿出另一枚令牌,上面画着一只背上盘着蛇的玄龟——即四象中的玄武。他又将令牌翻过来让我看背面,上面用大篆写着两个字:运筹。
我这才意识到我从收到那枚令牌起还未仔细端详过它。于是取出朱雀,看到背面也刻着同样笔法的两个大字:安民。
“传说朱雀为民而浴火,故持此令牌者需为除暴安民之人。朱雀属火性,可降天火,所谓除暴;也可补人之元气,救死扶伤,所谓安民。”
说完,又指了指自己手中那枚令牌。“玄武,其中玄龟,有占卜之术。武即为阴,所持之人虽性情阴冷,但要有为天下运筹之心。属水性,可唤雨。”
见我听得两眼发直,张良嘿嘿一笑,取走我手中的朱雀。
“只要持有对应令牌,心中专注于所祈求的术法,便可招来……”话说至一半而止,他闭上双眼,静默片刻。开眼的一刻大喊一声:“天火!”
话音未落,只见云层中忽现一片浓重的火红。然后一道如陨石一般的火团坠落于地,遍地野草一触即燃,瞬间腾起数尺高的火焰,热浪直逼得我退后了好几步。
我想到临近的村落,脸色发白地拉住张良想要制止他。但见他只是微笑着念了句“收”,泛着红光的那片云立刻暗了下去。然后举起那枚玄武,又是片刻后喊声“雨来!”,云层应声变暗,紧接着便是倾天暴雨直下,浇灭了野地上熊熊燃烧的大火。
“收。”
片刻前才怒吼过的天空又恢复了它往日的平静,只有地上残留的缕缕青烟不断提醒我这一切都不是幻象。我忽觉存在于天地之间的自己甚为渺小,强撑的冷静顺势崩塌,两膝一软,坐在了地上。
“这只是我能施展的力量,到了身为持有者的你们手中,不止天地会为之变色,整个时代的兴衰,治世抑或灭世,全看你们自己。所以,我必须谨慎选择。”
说罢,张良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一只手。那只手洁白无瑕,可我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握住它。朱雀令牌静静地躺在他的手心里,庄严而沉寂。
“这是……神的力量吗?”
于是我看到了,张良那充满怜悯的表情。他是在怜悯什么?即将在浩劫中挣扎的世人?还是不得不承受命运的人们?
“这不是神的力量,兴许只是天地原本的色彩。你要逃避它吗?”
一瞬间,一股热浪从心底直冲向头顶。我一把握住了面前那只对于男人来说略显纤细的手,像握住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何要做这些事,不知道他背后的人,不知道这青铜令牌到底为何物,不知道他为何认为这样就可以拯救万民于水火。
但是我明白了一点。我明白他本可以拥有这样的力量,却要将这力量交给我。想到初见时他提起的邾县民生的问题,我也明白了他为何要选择我。
我握紧手中的令牌。
安民。
只为这两个字,我愿意相信他。
————————————————————————
子房在邾县一直待到了第二年冬。因为总和他在外约见不太方便,我干脆撤了府门外的符阵,让他住进我府。结果真如他所说,那些魑魅魍魉从此都躲得远远的。我戏称要把他当作桃木剑挂在家门口驱邪,被他理所当然地回绝了。
关于令牌能释放的术法,我和他都认为天火还是少召唤为妙,只用朱雀进行必要的治疗。为了验证它的功效,我特意在邾县找了几位久病缠身的老人,结果当真是一治便好。老人家们感动得痛哭流涕,坚持要替我去街头巷尾宣传美名,被我果断制止住了,并恐吓一旦说出去旧病就会复发。全天下病人那么多,我又不擅长回绝人,到时候衡山王府变成医馆,我可承受不住。
第二天我就为了父亲的头疾回了趟鄱阳。发现各种灵丹妙药都治不好的头痛就这么轻易没有了,父亲沉默了很久。我没有指望他会向我道谢,反而为他欠了我一个人情沾沾自喜。观察了他几日确认没有异状,我就打算离去了。
和他道了别准备出门之际,他叫住了我。我回身,就见他对着窗外低喃道:“有你这法子,筵的病也可以治好了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虽然不确定答案,但我还是很坚决地回答道:“恐怕不行。筵的病,只有在东海那边才能找到解决办法。”
过去了这么多年,再回过头来否定当年的决定,再去后悔,又有什么意义?木已成舟。倒不如坚定之前的信念,多少还会留有一丝慰籍。
从鄱阳回来后不久,某一日,苹儿怀里抱着一只鸽子来找我,说是英布有信送来。我接过竹筒,抽出里面的帛书一看,原来是项羽打算于今年三月出兵攻齐,要英布派兵随之一起北上。英布问我的意见。
当初选女婿时果然没看错人,我心想。即使他现在的地位甚至在我之上,为了当年的约定,凡事还是会遵从我的意思。
我至今脑海中还时常浮现出三年前,英布带着数百骊山刑徒投奔我时的样子。那时所有人都嘲笑他的身份和脸上被黔的字,戏称他为黔布。而他只是憨笑着回应,说什么“相面的早年就说我当刑而王,现在刑是受过了,就差王了”之类。我看中他的能为和洒脱,将独女念云许配给他时,众人那下巴几乎惊掉的表情我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好笑。
带着英布的书信,我又回到案牍前。准备写回信时,子房进来了。自从他住进我府,我们就亲近了许多。我改称他为子房,但他却执意叫我番君。说这是百越人拥戴我才起的敬称,他这样叫也是要我莫忘百姓。
我没有避讳他的意思,但也不由得住了笔。他见我在办正事,转身要掩门离去。我叫住他。
“如你所盼,项羽要出兵攻齐了。”
他叹息:“并未如我所盼。”说罢从怀中掏出了一枚不同于玄武的青色令牌,“青龙回归,韩成已毙命。”
我轻呼出声:“为何?项羽应该没有借口杀他了!”
“刘邦违约,派韩王信破韩,收降郑昌。我之前为救韩成而保刘邦的话语反而成了他的催命符,是我的过错。”
我放下了手中苍毫。“刘邦毁约,野心昭然若揭,你还是不要与他牵扯过多为好。”
他沉吟片刻。“不然,刘邦此人不可妄断,我还是要去当面问过。况且青龙和玄武的持有者还未找到,这一趟,我就是来向你道别的。”
我随后说出了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话:“你说过我足以治世安民,为何还要去考虑追随刘邦?”
他有些惆怅地苦笑道:“安民可抵御外敌,却无法统一天下。”
是的,我知道。我坐回原处,为自己的失态感到羞愧。
“老实说,如果有其他选择,我不会选择刘邦。他足够杰出,还善于纳谏、招揽人才,得知我的身份后对我言听计从。但他因为某些原因,惯于利用他人,也包括我。所以你一定要小心。朱雀的事,绝对要保密。”
你也会被人利用吗?这竟让我对刘邦生出些许好奇。但子房不愿过多提及那所谓“某些原因”,我便也没再询问,点点头答应了。
子房就这样离开了,我没去送他。这当然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在给英布的信上只写了四个字:称病,观望。
将竹筒交给苹儿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对她提了句:“过一阵,我可能会北上中原。”
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说:“我也去。”
我摆手表示不同意,告诉她这回和上次反秦出战不一样。上一次秦朝的灭亡是早晚的事,我只是坐收渔利,但这一回胜负在哪边却不好说。
但她的认真程度却不亚于我,无论我怎样解释她都不听,还威胁我说如果不允许她跟随,她就女扮男装溜到英布那里随军,仿佛又变回了小时候的执拗性子。看着她得意洋洋地离去,我真恨自己总是这么容易被她说服。但说真心话,我也的确不想离开她,至少从生活层面讲,没了她我还真会不习惯。
但苹儿呢?为何要如此坚决地陪在我身边?也许是我错看了她,说不定她对我的感情比我体会到的要多得多。
夕阳留下的余晖有些耀眼,我闭上双目,独自静立于庭院中,静听风吹起落叶的声音。冬日的柳树即使仍长着叶子,也早没了春日里的生机,萧萧瑟瑟地相互拍打着。
渐渐地,我仿佛从这些平淡的天地之音中听到了远方的声音。就在那遥远的北方,楚骑的马蹄要将大地踏碎般发出类似怒吼的巨响,战鼓雷雷,刀和枪相互碰撞,血和肉向空中蹦飞。那是天地都要为之震动的声音。
我豁然张目,决绝地目视前方。
这场谁也逃不掉的战争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