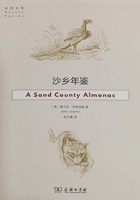
三月
大雁归来
一只燕子的来临说明不了春天的到来,但当一群大雁冲破了三月暖流的雾霭时,春天就来到了。
一只主教雀正对着暖流歌唱春天,后来却发现自己搞错了,不过,它可以纠正它的错误,再继续保持它在冬季的缄默。一只花鼠想出来晒太阳,却遇到了一阵夹雪的暴风,只有再回去睡觉,而一只定期迁徙的大雁,是下了在黑夜飞行二百英里的赌注的,它期望着在湖上找到一个融化的洞眼,它要想撤回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它的来临,伴随着一位切断了其后路的先知的坚定信念。
对于那没有往天空扫视一眼,也没有用耳倾听雁叫的人来说,即使身处三月的早晨,也是一样地单调灰黄。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教养的女士,佩戴着像鸟的环志似的全美大学联谊会的标志9,她告诉我,她从未听到,也未见过大雁一年两度对她阳光充足的屋顶宣告着去而复来的季节的来临。教育有可能是一种取得对不大值钱的东西的认识的方法吧,在这种价值观下,大雁立即就成了一堆羽毛。
向我们农场宣告不同季节来临的大雁知道很多事情,其中包括威斯康星的法规。十一月份南飞的鸟群,高高地、目空一切地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即使发现了它们所喜欢的沙滩和沼泽时,也几乎是一声不响。通常,乌鸦的飞行被认为是笔直的,但与坚定不移地向南飞行二十英里,直达最近的大湖目标的大雁相比,也就成了曲折的了。在那儿,白天大雁在宽阔的水面上闲荡着;晚上就到刚刚收割了的地里偷食玉米。十一月份的大雁知道,每个沼泽和池塘,从黎明到夜幕降临,都布满了窥探着它们的猎枪。
三月份的大雁则有不同的经历。尽管它们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遭受枪击——它们那被大号铅弹所击碎的翅膀上的羽毛就是证明,它们仍然知道,现在正是不狩猎的春季。它们顺着弯曲的河流拐来拐去,低低地穿过现在已经没有猎枪的狩猎点和小洲,向每个沙滩低语着,就如同久已失散的朋友一样。它们曲折地在沼泽和草地上空低低穿行着,向每个刚刚融化的水洼和池塘问候着。终于,在我们的沼泽上空做了几次试探性的盘旋之后,它们鼓起翅膀,静静地向池塘滑翔下来,黑色的翅膀慢慢地扇动着,白色的尾部朝向远方的山丘。一触到水,我们刚到的客人就叫起来,它们溅起的水花使得那脆弱的香蒲也把它的那点儿冬思抖落掉了。大雁又回到家里了。
这正是我每年都希望自己变成一只麝鼠的那一时刻——沼泽里的麝鼠能望到深处。

一旦第一群大雁来到这里,它们便向每一组迁徙的雁群高声地喧嚷着发出邀请,因此,不消几天,在沼泽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根据两个标准来衡量我们春天的富足:所种的松树和停留的大雁的数目。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我们记录下来的大雁数目是六百四十二只。
与秋天一样,春雁每天都要往玉米地做一次旅行,不过不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从早到晚,成群地喧闹着往收割后的玉米地飞来飞去。每次出发之前,都有一场高声而有趣的辩论作先导,而每次返回之前的争论则更为响亮。返回的雁群一旦完全到了家,便不再在沼泽上空做试探性的盘旋。它们像凋零的枫叶一样,左右摇晃,从空中翻腾着落下来,并向下面欢呼着的鸟儿们伸展出双脚。我猜,那接着而来的咕哝声,是在论述白天食物的价值。它们现在所食取的遗穗在整个冬天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因此未被那些在雪中搜寻玉米的乌鸦、棉尾兔、田鼠以及环颈雉所发现。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雁选取食物的那些收割后的玉米地,通常总是过去的草原。谁也不明白这种对草原玉米的偏爱反映了什么。也许它反映了某种特殊的营养价值,或者反映了自草原存在的时代以来就代代相传的传统。大概,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草原玉米田正在扩大。如果我们能懂得它们每天往返于玉米地前后的辩论,我们就能很快懂得这种偏爱草原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能。所以,我极力主张,它应该作为一种神秘的东西保留下来。如果我们懂得了所有有关大雁的知识,这个世界将会多么单调无味!
通过对春雁集会的日常程序的观察,人们注意到所有的孤雁都有一种共性:它们的飞行和鸣叫很频繁。人们很容易把一种忧郁的声调与它们的鸣叫联系起来,而且很快就得出结论说,这些孤雁是心碎的寡妇,或是在寻找失散了的子女的父母。然而,阅历丰富的鸟类学家们认为,这样一种主观的对鸟类行为的解释是不慎重的。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都试图不拘泥于一种答案。
我和我的学生开始注意每支雁队组成的数字,六年之后,在对孤雁的解释上,出现了一束不曾预料的希望之光。从数学分析中发现,六只,或以六的倍数组成的雁队,要比偶尔出现一只的情况经常得多。换句话说,雁群是一些家庭,或者说是一些家庭的聚合体,因此,孤雁正好大概符合我们先前所提出来的那种多情的想象。它们是在冬季狩猎中丧失了亲人的幸存者,现在正徒劳地寻找着它们的亲属。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这些孤独的鸣叫者悲痛了。
单调枯燥的数字竟能如此进一步激发爱鸟者的感伤,确实少有。
在四月的夜间,天气暖和得可以坐在屋外,我们喜欢倾听在沼泽中的集会过程。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静悄悄的,人们听到的只是沙锥鸟扇动翅膀的声音,远处的一只猫头鹰的叫声,或者是某只多情的美洲半蹼鹬从鼻子发出的咯咯声。然后,突然间,刺耳的雁叫声重新出现,并且带着一阵急骤的混乱的回声。有翅膀在水上的拍打声,有由蹼的划动而推动起来的“黑色船头”冲出来的声音,还有观战者们为激烈的辩论所发出的呼叫声。最后,一个深沉的声音做了最后发言,喧闹声渐渐地转为一种能听见的模糊的小声谈论。这种大雁的小声谈话是难得停止的。于是,我再一次真的希望自己是一只麝鼠。
等到白头翁花盛开的时候,大雁集会也就逐渐减少。在五月来到之前,我们的沼泽便再次成为弥漫着青草湿气的地方,只有红翅黑鹂和黑脸田鸡带给它生气。
历史不曾预料到,大国将会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上发现一个各国的联合体。10然而,世界上的大雁具有这种观念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年三月,它们都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为这个基本的信念做赌注。
最初仅有冰原的统一,接着是三月暖流的联合,以及大雁向北部的国际性逃亡。自更新世以来,每年三月大雁都要吹起联合的号角,从中国海到西伯利亚大平原,从幼发拉底河到伏尔加河,从尼罗河到摩尔曼斯克,从林肯郡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自更新世以来,每年三月大雁都要吹起联合的号角,从卡瑞托克到拉布拉多,从曼塔木斯基到昂加瓦,从霍斯述湖到哈得孙湾,从艾沃瑞岛到巴芬岛,从彭汉德尔到麦肯齐,从萨克拉门托河到育空河。
因为有了这种国际性的大雁活动,伊利诺伊的玉米遗穗才得以穿过云层,被带到北极的冻土带,在那里与白夜中的六月的多余阳光结合起来,在所有其间有土地的地方生出了小雁。在这种每年一度以食品换取光明、以冬季的温暖换取夏季的僻静的交易中,整个大陆所获得的是一首有益无损的、从朦胧的天空洒落在三月的泥泞之上的、带着野性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