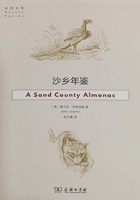
四月
春潮来临
大河总要流过大城市,同样的道理也使得劣质的农场有时要受到春季洪水的包围。我们的农场质量很差,因此,有时我们于四月中旬去那里时,也会陷入困境。
当然,不必特意,人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天气预报中猜测到,什么时候北方的雪会融化,人们也能估计到,要多少天洪水就会冲破上游城市的防卫。如果可能,星期天晚上,人们肯定会回到城里去工作,然而,人们不能。不断漫溢的水为星期一早上遭难的残骸咕哝着悼文,该是多么新鲜!当大雁远征了一片又一片的玉米田的时候,也正是每一块田变成一个湖的过程。这时,它们的叫声该是多么深沉,多么骄傲!每隔几百码,就会有一只新上任的头雁飞行在空中,为率领它的雁群在清晨巡视这新的水的世界而奋斗着。
大雁对春潮的热情是一件很微妙的事。那些不熟悉大雁饶舌的人,是很容易忽视这一点的;而鲤鱼对水的热情却是显而易见和十分明确的。连上游的洪水打湿草根的速度也没有它们来得快,它们以猪一样的巨大热情搜寻着、翻滚着,最后到达了牧场;它们闪动着红色的尾巴和黄色的腹部,越过马车的车道和牛走的小路,它们摇动着芦苇和灌木,急于去探索那个对它们来说正在扩大的世界。
与大雁和鲤鱼不同,陆生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是以一种哲人式的超然态度来对待大水的。在一棵河杨上站着一只主教雀,它高声地啼叫着,要求认领一片看不见其存在的领地——但不是树木。一只松鸡从洪水漫延的树林里发出敲鼓般的声音,它肯定是站在那个最高级的发出咚咚响声的圆木的高顶上。田鼠以小麝鼠般的镇静自若,在隆起的高地上摇摇晃晃地走着。从果园里蹦出来一只鹿,它是从平日白天在柳树丛中的床上被赶出来的。到处都有兔子,它们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我们山丘上的一小方块地,因为诺亚不在这里,这块地方就可为它们做方舟之用了。
春潮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高度的冒险,同时还带来一种预料不到的、从上游农场里漂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块旧木板漂落在我们的草坪上,对我们来说,它的价值要比刚从伐木场里得到的同样的木板高两倍。每一块旧木板都有它独特的历史,它们的历史常常是不为人知的,但常常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猜测的;从它的木材上,它的尺寸,它的钉子、螺丝,或者绘画上,它的抛光,或者它的缺点,它的磨损和腐蚀上,人们甚至可以从它在沙滩上被磨损的边缘和两头上猜出,在过去的年代里,有多少次洪水曾经携带过它。
我们的木材堆,全部是从河流中募集来的,因此,它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收藏,而且是一部关于上游农场和森林的人类奋斗历史的集锦。一块旧木板的自传,是一种在大学校园里还未曾讲到的文献,而任何一个河边的农场,都是一个锤子或者锯子可以随意阅读的图书馆。春潮来了,总会有新书增添进来。
有各种程度和类型不同的僻静之处。湖中的小洲是一个类型,但湖里有船,而且总有一个人们可能要登上岸来进行访问的机会。高耸入云的山峰是另一种类型,但多数山峰都有小径,在小径上有旅游者。我知道,没有一个僻静的地方会像春潮指引的地方那样安全。大雁也会这样认为——它所见到的各种类型的僻静处所要比我多。
现在我们正坐在一个山丘上,在一株刚刚盛开的白头翁花旁边,望着大雁飞过。我看见,道路慢慢地浸入水中。我的结论是(是发自内心的欣喜,而非表面上的不偏不倚),交通问题无论国内或国外,起码在这一天,只在鲤鱼中才会引起争论。
葶苈
现在,在几个星期之内,葶苈,那种怒放着的最小的花,就会把那小小的花朵撒满所有有沙土的地方。
渴望春天,但眼睛总朝上望的人,是从来看不见葶苈这样小的东西的;而对春天感到沮丧、低垂着眼睛的人,已经踩到了它,也仍浑然不知。把膝盖趴在泥里寻求春天的人发现了它——真是多极了。
葶苈所要求和得到的,不过是一点点温暖和舒适,它是靠时间和空间多余的残渣维持生活的。植物学书籍会给它两行或三行的位置,但从来不曾附上一幅它的插图或照片。贫瘠的沙地和微弱的阳光孕育不出较大、较美的花,却足以孕育出这些葶苈。再说,它确实不是春天的花,而仅仅是一种希望之补遗。
葶苈拨动不起人们的心弦。它的芳香——如果有的话,也消失在一阵阵的风中了。它的颜色是简单的白色,它的叶子蒙着一层明显的茸毛。没有动物吃它,它太小了。没有为它吟唱的诗歌。某个植物学家曾经给它起过一个拉丁文学名,然后就把它忘记了。总而言之,它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生物,迅速而妥善地做好一件小小的差事。
大果橡树
当学校的孩子们在投票表决州鸟、州花或州树时,他们并不是在做某种决定,而仅仅是对历史进行认可。因此,就在大草原的各种草取得了这个地区的占有权的时候,历史使大果橡树成为南威斯康星的特色树种。它是唯一能够经受草原大火并得以生存的树。
你是否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整株大果橡树都包有一层厚厚的软木皮,即使最细小的嫩枝也不例外?这层软木是盔甲,大果橡树是由侵略性的森林派去攻击大草原的突击队,火是它们必须搏斗的。每年四月,当新草给草原穿上不能燃烧的绿装之前,火已经自由自在地跑遍了这块大地,未受伤害的只有这种长着厚皮的老橡树。其皮之厚是难以烧焦的。那些散布在各处的老树的小林子,即为拓荒者们所熟悉的“橡树空地”,大部分是由大果橡树所组成的。
工程师们没有发现绝热体,但他们从这些草原战争中的老战士身上仿制出了它。植物学家们能够谈出那个有着两万年长的战争史。其记载包括有压在泥炭中的一部分花粉颗粒,一部分被扣在后方和被遗忘在那儿的残留下来的植物。这些记载说明,森林的前方在某时曾退到苏必利尔湖,但某时也曾推进到南部。有一个时期,它曾向南推进得那么远,以致云杉和其他一些“后方的哨兵”品种,也曾生长到威斯康星南部边界和更远的地方。在这里,所有的泥炭沼泽的某一层中,都可发现云杉的花粉。不过,大草原和森林之间通常所有的战线,大约就是现在它所在的地带,所以,战争的结果是个平局。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中有一个是那些盟友们,它们先支持这一边,然后又支持另一边。因此,兔子和老鼠在夏天扫荡了所有的草本植物,到冬天则又剥着所有幸免于火灾的小橡树苗的皮。松鼠在秋天贮藏着橡实,并在其他季节里也靠此为生。六月的甲虫,幼年时期破坏着草原的草皮,成年期则又使橡树失掉了叶子。如果没有这种盟友们时左时右的不坚定立场,从而使任何一方都可能取得胜利,那么,在今日的地图上,我们就看不到如此多姿多彩的草原和森林土壤的镶嵌画了。
乔纳森·卡弗11给我们留下了一幅非常生动的在有人居住以前的草原边界的写照。一七六三年十月十日,他到过布卢·芒德斯,这是靠近戴恩县西南角上的一群高山(现在已被树林所覆盖)。他说:
“我登上了最高的一座山峰,因此能够瞭望这个地区。在数英里内,除了小小的群山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这些群山从远处看来就像是一些尖顶的干草垛,上面没有树。只有寥寥几个小山核桃树林和矮小的橡树遮盖着某些山谷。”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种新的动物——拓荒者——介入了这个平原战场。本来他们并未打算介入,他们只是耕耘着足够用的农田,然而却让草原丧失了它自古以来就有的盟友——火。小橡树立即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草原,原来是平原的地方成了布满了种植着树木的农场。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有所怀疑,就去数数威斯康星西南部的无论哪一个“地垄”上的一棵树上的年轮。除了最老的树,所有这些树木,其年代都要上溯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正是火在平原上熄灭的时期。
约翰·缪尔是在这个时期,在马凯特县长大的,这个时期也正是新的树林在古老的草原上横冲直撞,并用一丛丛小树席卷着“橡树空地”的时候。他在《童年和青年》一书中回忆道:
“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平原上的沃土上,曾为火生长着那样稠密高大的草,以致没有树能在草原上生存。如果那儿没有火,这些美丽的草原——标志着这个地区的面貌的草原,早就被浓密的森林所覆盖了。农民预防火的蔓延像‘橡树空地’的出现一样快,小树逐渐长成(扎下根来)树木,并形成了高高的小树林,它们长得那么稠密,以致要穿过它们都很困难,所有阳光沐浴着的橡树空地的痕迹都消失了。”
因此,拥有一棵大果橡树的人拥有比一棵树更多的东西。他拥有一个历史图书馆,并且在演变的剧场中有一个预定的座位。在有洞察力的眼光看来,他的农场标着草原战争的徽章和标记。
空中舞蹈
当我知道每逢四月和五月的晚上,在我的树林的上空都可以看到这种空中舞蹈的时候,这个农场属于我已经有两年了。自从我们发现了它,我们全家就几乎连一次表演也难得错过。
表演在四月的第一个暖和的夜晚,六点五十分准时开始。每天幕布拉开的时间要比前一天晚一分钟,这样直到六月份,这时的时间是七点五十分。这种变化的幅度是由虚荣心所支配的,因为舞蹈者要求一种零点零五英尺烛光12的浪漫亮度。可不要迟到,而且要静静地坐着,以免惹恼了它而让它飞走了。
舞台道具,和开场的时间一样,也反映了演出者的情绪性要求。舞台一定要在一个露天的树林或灌木丛中的圆形凹地上,在它的中央必须是一片苔藓,一层不长任何植物的沙子,一块裸露地面的岩石,或者是一段光秃秃的道路。为什么雄丘鹬这样坚持要一块光秃秃的舞蹈地面,最初我也很糊涂,但是,现在我想,问题在于它的腿。丘鹬的腿是很短的,因此它的各种神气活现的样子在浓密的牧草和野草中,是无法取得优势的,它的女士也无法看见它的样子。我这里的丘鹬要比大部分农民们那里多,因为我有着较多的苔藓沙地,这些沙地太贫瘠,因此连草都长不出来。

知道了地点和时间,你就让自己坐在舞场东面的一丛灌木下面,等待着,在夕阳的映照下望着丘鹬的到来。它从某个邻近的树丛中低低地飞来,落在光秃的苔藓上,并立即开始了序幕:一连串古怪沙哑的“嘭嗵”声,其间有两秒钟的间歇,听起来特别像夏天里夜鹰的叫声。
突然,“嘭嗵”声停止了,这只鸟拍打着翅膀,兜着圈子,盘旋着向天空飞去,并发出音乐般的颤动着的叫声。它飞得越来越高,盘旋的幅度也越来越陡和越小,而叫声却越来越高,直到这位表演者在空中成为一个小斑点为止。这时,事先并不警告,便突然像一架失去控制的飞机一样翻落下来,同时发出一阵让三月的东蓝鸲也要羡慕的、柔和而清脆婉转的啼鸣。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它转为平飞,并落到它曾发出“嘭嗵”的地面上,通常总是一点不差地落在它开始表演的那块地方。在那里,它又恢复了“嘭嗵”。
天色很快就变得很黑,所以看不见在地面上的鸟了,但是你能看见它在空中的飞翔达一小时,通常这就是它演出的持续时间。不过,在有月光的夜里,它可能还会继续,在幕间休息后,一直持续到月光消失的时候。
在破晓时,演出会再次进行。在四月初,最后的幕布拉下来时是清晨五点十五分;这个时刻每天提前四分钟,一直到六月,这时,本年度的演出就在三点十五分时闭幕了。为什么在变化幅度上有这样的差别?唉,我想,恐怕是黄昏时的风流已卖弄得疲倦了,因为它只使用了五分之一的相当于它在日落时开始空中舞蹈的光就停止表演了。
大概幸亏是,不论人们怎样专心地研究着数以百种的树林和草地上的小戏剧,人们仍然永远不能全部掌握有关它们中的任何一种的最明显的行为。关于空中舞蹈,我还不明白的是:那位女士在哪儿?那么,如果她在那儿,她正好表演哪一部分?我常常看见两只丘鹬在同一个“嘭嗵”地面上,而且有时两只还一起飞翔,但它们从不在一起发出“嘭嗵”的声音。这第二只是一只雌鸟,还是一只雄的竞争对手?

另一点不知道的是:那悦耳的嗓音也许是它的机械功能?我的朋友彼尔·菲尼,曾用一只网扣住了一只正在“嘭嗵”的鸟,并拔去了它外面主翅上的羽毛,结果,这只鸟还在“嘭嗵”和啼叫着,但再也没有嘁嘁喳喳的颤动声音了。不过,这样一种实验很难就认为是一个结论。
还有一个未知的问题是:雄鸟的空中舞蹈持续到求偶的哪一阶段?我的女儿有一次曾看见一只鸟在离一个里面有孵化了的蛋壳的鸟窝二十码的地方“嘭嗵”着。难道这就是它的情侣的窝?也许这个秘密的家伙在我们还未发现它的时候,已经犯了重婚罪?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问题,都留在那深沉的黄昏的神秘之中。
空中舞蹈的戏剧,每夜都在千百万个农场中表演着,农场主们却为没有娱乐而叹息着,而且总有一个错觉是,娱乐只有在剧院里才能找到。他们靠土地活着,而不是为土地活着。
就那种认为一种猎鸟只是为了做靶子,或者该被人优雅地放在一片吐司上的说法,丘鹬是一个生动有力的驳斥。除了我,没有人会情愿在十月里去打丘鹬。而且,自从发现了空中舞蹈后,我发现自己只要打上一两只就够了。因为我必须肯定,在四月来到时,在日落时的空中,我还能再度见到那些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