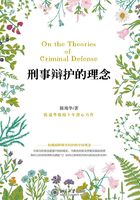
四、“五形态分类法”的局限性
迄今为止,“五形态分类法”得到了律师界的广泛接受。究其实质,这些形态的分类标准无非是辩护的目标和辩护的方法。“五形态分类法”的提出,显示出我国律师界对刑事辩护形态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进展。这五种辩护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事辩护的一些规律,也与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保持着同步性。
但是,由于受司法制度的种种限制,律师很难完全独立地从事某一类型的辩护活动,而不得不在辩护实践中进行一定的妥协。而在逻辑上,有些辩护形态相互间存在着一定的重合或交叉。这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在那种定罪与量刑没有完全分离的审判程序中,律师的量刑辩护与无罪辩护经常会发生冲突,量刑辩护的空间会受到无罪辩护的挤压;二是在法院无罪判决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无罪辩护的空间越来越小,很多无罪辩护都在发挥量刑辩护的效果;三是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实施的情况下,程序性辩护的成功率极低,很多程序性辩护也具有与量刑辩护相似的功能;四是无罪辩护与证据辩护、证据辩护与程序性辩护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难以保持独立性;五是罪轻辩护是在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妥协性。以下依次对这几个问题作出简要的分析。
真正独立的量刑辩护建立在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的制度基础上。英美法实行的就是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审判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假如被告人作出了无罪答辩,法院将组织陪审团专门审理定罪问题,法官在陪审团作出定罪裁断的前提下,再来组织量刑听证程序。而假如被告人选择的是有罪答辩,法院就不再组织陪审团对定罪问题进行审理,而直接举行量刑听证程序。因此,只有在陪审团确定被告人构成犯罪或者被告人选择有罪答辩之后,律师才有机会进行专门的量刑辩护。18
我国2010年开始启动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并没有确立这种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审判程序,量刑程序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19假如被告人当庭作出有罪供述,律师也放弃了无罪辩护机会,那么,法院对定罪问题的审理将变得大为简化,可以对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尤其是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法庭审理实质上变成一种量刑审理程序。在此情况下,律师可以围绕着被告人的量刑问题提出较为独立的辩护意见。但是,假如被告人当庭拒绝认罪,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法院将按照普通程序对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交叉审理,也就是将法庭调查区分为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将法庭辩论分为定罪辩论和量刑辩论,并在统一的裁判文书中分别就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裁判。在此类案件中,律师假如放弃量刑辩护,就只能进行纯粹的无罪辩护。但假如律师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提出辩护意见,其量刑辩护有可能与无罪辩护发生冲突。20
从逻辑上看,量刑辩护的前提是对被告人构成犯罪不持异议。但是,律师一旦提出无罪辩护的意见,即意味着要完全推翻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或罪名。在一个对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交叉审理的诉讼过程中,律师很难同时兼顾无罪辩护和量刑辩护,经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律师对无罪辩护意见的坚持,会大大压缩量刑辩护的空间。毕竟,一个试图推翻公诉方指控罪名的辩护律师,经常不愿意全面讨论对被告人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问题。这使得量刑辩护经常流于形式,无法起到说服裁判者作出有利于被告人裁决结论的效果。另一方面,律师所提出的量刑辩护意见,会程度不同地削弱其无罪辩护的效果。律师既然愿意讨论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幅度,那就意味着他对被告人构成犯罪这一点是不持异议的。既然如此,律师的辩护意见不就自相矛盾了吗?其无罪辩护不也就被自己所否定了吗?
在最高人民法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曾经有法律学者主张建立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审判程序,但这一改革方案没有得到采纳。最高人民法院最终确立了所谓“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21可以说,在不确立专门的量刑审理程序的情况下,要保证律师有一个独立的量刑辩护空间,确实是十分困难的。除非律师放弃无罪辩护,否则,这种量刑辩护与无罪辩护发生冲突、无罪辩护挤压量刑辩护空间的问题,就将始终存在。
在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无罪辩护虽然很难达到说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效果,有时却可以促使法院作出从轻量刑的裁决。特别是在那些社会影响较大、法院难以独立审判的案件中,律师的无罪辩护尽管达到了积极的效果,使得公诉方的指控受到了根本的动摇,却根本无法说服法院作出宣告无罪的判决。在此情况下,一些法院选择了一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也就是认可公诉方的指控罪名,但在量刑上却不作出较为严厉的处罚,而选择程度不等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这一裁判方式,一些律师认为无罪辩护达到了说服法院宽大处理的效果,因此促进了量刑辩护的成功。有人甚至据此认为,这种无罪辩护所达到的从轻量刑效果,恰恰是量刑辩护所无法达到的。“法乎其上,得乎其中;
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如果仅仅选择量刑辩护,法院即使作出从轻处罚,所选择的从轻量刑幅度也是十分有限的;而只有选择无罪辩护,使法院受到强大的压力,才有可能说服法院选择幅度较大的从轻处罚。
应当承认,这种“通过无罪辩护来达到量刑辩护效果”的辩护方式,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有其存在空间的。由于多种原因,无罪辩护的完全成功的确会面临重重困难。22特别是在律师以“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为由提出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院尽管很少作出无罪判决,却经常采取“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误判案件,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都显示出这种“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在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中是普遍存在的。23但是,这种以无罪辩护来推动法院作出宽大处理的现实,恰恰是中国刑事司法出现“病症”,亟待“疗治”的证据,属于刑事司法陷入困境的标志。从立法原意和司法规律来看,无罪辩护所要达到的其实就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裁判结局,法院要么选择有罪裁判,要么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选择“疑罪从轻”的处理方式。而那种以法院的暂时妥协为依据来否定量刑辩护独立性的观点,其实是不理性的。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律师完全不必探索量刑辩护的规律,也无须在量刑辩护方面进行必要的防御准备,更不必为追求最好的量刑裁决结果而展开积极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了。这在大多数案件没有无罪辩护空间的司法环境中,其实是非常有害的一种论调。
同时,片面地夸大无罪辩护对于量刑裁判的积极作用,还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律师不经理智的评估和选择,动辄在大量案件中选择无罪辩护,使得无罪辩护存在着被滥用的危险。而在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下,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几乎很难再有充分地、专门地从事量刑辩护的机会。这会造成大量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特别是酌定从轻量刑情节)难以进入法官的视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无法反映到法官面前,公诉方的量刑建议甚至会变成一种压倒性的意见,对法院的量刑裁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恰恰难以维护量刑裁决的公正性。
从实质上看,量刑辩护是一种完全独立于程序性辩护的辩护形态。如果说程序性辩护的目标在于说服法院作出宣告无效之裁判的话,那么,量刑辩护的归宿则在于促使法院作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裁判结果;如果说程序性辩护的手段主要是挑战侦查、公诉和审判程序的合法性的话,那么,量刑辩护的操作方式则在于挑战公诉方提出的量刑情节,推翻公诉方提出的量刑建议,提出新的量刑情节,说服法院接受本方提出的量刑意见。
但在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辩护律师对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合法性的质疑,很难促使法院作出宣告无效的裁决。一些法院针对那种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特别是刑讯逼供、诱惑侦查等违法侦查行为,也试图采取另一种形式的制裁措施,以示对这些程序违法行为的零容忍,以及对程序违法行为受害者的救济和抚慰。这种制裁通常都是通过作出从轻量刑的方式实施的。结果,对于侦查人员存在的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法院不是作出宣告无效的裁决,而是在采纳有争议的控方证据的前提下,对被告人作出较为宽大的刑事处罚。例如,针对辩护律师提出的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问题,法院一经查证属实,就可以此为根据,对本应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改判较为轻缓的刑事处罚。这一裁判逻辑曾经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俊岩涉嫌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判决中得到体现24,后来在著名的刘涌案件中再次得以贯彻。当然,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所做的那份有争议的判决书,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再审程序予以撤销。25不仅如此,就连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也对侦查人员滥用诱惑侦查措施的程序违法行为,采取了维持有罪裁决、量刑宽大处理的应对措施。比如说,针对侦查人员在毒品案件中采取的“犯意引诱”“双套引诱”和“数量引诱”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就明确表达了拒绝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政策。26
作为一种进攻性辩护,程序性辩护本来属于挑战侦查、公诉和审判行为合法性的辩护活动,却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院的量刑结果,达到了说服法院从轻量刑的效果。这显示出中国法院在面对那些结构性的程序违法行为时,具有一种既要实施制裁又无法过度制裁的微妙心态。法院对程序违法行为予以适当的制裁,可以向社会宣示维护法律程序、禁止程序违法行为的理念,避免成为侦查机关程序违法行为的“共犯”;而避免采取宣告无效的过度制裁措施,则是为了避免过度刺激侦查机关,防止出现因为排除控方关键证据而不得不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局面。作为一种带有妥协性的裁判结论,法院从轻量刑的处理方案对辩护律师也具有程度不同的诱惑力,也容易使其误以为通过程序辩护就可以达到量刑辩护的效果。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这种通过程序性辩护来达到说服法院从轻量刑之效果的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而只在特定案件中或者特定地区的法院审理过程中有其存在的空间。律师假如将量刑辩护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挑战诉讼程序合法性的辩护思路上,将很难取得普遍的辩护成功。
很显然,量刑辩护具有其独立的诉讼目标,也具有一系列独特的操作方式。程序性辩护尽管在部分案件中具有影响法院量刑结果的辩护效果,却是与量刑辩护迥然不同的辩护形态。正如律师无法以无罪辩护、罪轻辩护来取代量刑辩护一样,那种指望通过程序性辩护来偶然地影响法院量刑结果的观念,也注定无法取得普遍的辩护成功。
本来,无罪辩护是以推翻公诉方指控的罪名为目的的辩护活动,证据辩护则包含着对公诉方证明体系的推翻活动,两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那种通过论证公诉方的证据无法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辩护活动,则既是无罪辩护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证据辩护的一种类型。这显然说明,在论证公诉方的证据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的问题上,无罪辩护与证据辩护确实存在着交叉情形。
而程序性辩护与证据辩护的交叉则显得更为明显。本来,狭义的程序性辩护是通过论证侦查行为或审判行为的违法性,来说服法院作出宣告无效之裁决的辩护活动。其中,律师针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所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所追求的是法院在宣告侦查行为违法性的基础上,对有关证据的证据能力作出否定性评价,也就是作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决。这里所说的“排除非法证据”,也就是否定公诉方证据的证据能力。而对公诉方证据能力的否定,也同时属于证据辩护的一种具体形态。这说明,在排除公诉方非法证据问题上,程序性辩护所强调的是对侦查行为违法性的宣告,而证据辩护所重视的则是对控方证据之证据能力的否定。两者说的其实是一回事。
辩护形态的交叉还体现在证据辩护的独立性方面。前面所说的“证据辩护”,更多地体现在对公诉方证据的挑战方法上面。但是,辩护方除了要挑战公诉方的证据以外,还有可能通过提出证据来论证本方所主张的案件事实,如论证本方所主张的无罪事实,论证本方所提出的量刑事实,论证本方所申请的新的轻罪事实,或者论证本方所申请的程序性争议事实。而在这种主动论证本方案件事实的场合,所谓的“证据辩护”就更多地依附于其他辩护形态,成为其他辩护的具体方法,而失去了基本的独立性。
这主要涉及“罪轻辩护”的正当性问题。迄今为止,律师界普遍承认这种辩护的正当性。不过,这更多的是从司法现实角度所做的选择,也带有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妥协的意味。假如我国法院不采取“变更起诉罪名”的做法,而将刑事审判定位为“裁判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上面,那么,这种所谓的“罪轻辩护”也就不存在制度空间了。然而,真正的司法现实却是法院不甘心只做“司法裁断”,而愿意发挥继续追诉的作用,对公诉方的指控“拾遗补漏”,充当“第二公诉人”的诉讼角色。在此情况下,辩护律师假如仅仅论证控方指控的罪名不成立,那么,仍然无法达到说服裁判者接受本方诉讼主张的效果;辩护律师要说服这些充满追诉欲望的法官,就需要在推翻公诉方指控罪名的同时,提出另一个较轻的罪名,使得法官按照辩护方提供的“台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结论。这种辩护方法虽然有迫不得已的考虑,但就辩护效果而言,却是迁就和附和了法院的不合理要求,使得无罪辩护的空间受到较大幅度的挤压,也影响了无罪辩护的效果。在一些略显极端的案件中,个别辩护律师考虑到说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极端困难,有可能对那些本来确信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违心地选择了罪轻辩护。
当然,在辩护形态的选择上,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辩护律师,都不具有太大的主动性。考虑到刑事辩护主要是“说服法官的艺术”,辩护方不可能无视法官的裁判方式,而完全提出自己的独立辩护意见。对罪轻辩护的选择,也是辩护律师为说服我国法官所做的无奈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辩护形态所引发的异议,与法院变更起诉罪名所引起的争议,其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要促使律师放弃这种带有妥协性的辩护策略,对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就需要法院放弃变更起诉罪名的做法,回到“对公诉方指控罪名是否成立作出裁判”的原来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