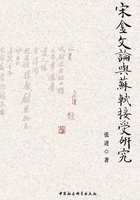
序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为人、为文、为政,皆堪称最上乘者。苏轼一生尽管不顺,跌宕起伏,辗转南北,流离失所,亲人半程而逝,其情感,或缱绻缠绵,或豪放恣肆,然其人生态度,不卑不亢,不喜不怒,独立不惧,百折不摧,实为人所共称。南宋初期,苏轼得到了高宗的肯定,特赠资政殿学士、朝奉大夫;又被孝宗赐谥号“文忠”、追赠为“太师”。其为政、为文,均得到高度赞誉。
苏轼的文学成就,历来为人所称道。其文、赋、诗、词等文体,境界开阔,皆开创一代之风气。苏轼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把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悟融入他的文学创作之中,通过文学形象、意象、境界提炼出来,给人以无限的寻绎、玩味、体悟。这就是他自己倡导的一种有别于唐人诗的“意理”,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而此“意理”,即为诗歌之理趣,也即他的灵心、妙慧、睿智。
苏轼的文学理趣,与他熟稔佛教“空观”(śūnyatā)似乎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的“空观”是全部佛教哲学的核心,是佛教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石。“空”,早在《奥义书》(Upanisad)中,就被赋予哲学意义。他们认为“空”是世界产生的根源和归宿。[1]佛教的“空”(śūnya),明显来源于婆罗门教的“空无”思想和上古印度数学上“零”的意义。大乘佛教不只强调了空无所有,还凸显了它的虚空不实,即指现象界的虚幻不真,也即所谓的不真则空。[2]世界是虚幻的,物质是虚幻的,人也是虚幻的,一切皆空。正是这种“空观”,导致了佛教一般信众对现实世界的怀疑、否定,而深入理悟者,则能在怀疑或否定中予以超越。苏轼就是这样一位深刻理悟者。因此,在经验世界中,他能处处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佛教“空观”[3]来指导自己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当面对人生的沉浮时,他非常坦然地以佛教的“梦空”来理悟。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凭吊一番三国时期的风流人物后,对人世间的沧海桑田、宦海沉浮,发出了“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和喟叹。有了这样一种人生感悟:世事苍凉,人生如梦,又何必去执着不放呢。尽管人间如梦亦如电,人生虚幻不实,但仍然可以洒酒邀月,抒发豪迈之情、旷达之意。正是这样的“梦空”观念,才使得东坡能把一首抒发人生失意、坎坷的词,写得如此境界雄浑寥廓,气势磅礴恢宏。他的“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慈湖夹阻风》),是与《赤壁怀古》情调、理趣一致的。当身处自然山水和人事之中,他深切地感悟到了其中的变幻莫测,虚实不定。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看山总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人的见(drsti;darśana)闻(śruti;śrutvā)觉(鼻舌身:ghrāna-jihvā-kāya)知(pratyabhijñā)是六识(sad-vijñāna:眼耳鼻舌身意)作用于外境(bāhya-visaya)而所得,往往如瞎子摸象,以偏概全。尤其是身处其中,见识受限,真境蒙蔽,幻实莫辨。再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上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正道出了人间的虚幻,时间的易逝,岁月的无情,不管你如何努力进取、拼命挣扎,也不过是留下几点飞鸿爪印,如果你执着了这些爪印(功名利禄),则会陷入世俗的樊篱之中,难以超脱,进入自觉、自由、自在的境界。这正是“幻空”观念在文学书写中的一种自觉作用。由是观之,东坡精神上的那种傲视苦难、超越痛苦的旷达洒脱、自富自在,正源于此。当探讨诗歌的艺术真谛时,东坡认为诗语之妙,在于“静空”。所谓“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静空”,即佛教以静而观空。“静”(śānta)最早是上古印度对禅定的另一种称谓。“禅定”是指在寂静的状态下,心不散乱,神志专一,凝然沉思,静虑修习,弃恶扬善,观照宇宙,洞悉性灵。佛教兴起,吸取禅定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与自觉、觉他结合一起。佛教入华,禅定深入文学园地,深受文人喜爱。以禅入诗,以禅学诗,以禅喻诗以及“诗家三昧”说等[4],基本反映了唐宋好禅文人的诗歌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唐代,王维就禅静观与诗歌的创作有机地结合一起,如“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蓝田山石门精舍》)、“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县兴上人山院》)、“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自云期”(《早秋山中作》)、“食随鸣盘巢鸟下,行踏空林落叶声”(《过乘如禅师萧居士嵩丘兰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等,将寂静空灵的禅思融入诗歌之中,开启了诗歌静空观的范例。东坡喜好禅,坐禅、参禅,其禅学水平绝非一般崇佛文人所能比。因此,他把读诗、作诗与参禅、悟佛联系起来,深有感触:“暂借好诗消永昼,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在东坡的思想世界里,诗与禅,静与动,空与有,不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其澄静之心观照大千世界,动静喧寂,相互映衬,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此种静空观,不只是对自然景物的一种深邃观照,还把社会人事的处境融入其中,在审美的景物之中暗喻着人生态度。东坡以佛教“空观”观察世界、体悟人生,自然是有别于他人的认知而独树一帜。我以为,这正是东坡诗歌创作“理趣”的思想渊源。
东坡这样的理趣,成就了他的文学写作的创新和拓展,给北宋文学吹送了缕缕春风春意,令诸多文人欣喜不已,心向往之。然而,成败萧何,至南宋、金,文人在敬佩、盛赞东坡的同时,也有对其批评者,如刘克庄、朱熹、李清照、严沧浪、元好问等。以诗为词、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批评意见似乎明确地概括了东坡文学创作的特征。不过,东坡毕竟是伟大的文学家。后代见仁见智的批评,丝毫不足以影响其巨大成就和突出贡献。而东坡的文学影响越大,也就越具有品尝的韵味和探究的奥妙。
《宋金文论与苏轼接受研究》一书是家姊张进教授第二部研究苏轼的专著。此前,她与张惠民教授合作,出版了《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而本书的写作,历时20余年。其中部分内容尝以单篇论文发表。此次她在已发表的系列论文基础上,广泛听取了学界同行的意见,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勒成专著,出版之前,嘱我为序。由此,我得以先睹。该书所关注的重点是宋金(主要是南宋、金)时期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对东坡的接受。这种接受,并不是简单的赞誉或否定,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思想、社会、文学批评的背景。如,朱子批评东坡,着眼于理学、道学;易安批评东坡,则关注于词体;沧浪批评东坡,则集于其才学,如是等等。然而,这些批评家在批评的同时,更多的是主动的接受,是被深刻地影响。该书这样详尽的梳理和探究,似乎更近于实际状况,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个鲜活的东坡形象:他是那么的伟大,却又不是完美无缺。这就有别于长期以来文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研究对象,因为研究者注入的强烈情感而被无限度地放大;也可以让读者了解宋金批评家接受东坡的心理过程和批评实践,体察出文学史的意义。我以为这是该书最值得称道之处。
我和姐姐虽然工作、生活不在一个城市,但是每当看到她的论文和著作出版,都为她欣喜。她主持的《王维资料汇编》(全四册,中华书局版)于学界获得了较高的声誉。每每看她的文字,便不由得想起了我们一起成长的情景。姐姐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的好学生、学生干部,而我的小学中学时代是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步的。在那个年代,我的语文写作水平和能力多半是在姐姐的帮助或辅导下提高的。她曾两次当知青插队,之后在县委机关工作。1977年顺利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大学四年的学习,使她一头扎进古代文学与古代文论的研习中,毕业后担任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期间又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宋元明清文学进修班学习。1993年后转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兼任陕西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生导师。及至退休以后,仍然笔耕不辍,收获多多。我为她的这种治学精神而感动,也衷心地祝愿她心安、体康、笔健、事顺。
普慧
2018年元月于
成都四川大学中兴村
[1] 《唱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IX 9:1:“问曰:‘此世界何自而出耶?’曰:‘空(ākāśa)也。维此世间万事万物,皆起于空,亦归于空。空先于此一切,亦为最极源头。’”(《五十奥义书》,徐梵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2] 元康《肇论疏》:“诸法虚假,故曰不真;虚假不真,是故名空。”(张春波《肇论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页)
[3] 对苏轼影响深远的佛教“空观”主要为“梦空”(svapna-śūnya)、“幻空”(māyā-śūnya)和“静空”(śānta-śūnya)。
[4] 一般认为,以禅入诗是指王维诗歌创作引入禅语、禅趣,以禅学诗由苏轼提出,以禅喻诗由严羽《沧浪诗话》提出,诗家三昧是由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