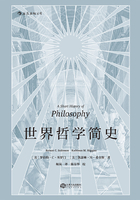
柏拉图:形而上学家抑或高明的幽默大师?
柏拉图是哲学界最伟大的作家,也是戏剧天才。当然,他很幸运,有很多作品留存了下来。(不过,这说的是他的哲学作品。柏拉图在决定献身于哲学时焚烧了自己的全部戏剧作品。)柏拉图还创建了一座学校,即学园,由此确保自己的作品和观念(以及苏格拉底的教义)得到传承。
实际上,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柏拉图更具有才华、更动人、更风趣,也更深刻。我们来看看下面两段分别摘自《理想国》和《会饮》的简短对话:
苏:那么色拉叙马霍斯,请你从头回答我。你不是说极端的不正义比极端的正义有利吗?
色:我的确说过,并且我还说明过理由。
苏:那么好,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究竟怎样?你说它们俩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吗?
色:这是明摆着的。
苏:正义是善,不正义是恶?
色:我的朋友,你真是一副好心肠。像我这样主张不正义有利,而正义有害的人,能说这种话吗?
苏:那你怎么说呢?
色:刚刚相反。
苏:你说正义是恶吗?
色:不,我认为正义是天性忠厚,天真单纯。
苏:那么你说不正义是天性刻薄吗?
色:不是。我说它是精明的判断。
苏:色拉叙马霍斯,你真的认为不正义是既明智又能得益吗?
色:当然是的。至少那些能够征服许多城邦许多人民的极端不正义者是如此。你或许以为我所说的不正义者指的是一些偷鸡摸狗之徒。不过就是小偷小摸之徒吧,只要不被逮住,也自有其利益,虽然不能跟我刚讲的窃国大盗相比。
苏:我想我并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不过你把不正义归在美德与智慧这一类,把正义归在相反的一类,我不能不表示惊讶。
色:我的确是这样分类的。
苏:我的朋友,你说得这样死,不留回环的余地,叫人家怎么跟你说呢?如果你在断言不正义有利的同时,能像别人一样承认它是一种恶一种不道德,我们按照常理还能往下谈;但是现在很清楚,你想主张不正义是美好和坚强有力;我们一向归之于正义的所有属性你要将它们归之于不正义。你胆大包天,竟然把不正义归到道德和智慧一类了。
色:你的感觉真是敏锐得了不起。
苏: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我觉得你说的是由衷之言,我决不畏缩、躲避,我决定继续思索,继续辩论下去。色拉叙马霍斯,我看你现在的确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在亮出自己的真思想。
色:这是不是我的真思想,与你有什么相干?你能推翻这个说法吗?
苏:说的不错……
——《理想国》(348b8-349b1)
苏:一个盼望的人所盼望的是他缺少的、还没有到手的,总之是他所没有的,是本身不存在的,不在那里的;只有这样的东西才是他所盼望的、他所爱的。
阿:确实是。
苏:那我们就总结一下所说的话。这就是:爱神首先是对某某东西的爱,其次是对他所欠缺的东西的爱。是不是?
阿:是的。
苏: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回想一下,你在颂词里把爱神说成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提醒你。你大致是这样说的:由于爱美好的东西,才把自己的活动安排成那个样子,因为丑的东西不是神所爱的。你是不是这样说的?
阿:不错。
苏:你说的很妥当。朋友,既然如此,爱神所爱的就是美的东西,而不是丑的东西咯!
阿:是。
苏:我们不是也同意过一个人所爱的是他缺少的、没有的东西吗?
阿:是的。
苏:那么,爱神就缺少、没有美的东西咯!
阿:必然如此。
苏:那缺少美、没有美的,你说美吗?
阿:不能那么说。
苏:既然如此,你还主张爱神是美的吗?
阿:苏格拉底啊,恐怕当初我只是信口开河,并非真懂所说的话的意思。
苏:你说的还是很动听,阿伽通啊,可是我还是有个小问题:你是不是认为好的东西也是美的?
——《会饮》
苏格拉底的命运笼罩着每部对话,让每段交谈读来都令人心酸,让每个论证都显得高贵。实际上,柏拉图最初把苏格拉底当作戏剧角色来使用,只是后来才把他当作哲学代言人,由于极为成功,柏拉图因此就继续这样使用,即便柏拉图阐述和主张他自己的观念时,他也依托苏格拉底来进行。
这里就引发了大家熟悉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柏拉图何时忠实于苏格拉底,何时只是把苏格拉底用作自己言辞和哲学的发言人呢?我们如何认定他们两个何时一致,何时只是柏拉图个人的观点?更复杂的是,对话形式固有的困难使我们无法确保对话作者(柏拉图)的观点等同于对话中发言人的观点。比如,在《会饮》中,柏拉图向我们呈现了七个发言人彼此矛盾的观念,这绝不意味着他自己认同其中任何发言人,包括苏格拉底。(在某些晚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完全消失了。)
首先,柏拉图的哲学始于对苏格拉底毫无保留的信赖,甚至可以说,他对苏格拉底过于崇敬、毫无批判,这尤其体现在对苏格拉底最后日子的叙述上。对苏格拉底的审判、监禁和处死,分别记录在《申辩》《克力同》和《斐多》之中。此外,柏拉图还创作了大量其他对话,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与他同时代最聪明的思想家(也有些不那么聪明的思想家)侃侃而谈,其中包括阿里斯托芬、阿尔喀比亚德、巴门尼德、芝诺、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通过苏格拉底对各式各样论点的驳斥,柏拉图开始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说,柏拉图的早期对话,那些特别关注伦理、做个好人以及德性定义的对话,是对苏格拉底观点的合理却大加渲染了的阐释。而晚期对话,那些更多关注知识和宇宙论问题的对话,几乎可以肯定是柏拉图自己的哲学。
柏拉图的宇宙论,包括毕达哥拉斯数的世界观、赫拉克利特流变和逻各斯的世界观,以及巴门尼德永恒不变且不可知的实在观。不过,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他的形式论,当然它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有所显现。这个理论设定了“两个世界”的宇宙论。一个世界是我们日常的变化世界。另一个世界则是充满了理想“形式”的理念世界。第一个世界是“生成的世界”,如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不断流变;第二个世界是“存在的世界”,如巴门尼德所要求的,永恒不变。柏拉图这个新观点的魅力在于,首先,这两个世界相互关联,而不像巴门尼德和某些智术师认为的那样彼此毫无关系。这个生成的世界,即我们身处的世界,由存在的世界即理想形式的世界决定,前者是对后者的“分有”。因此,日常世界背后有不变的逻各斯,这个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形式的理想化,它决定了那个流变的世界。此外,这个理想的形式世界并不像巴门尼德所说的是不可知的。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通过理性窥见这个世界。
这种对理念世界的窥视,在数学和几何领域有现成的例子。比如,我们可以以三角形定理的几何证明为例。我们在黑板或纸上画的三角形并非绝对的三角形。事实上,线条模糊、弯曲,角也没有完全形成,可以说,它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三角形。然而,通过这个不怎么样的三角形,我们能够证明三角形的某些原理。这是如何可能的?
毕达哥拉斯通过他的理论已经表明,世界的本质可以在数、比例中找到。毕达哥拉斯认为,最真实的不是事物的质料,而是事物的形式。因此,数学和几何研究就是研究实在的本质结构,而不管具体存在者和关系注定消逝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说,数学和几何研究让我们“透过”日常世界的流变,理解某种不变的本质之物。同样,我们“透过”画得不怎么样的三角形看到三角形本身的理念或形式。可以说,我们所证明的与其说是所画的蹩脚三角形的定理,不如说是所有三角形的定理,因为它们都是三角形本身的实例。当然,我们所画的蹩脚的三角形也与定理相符,因为它也是三角形的表象。但是,说它是三角形,只是因为如下事实:它是在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三角形本身的表象。即使如此,我们显然仍能够认识三角形本身,即三角形的理想形式。我们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认识它。
同样,不论怎样,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理想形式的表现。回顾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形象不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何种意义上提出了形式论(不管他是否确实相信)。当探寻德性的“定义”时,他实际上寻求的就是理想形式,即德性本身。当探寻勇气、正义或智慧的定义时,他所寻求的是理想形式。当探寻“善”时,苏格拉底所寻求的也是所有善的事物、善的行为和善的存在者背后的形式。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苏格拉底通过各种尝试定义的反诘法和推理思考如此重要。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何苏格拉底如此坚决地宣称自己无知,坚持自己无法教授这些定义以及经由启发而产生的德性。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自己“看见”这些形式。我们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眼睛始终盯着这些理想形式,无论他是否向我们给出了非凡的定义本身。他之所以如此自信和坚定不移,甚至在面对死亡之际仍然如此,原因就在于此。
柏拉图在他的杰作《理想国》第七卷中给我们提供的图景,或许是关于形式及其使观看它们的哲学家头晕目眩最难忘的景象。在那里,他讲述了“洞穴神话”的寓言,它既关注于存在世界与生成世界(形式与世间万物)之间关系,也对哲学家面临的危险进行警告。这里的哲学家,柏拉图大概指的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后者试图向大众解释或阐明这些形式。
这个神话的开端是囚徒被束缚在洞穴之中,面对洞内墙壁。他们所看见、所认为的实在,其实是投射到墙上的影子。因此,苏格拉底进而解释到(根据柏拉图对寓言的叙述),我们当成实在的东西基本上是由影子构成的。这不是说影子是不真实的。影子是真实的,但有比他们更真实的东西。因此,这里的区分类似于巴门尼德,是实在与幻象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真实程度的区分,是较高世界与较低世界的区分。
现在,我们假设其中某个囚徒,即哲学家,摆脱了束缚转过身去,生平首次把眼睛看向投射出影子的真实物体和火光。他能不头晕目眩吗?与现在看到的实在相比,他不觉得日常实在的影子很不完美吗?因此,哲学家在看到德性、正义和勇气的完美形式时,再与普通民众那些不完美、常常混淆的观念和行为加以对照,就会头晕目眩。随后,他的希望就会“高远”得多。如果这个哲学家返回到洞穴,并且试图告诉他的同胞他们身处的世界多么贫乏,他们的想法多么不足,这些人难道不会攻击甚至杀死他吗?苏格拉底自己的命运就是特别的例子,不过,形式意指的东西,具有更普遍、更深刻的意义。
形式论让柏拉图的哲学显得很抽象,像是宇宙论。事实上,柏拉图的哲学首先是政治哲学,《理想国》是极具争议的政治著作。但它也不只是单纯的政治学。维护和重新定义希腊城邦,需要全新的宇宙论,事实上,这是取代宙斯及其众神的新宗教。(在针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有一项就是不信雅典的诸神而引入“新神”。)
不用说,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与雅典城邦有许多共同点,但是它也呈现出令人不安的差异,其中许多还很极端。首先,它不是民主政体。在这方面,柏拉图与苏格拉底当然一致。统治权在那些富有洞见、头脑清晰的有德性的人手里,这些人就是哲学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为我们描述了哲学王的形象,无疑,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当时,这样的形象都会受到人们嘲笑。(至少从泰勒斯开始,关于哲学家心不在焉的笑话就没有消散过。)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奇异的结合体,独裁、等级、平等纷列其中。它是“自然”的贵族政体,基于天赋、出生的幸运和后天的教养。它是温和的独裁政体,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它不是迎合个体或个体利益的社会,相反,在这个社会中,个体和个体利益被认为要服从于共同善。比如,柏拉图提倡进行艺术审查,主张艺术的激励作用应以灌输恰当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为限。在这个社会中,人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自由地抚养自己的孩子,而是由国家来教育。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妇女被给予与男人相同的权力——这在当时是大胆的提议。最卑微的公民的幸福被认为与最伟大的公民的幸福同等重要。甚至,统治者没有特权,也不会必定幸福,反倒是具有令人又敬又怕的责任。柏拉图告诉我们说,幸福并不是为哪个特权阶级而备,而是针对整个城邦而言。
这种反民主的美好社会图景,很难与苏格拉底向来圣洁的好人典范(虽然古怪但善良的牛虻形象相容)。但是,《理想国》不只是纯粹想象国家的政治模型。它也倡导某种反思自我和世界的新方法。我们可能拒斥柏拉图描述的理想国中的独裁和不平等的方面,但不必抛弃《理想国》中的世界观。(实际上,柏拉图自己就拒斥了这个理想国模型,在他最后的对话《法义》中维护了某种较为含糊的政治观。)因此,我们也可以拒斥形而上学,不去相信绝对理念的世界,而不必放弃德性理念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哲学培养各种德性的重要性。可是柏拉图,类似于苏格拉底,向我们允诺的不只是乌托邦式的城邦和极不可信的形而上学。他也向我们展示了鼓舞人心的灵魂图景,我们借此可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正如我们此前提到的,希腊人,从荷马到德谟克利特,只是在最低程度上“相信”灵魂。他们承认,需要有某种称之为“气息”(即 psyche 的原初意义)的东西使身体具有生命,它会因死亡而离开身体。不过,这样的话,灵魂需要身体就像身体需要灵魂。没有灵魂,身体就是死的,但没有身体,灵魂就只是可怜的影子,毫无意义和价值。但在苏格拉底看来,灵魂有道德意义。它也比身体更重要。苏格拉底认为,灵魂在重要的意义上比身体更持久。(在这方面,他显然接近于毕达哥拉斯派关于灵魂不朽和灵魂轮回的学说。)
在《申辩》中,苏格拉底幻想死后可以不受干扰地沉浸在哲学思考的快乐中。他好像把死亡视为将要到来的休假,甚至认为它是某种治疗。①柏拉图后来的观点为我们理解这个灵魂概念提供了媒介。灵魂与我们的其余部分不同,它(部分)属于存在世界、永恒世界。因此,身体的丧失对它而言只是部分丧失(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丧失,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好人最终不会遭受任何恶,哪怕身体受到伤害甚至死亡,原因就在于此。
此外,如果灵魂(部分)属于理念世界,它就已经包含了形式的知识。因此,我们关于德性、美和善的知识就不是靠学习而来,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教授了。我们生来就具有这样的知识。它是“自然的”(字面意思就“出自”我们自己)。在《斐多》中,苏格拉底说,“为了完全认识某个事物,我们必须摆脱身体,只用灵魂的眼睛注视真实的实在。”因此,灵魂成了理智生活和道德生活的通道。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生活中唯一真正值得在意的事。
苏格拉底对话中最令人难忘和当之无愧的著名对话,无疑是《会饮》,它描述了晚宴后的聚会场景,虽然是虚构的,但场面欢快,苏格拉底与诗人和剧作家就“厄若斯”即爱欲的德性展开讨论与辩论。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也参与其中。或许,这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在《云》中受到的抨击进行的回应。(比如,阿里斯托芬在这部对话中饱受打嗝之苦。)此外,还有才华横溢的年轻悲剧作家泡赛尼阿斯和会饮的主人阿伽通。或许,书中最富戏剧性的人物是阿尔喀比亚德,他最晚出场,喝得酩酊大醉,受到苏格拉底有意冷落。在《会饮》中,苏格拉底主张,爱不只是对美的身体甚至美的人格的欲求,而且欲求某个更多的东西——即对美本身的爱。当然,“美本身”是形式。它使真正的爱者成为智慧的爱者,即哲学家。
《会饮》对美的强调反映了柏拉图思想的重要特征。关切美和秩序是整个柏拉图哲学的核心。美体现了人类的形式,最容易被认识,人们常常在对美的凝视中激起了对哲学的追寻。此外,对柏拉图而言,德性与美紧密相关。德性使灵魂和谐,就像美使脸庞或风景的各部分变得有序。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涉及各组成部分和谐的审美观念。审美观念在阐述伦理和政治观念中的核心位置,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仍继续存在,并且不断出现在后来哲学的各种观点之中,尽管很少再有古希腊人(或早期中国人)那样直截了当。
《会饮》有几个值得提及的具体特征。首先,在这篇较早的对话中,柏拉图并没有让苏格拉底完全代表他发言,对话的结果不只是苏格拉底的观点。阿里斯托芬做了奇特的演说,无论苏格拉底对其如何嘲讽,都令人难忘、凄美动人,很好地说明了爱的起源。(这个古代故事讲的是,人最初是双生体,后来被宙斯劈成两半,从此总是“努力在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其他发言者也指出,爱有风趣和实践的特征。
在对话的结尾,阿尔喀比亚德突然闯入,嘲弄苏格拉底,恶言相加,说他是负心人。不过,阿尔喀比亚德也提出重要观点,这个观点与苏格拉底自己的教义直接相互矛盾。他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但实际上并不认为),爱并不指向形式,而是指向特殊的个体,而且,个体的美和德性与爱并没有特别的相关性。(苏格拉底或许是个有德之人,但他显然也长得不怎样。相反,阿尔喀比亚德倒是相貌堂堂,不过臭名昭著。)似乎是,柏拉图斟酌之后,认为厄若斯既要有苏格拉底体现的理想特征,又具有苏格拉底所忽视的某种形而上的、神话般的依恋性。
《会饮》也是苏格拉底明确表明自己并非无知的对话。他说,他唯一确知的事就是爱。当然,这是因为他已然是(智慧的)爱者,但这也意味着他并不拥有智慧。尽管如此,苏格拉底甚至也没有宣称有关爱的知识是他自己的发现。相反,他把这种知识归于第俄提玛。(第俄提玛是否真实存在,远没有她是位女性更令人感兴趣,因为希腊哲学家从未在妇女那里听取过什么哲学建议。②)
最后,应该说,《会饮》除了充满洞见,还非常有趣。③它彻底表明,哲学可以深刻,但不必乏味。不幸的是,这方面没有得到学者们真正严肃的承认,人们对于柏拉图有诸多赞美之词,但却没有这样的说法:他不仅是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极为高明的幽默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