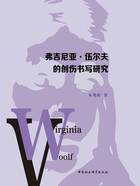
第二节 心理学视域中的伍尔夫研究述评
弗吉尼亚·伍尔夫因为其文学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艺术技巧的实验性与革新性而堪称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自191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起,她便受到了评论界的关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伍尔夫及其作品的评价和阐释见仁见智,他们从生平传记、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主义、伦理学、现代主义等角度来解读、分析她的作品,伍尔夫批评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对伍尔夫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和理论化。学界从政治、哲学、美学、文化、社会、语言学、叙事学、精神分析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层面,对伍尔夫的生活和创作及其关系展开了全方位的考察。此外,当代伍尔夫研究也致力于探讨伍尔夫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学集团、现代英国社会、女性主义运动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关于伍尔夫的种种考证,如伍尔夫与战争、伍尔夫与同性恋、伍尔夫与科学话语等也正在升起。其中,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始终是两个最主要的流派。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伍尔夫进行研究,虽然不能与一直占据国内外伍尔夫研究主潮的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相媲美,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学者将伍尔夫研究与心理学相结合,它在国外评论界一直被持续了下来,而且近年来呈现出升温的趋势。
20世纪对伍尔夫的心理分析主要是以传记研究的形式出现的。伍尔夫的日记和书信在50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的结集出版,1972年伍尔夫外甥昆汀·贝尔(Quentin Bell)所写的《伍尔夫传记》的发表,以及1969年伦纳德·伍尔夫去世后人们在他们夫妇二人留下的材料中发现的许多伍尔夫生平回忆资料,为进行伍尔夫心理传记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不少学者据此大显身手,以至于形成了伍尔夫研究的心理传记派(psychobiographi cal studies)。
一部分心理传记派批评家从精神分析的层面关注伍尔夫,从她的生活经历出发探讨她的精神状态及形成原因。这些精神分析传记有:吉恩·拉夫(Jean Love)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疯癫与艺术的源泉》、罗杰·普尔(Roger Poole)的《不为人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马克·斯皮尔卡(Mark Spilka)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哀伤的争吵》、斯蒂芬·特罗姆伯雷(Stephen Trombley)的《这个夏天她疯了》、路易斯·德沙尔弗(Louis Desalvo)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儿童期性伤害对她的生活和作品的影响》、彼得·达利(Peter Dally)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天堂与地狱的结合》。其中,罗杰·普尔的《不为人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路易斯·德沙尔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儿童期性伤害对她的生活和作品的影响》、马克·斯皮尔卡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哀伤的争吵》是这类研究的重要著作,并且体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不为人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披露了伍尔夫幼年时期多次被两个同母异父兄长猥亵的事实,但并不认为伍尔夫有精神异常之处,反之,正是这种不幸的经历使她获得了深刻认识生活的智慧,毅然与生活抗争的勇气,以及艺术地表现生活的动力,她作品的魅力也恰恰源于它们真实、深入地表现了生活中的遭遇和重重矛盾斗争。《弗吉尼亚·伍尔夫:儿童期性伤害对她的生活和作品的影响》也把关注点放在伍尔夫所遭受的家庭性侵犯上,但在德沙尔弗看来,这是导致伍尔夫精神异常的重要原因,并由此阐析伍尔夫文本中的儿童形象。她得出结论,伍尔夫的儿童人物不仅得不到成人世界的关爱与重视,反而常常成为被欺侮与被凌辱的对象,这种凄凉可怖的童年刻画一定程度上就是伍尔夫本人孩提生活的反映。《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哀伤的争吵》同样认为伍尔夫有精神疾患,自幼家庭成员的死亡,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她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情感的惶惑和精神的焦躁不安,因而,她笔下的人物也往往不能很好地处理情感的惶惑和精神的焦虑,甚至她对于传统叙述方法的舍弃,不记叙人物一生的故事而采用现代派断裂叙述手法,也根源于此。
另一类心理传记派评论家则聚焦于伍尔夫创作与生活的关联。如林德尔·戈登(Lyndall Gordon)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认为,伍尔夫将自己所有的生存经历和情感体验都倾注在了写作中,她的生活为我们理解她的作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反之,她的作品也是我们了解她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因而,她的创作与生活是相互参照、互为印证的。约翰·梅彭(John Mepham)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生平》是这类研究的另一个代表。在梅彭看来,伍尔夫是一位不断追求艺术创新的作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尝试,而她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在寻求反映生活和意识的新方式;她的写作生涯始终贯穿着一种力图深刻诠释生活、深入反映生命认识的努力。此外,埃伦·霍克斯(Ellen Hawkes)在1974年发表论文《贝尔的伍尔夫生平研究之方法》,他指出,对于伍尔夫来说,创作是对她的自我以及个人发展的不断探求。金·迪恩(Jin Dien)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研究之方法》中认为伍尔夫的创作是体现她个性的一个方面,是一种能使她一生大多数时间保持情绪平稳的重要活动。
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弗洛伊德和20年代在英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心理分析理论对伍尔夫的影响以及在她作品中的体现。如有批评家指出,《到灯塔去》中,詹姆斯一旦抑制住了自己与母亲关系的回忆,便获得了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这是弗洛伊德观念的映射;莉莉只有在呼唤出了她视之若母的拉姆齐夫人的形象后才获得了艺术的和谐,完成了她的画作,这是克莱因理论的体现。但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解读伍尔夫文学作品的专著并不多见。伊丽莎白·阿贝尔(Elizabeth Abel)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精神分析小说》是对伍尔夫作品进行精神分析研究的范例。它论析了伍尔夫作品与同时代的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互文关系,认为伍尔夫的作品是对精神分析成长小说的回应和重写;并且指出,伍尔夫小说《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的叙事模式分别对应弗洛伊德和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叙事模式。约翰·梅茨(JohnMaze)《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创造力、无意识》细致分析了伍尔夫作品中的精神病理学主题。
21世纪以来,仍有不少西方学者将伍尔夫研究与心理学相结合。代表性著作有3部。斯密斯(S.A.Smith)的《“直到出租车随水仙花起舞”:伍尔夫晚期创作中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融合》是对伍尔夫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补充。它以《岁月》《幕间》《三枚旧金币》等作品为研究对象,指出对战争的关注促使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突出外部事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影响;为此,她寻求一种融事实与虚构于一体的表述形式。唯因斯坦(A.L.Weinstein)的著作《找回你的故事: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和莫里森》表明,通过阅读普鲁斯特等作家,读者往往能够更好地发现那些隐藏于心灵深处的、不易觉察的故事。因为这些作家的名作,往往折射出读者的自我内心世界,使他们直面潜意识自我。在论析《达洛维太太》和《到灯塔去》时,唯因斯坦主要强调了作者在探寻自我时如何突出关系的重要性。施马尔夫斯(J.Schmalfuss)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西尔维娅·普拉斯著作中的心理象征主义》,主要聚焦美国女作家普拉斯的《钟形罩》和伍尔夫的代表作《到灯塔去》《达洛维太太》和《海浪》,对她们的心理象征手法进行了比较,认为她们都有意识地把自己的文本与心理分析理论相结合。
具体到精神创伤的角度,专门研究伍尔夫的著作有1部,即苏赛特·亨克(Suzette Henke)等人合著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创伤》。它主要论述了性屈辱对伍尔夫美学的影响,以及伍尔夫代表小说《达洛维太太》中的战争创伤症候和《海浪》中关于死亡创伤的表达形式。此外,Tsai 的《创伤与记忆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D.H.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马尔茨作品中的融合》,集中探讨了发生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等灾难性历史事件对现代主义作家精神状态造成的强烈影响以及他们如何采用现代主义形式来表达这种精神创伤。这些著作不再囿于以传记方式研究伍尔夫的精神创伤,而转移到了文本分析上,但缺乏当下相关前沿理论的支撑。
受西方评论界的影响,以传记的形式探究伍尔夫的心理特征、精神特质和文本创作,从而表达中国学者对伍尔夫文学的理解与阐释,也成为国内伍尔夫研究领域的内容之一。国内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工作。
瞿世镜于1989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传记类作品《意识流小说家伍尔夫》。该书的第五部分“心理学与哲学的影响”,考察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伍尔夫的影响。他认为,伍尔夫在《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中所说的“在1910年12月左右人的性格变了”[1],与弗洛伊德学说有密切关系。并且列举了种种理由。首先,在1910年前后,弗洛伊德学说在英国知识界流行开来。伍尔夫也阅读了他的著作,并且在和丈夫创办的霍加思出版社出版了弗氏著作最早的英译本。然后,更为重要的是,在伍尔夫的论文、小说和日记中都可寻觅到弗氏关于人的意识结构分为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次的观点对她的影响。例如,伍尔夫曾惊呼道:“大自然让与人的主要本质迥然相异的本能欲望偷偷地爬了进来,结果我们成了变化多端、杂色斑驳的大杂烩……。”[2]在她看来,我们在任何特定场合所显示出来的身份,可能并非“真实的自我”,它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把“我们的多样化的自我杂乱无章的各个平面”凑合到一起罢了。[3]伍尔夫也曾在日记中说,她有二十个自我。[4]在小说《到灯塔去》中,伍尔夫把拉姆齐夫人洞察别人心灵的目光比作一束投入水中的光线,可以照明水中的三个层次,这说明她和弗洛伊德一样,也把人的心灵看作一个多层次结构。在小说《奥兰多》里,她写道,一个人可以有两千个自我。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伍尔夫所谓“人性的改变”是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是接受了精神分析学说之后的产物;虽然她拒绝接受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她在小说中总是避免对于性的描写,但她把人当成多层面、多元化的复杂本体,而不再是单一的存在;正是基于这种人性观念,伍尔夫在她的小说中大量使用了多视角、多层次的人物透视法。显然,瞿世镜的这一结论,不同于西方学界关于“人性改变”应归因于后印象派艺术影响的说法,体现了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
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界又先后发表了好几部关于伍尔夫的传记作品。有陆扬、李定清的《伍尔夫是怎样读书写作的》(1998)。陆扬在卷首语中写道:“本书是以读书为线索,来给弗吉尼娅·伍尔夫的生平和作品写一部评传。作者有意把伍尔夫从曾经幽闭过她文学形象的象牙塔中请出来,还给读者一个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的弗吉尼娅·伍尔夫。”[5]作者认为,伍尔夫的神经官能症与她幼年遭受的性创伤、父母亲人的离世相关。在“阅读战争”一节中,更是详尽地指出了战争对伍尔夫精神状态及写作的影响。“伍尔夫在战争中读出的是恐怖和精神系统的紊乱。这恐怖和紊乱是刻骨铭心,永远无以排遣的。她相信外部世界的暴力和冲突正是内心小宇宙的一个写真,如是现实世界的战争终有尽时,心灵世界的剧烈冲突永无尽期……她感受到了战争给人心灵上留下的创伤,这创伤将和死亡同归于尽。”[6]他还说:“弗吉尼娅相信艺术可以穿越战争的劫难而达永恒。这促使她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创作不息,……”[7]在第四章“意识流说”中,也考证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伍尔夫及其创作的影响,“不论是对弗吉尼娅·伍尔夫还是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的动力和欲望,永远是压迫着我们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8]。伍厚恺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1999)也较为详尽地考察了伍尔夫精神病症的形成过程,认为家族的精神病遗传因素是存在的,而亲人的死亡是直接导致伍尔夫精神疾病的重要因素。还有,两个哥哥的猥亵,极大地影响和扭曲了她的人格构建过程,她的精神疾病无不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易晓明的《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2002)以传论的形式抒写了伍尔夫的人生历程、文学发展和艺术追求等。也强调了伍尔夫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认为伍尔夫是一位锐意创新的作家,她不仅不愿谨守成规,甚至包括刚建立的新规,她要的是不断地突破,因此,她的作品都是创新之后的再创新,超越之后的再超越;而她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技巧翻新,而是着意于通过新的规则来逼近生活,力图表现更多的生活内容,更充分地表现人生,更有效地传达出作家本人对人生的感悟与见解。
近年来,一些国内研究者还开始撰写论文对伍尔夫及其作品进行心理学解读。例如,吴艳梅的硕士论文《昨日重现:浅析弗吉尼亚·伍尔夫〈幕间〉的创伤主题》(2010)将受创者的维度,分为个体创伤和群体创伤两个层面,分析了《幕间》的创伤主题。另有10篇以上的期刊文章探讨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心理、精神病与伍尔夫文学创作以及伍尔夫作品与精神分析学的关系等。但难以发现系统性的、有学术分量的文章。
将伍尔夫研究与心理学相结合,开辟了伍尔夫研究的新领域。相对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等研究,这是一种向内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揭示女作家深邃的精神世界及其文本创作的精神特点。同时,对于伍尔夫的心理传记研究,表明人们并没有忽略伍尔夫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它将向内挖掘与向外拓展结合起来,也有利于展示出一个立体多姿的伍尔夫形象。
然而,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伍尔夫心理分析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传记式的精神分析研究占据了伍尔夫心理学研究的主体,研究文学作品的专著则较少,说明学界对伍尔夫文本的心理学关注还远远不够。第二,为数不多的一些专著致力于运用精神分析批评的方法解读伍尔夫创作,但都集中于她的几部重要作品。到目前为止,还没能从心理分析这一视角对伍尔夫的作品展开整体、系统研究。第三,心理分析批评家们从家庭、社会、性别、遗传、文化、战争等因素出发,探讨了伍尔夫心灵创伤与精神疾患的形成,还涉及了精神创伤在伍尔夫作品中的体现,却没有进一步关注伍尔夫是如何力图通过文学创作应对创伤、跨越创伤的。正如批评家奈尔默(James Naremore)对伍尔夫现代主义研究所进行的批判,认为批评界忽略了伍尔夫创作没有终止于“意识”,而是超越于“意识”之上这一重要事实。这一批判同样适用于伍尔夫心理分析批评。也就是说,对伍尔夫的心理分析研究尚停留在浅层,还有待深化。第四,从已有成果来看,绝大多数伍尔夫心理分析研究或者仅仅在以弗洛伊德学说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进行,或者只作一般性的、缺乏理论观照的描述和揭示。然而,弗氏学说中的重要部分——精神创伤理论在当代学术语境中已获得逐步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创伤学理论,是迄今可用于分析、解读文学性创伤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当今伍尔夫研究界,还鲜有学者利用这一理论研析伍尔夫其人其作。可见,伍尔夫心理分析研究也缺乏当下理论的支撑和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