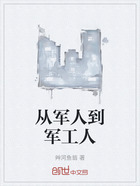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12章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的中学生活
1972年2月,我小学毕业。以居住地划片就近分配入学,升入CQ市第20中学(后为CQ市育才中学)读初中,分在初74级12班。3月份,我以小学学生干部的身份,又一次被初中的新班级选为班长。
CQ市第20中学,是中国教育家陶行知1939年7月,创办于重庆合川县草街乡古圣寺的育才学校,创办之际,育才学校就经受了抗日烽火的洗礼。当时在学校聚集了大量的全国知名文化人士:茅盾、贺绿汀、陈烟桥、艾青、翦伯赞、章泯、郭沫若、戴爱莲等在校任教。1945年秋迁至沙坪坝区的红岩村,1947年部分师生迁上海。
建国后的1950年春,育才学校留渝师生迁址至JLP区谢家湾,更名为“重庆育才中学”。1953年人和中学并入,并按统一编号更名为“CQ市第20中学”。1978年被SC省教育局确定为首批省属重点中学,1981年恢复校名为“SC省CQ市育才中学”,1997年更名为“CQ市育才中学”,成为CQ市的重点中学。
中学和小学存在很大的区别:小学主要学习基础课程,而中学则学科知识更加系统化,难度也比小学大得多;小学的学习依赖老师的安排,而中学则要求学生更加自觉主动地学习;小学老师注重使用直观教学手段,学生被动接受,而中学老师则更注重引导学生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更强调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学生与小学生也大不一样,小学生的生活通常由家长全方位照顾,而中学生身体机能逐步健全,需要开始培养自己的生活能力。在心理特征上,小学生的学习主要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中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强烈,具备更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按照“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改革”的教学理念,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那时的中学学制实行了“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当时的课程设计比较简单,对系统的知识体系进行了合并,注重实用知识的讲解,学科的基础知识有删减削弱。课堂学习环境比较宽松,课时也大为减少。老师管理也相对粗放,认为中学生的自律能力足够强的观点有点超前,反正课堂学习讲自觉,考试更是少之又少,还一律开卷,课外作业也很少。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学习的动力。想学习的学生埋头读书,可以自由地与各科老师频繁请教交流;对爱玩的学生,则放任自流,由着性子玩,学习成绩形成了两极分化。
当时第20中分为英语班和俄语班,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有16个班。1至8班为英语班,9至16班为俄语班。我们12班的外语课,学的是俄语。
俄语是我中学所有科目中最差的一科。俄语成绩差,有自己努力不够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外语学习的环境不好造成的。
我们班教俄语的是一名中年女老师。开学上第一节俄语课的时候,有个学生上课偷看小说,被老师发现收缴。可能那本书是借的,学生非要讨回,造成了冲突。闹到学校教务处后,学校还是把收缴的书还给了学生。
俄语老师从此上课便走过场,举书本遮脸讲课,也不管下面学生干什么,对教室里乱哄哄的象自由市场的现象听之任之。后来上俄语课的时候,少数不想学俄语而又胆子大的男生,干脆从窗子翻出教室,溜号到操场去打篮球;一些对俄语兴趣不大的女生,则在课堂上织毛线衣、看小说;而想学俄语的同学,经常听不清老师的正确发音,搞不明白讲的内容。受此影响,我的外语成绩一塌糊涂,以至于在十五年后我都参加工作多年了,还重上夜校补习了英语,才被评上了工程师职称。
因为上课非常轻松,也有相当充裕的课余时间。每天放学之后,我放下书包,还是相约同学或邻居玩一阵。但晚上上床后,必然要捧一本书在手看上几页,然后才睡觉。为此,我的枕头边总是放着几本书。所以,我的语文成绩一枝独秀,历史、地理也名列前茅,数学还勉强可以,物理、化学成绩则一般般,但最怵外语课,偏科有点严重。
被称为“书生”的我,阅读与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渐渐养成了内敛含蓄的性格。
从中学开始,我受到徐特立的名言“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影响,读书看报时开始记笔记,以增强阅读的效果。开头只是在书本或报刊杂志上圈点勾划、标示重点,体会立意构思,揣摩布局谋篇,摘抄警句格言,欣赏妙词佳句。进而在书本边角空白处作批注,写出自己的理解、体会和感悟。后来又用作业本摘录一些需要请教的学习难题和老师的解答。偶尔也写读后感,字数不多,有感而发,包括日常见闻,对某些际遇的好奇、疑惑和个人感受等等,内容五花八门,自由自在,没有什么章法。
随着边读边记的积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尤其是每年3月5日全国学习雷锋活动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于是就模仿《雷锋日记》开始记日记。但限于思想认识和写作水平的限制,有记的内容时天天记,没有什么可记时就写周记或月记,更多的是几个月总结一次,并未逐日记录。由于太随意,严格说都算不上日记,只能算是笔记。
但随手记笔记就这样从学生时代断断续续坚持到下乡当知青、入伍当兵和进工厂参加工作。直到上世纪90年代,家里买了电脑,我因为工作学习太忙,嫌在本子上动笔记笔记麻烦。就在电脑上建了一个专题文件夹记录日常。从此写作、编辑、保存、使用方便了很多,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吧。
再后来,由于数次搬家,那一堆长年束之高阁的陈旧笔记本,不经意间被清理出来和废旧书报一起当废纸卖了,造成原稿散失没有保存下来,甚为可惜。
好在我买了电脑后,曾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对旧笔记本按编年体的体例进行过一次整理,将一些重要的内容摘要作为备忘录而录入了电脑。当时只是用常识思考问题,并非有先见之明,这才使多年前的那些努力勉强没有完全白费。
刚上中学的那年,父母在我的生日时,给我买了一副乒乓球拍。那时我就读的第20中初中教学楼旁边的空地上,修有10张水泥乒乓球台,那里是同学们课余时间的好去处。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我早早收好书包,与暗中有约的几个同学眉来眼去、传递眼色,只待下课铃一响,大家便箭一般冲出教室去,和喜欢打乒乓的其它同学抢占球台,然后打乒乓球直到天黑才心满意足地回家吃饭。好在那时没啥课外作业,如今的学生们学习负担之重,是没有条件充分享受我们当时那种运动的乐趣的。
初中两年半的学习,就这样在轻松散漫中一晃而过。1974年7月,我初中毕业。9月升入同校读高中,我又被选为班委学习委员。
高中第一学期,学校遵循“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的教学理念,按照“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教学惯例,执行“开门办学”的办学方式。学校在课堂学习之外,又把学工、学农列入教学计划,分别与工厂和农村挂钩建立了学工、学农基地。
同学们开学后刚刚熟悉了新的学校环境,认识了各科老师,学校便安排十五六岁的少年新生们,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各班分别到附近的几家工厂参加了学工劳动,时间为一个月。
我们班到的是国营重庆矿山机械厂,这个工厂规模不大,三线建设期间由上海内迁来渝,地址在石坪桥,离杨家坪很近。
正式的“学工”是1974年国庆节假期后开始的。重庆矿山机械厂先在工厂礼堂开了一个欢迎会,工厂的领导和学校领导讲了要求和纪律。然后,全班同学被分到工厂的几个主要车间,跟着工人师傅一起学习劳动。老师和同学每人发了一张临时通行证和若干饭菜票,早晨8点到厂上班,中午在工厂职工食堂就餐,晚上与车间工人一起下班。班主任每天与工厂人劳科的师傅到各个车间巡查,了解学生的状况,解决同学们遇到的困难。
我被分配给一个做摇臂钻车的师傅学习,其它同学有的跟元车师傅,有的跟铣车师傅,有几个女同学分配到了钳工组。工人师傅们教我们学识图,让我们观摩他们操作机床加工零部件和机床保养。
机床操作是有规范的,需要正规的培训,获得专业的技能证书,才有资格上岗作业。所以车间一般不让同学们碰机床设备,大家只能给师傅们打打下手,递一递工具,做做清洁打扫卫生,但可以参加车间每周的学习会、所在生产小组每天的班前会等等,粗略了解了一些国营工厂的运行机制。
工人在社会上被称为“老大哥”,是当时受人尊敬、令人羡慕的职业。我在工厂一个月学工劳动的收获是获得了工人师傅“朴实”的评语;最大体会是提前感受了当工人的感觉,一个字——“爽”。
11月上旬,离开学工的重庆矿山机械厂回到学校,我们总算安稳地坐到教室里开始上课,我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当“书生”、“啃”书本了,学习生活进入了正轨。
1974年12月27日,我在重庆第20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五四青年节,又被选为年级共青团支部宣传委员。共青团组织在课余要组织一些学习、宣传、文娱活动和志愿活动,每年的5月4号,要组织青年节的纪念活动;11月27号,还要组织团员参观红岩村或到烈士墓扫墓,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春秋两季,也组织团员青年到南温泉或北温泉等风景区进行郊游活动。
当年学校新建了八个标准篮球场,建筑单位的工人师傅忙碌了好几个月。学校共青团发出号召,组织志愿活动,团员们踊跃参加义务劳动。记得年底好几个星期天,我们共青团支部组织团员参加了敲石子的义务劳动。
篮球场修好后,篮球运动立即受到追捧。高年级各班,便经常自发举行班级间的篮球赛。形式也很接地气,一般由两个班级的班干部或团干部,在课间先口头约定好,在学校的告示栏贴一张通知,放了学后,班上爱好打篮球的同学组成一个队,轮番上场参加比赛。场上没有裁判也没有教练,只有两个手持粉笔的同学在一张小黑板上划“正”字记分。罚球、记时等等一切均约定俗成,比如,任何一方只要吹响一声口哨,就可以换人;“咚”的一声铜锣敲响,比赛就会戛然而止。
比赛的水平并不重要,重在参与才是真谛。大家都挺投入的,偶尔一招一式也玩出观赏性:运球、过人、传球一气呵成,三大步腾空而起,投蓝、灌篮、扣蓝干净利落,倘若遇到某些场次球场边观战的女生比较多的话,那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的“选手”们为获得摇旗呐喊的女生们清脆的喝彩,竞相表演“高难动作”而摔得鼻青脸肿是常有的事,这是老实话。
高一上学期,我们大概上了4个月的课。教室里的板凳都还没有坐热,下学期又走出教室,联系实际去了。
1975年寒假后返校,学校安排高中各班分批到“农村分校”轮流学农劳动半年。我们年级16个班,分两批学农,每批8个班。我是班干部,被派出打前站,和年级其它班的几个学生干部一起,在老师带领下提前一周到我们学校的农村分校(位于伏牛溪的五七干校),协助老师安排大家的食宿。
伏牛溪五七干校位于袁茄公路旁边的一条小溪沟旁边,离长征机器厂不远。干校有好几个相距不远的建筑群,田地分布在一片起伏的丘陵中,还有一片很大的果园。宿舍是几排平房,围成一个很大的院子,大家以班组为单位睡大通铺。院子旁边还有一个猪圈,学校安排了几个同学专门喂猪。食堂在相距80余米的另一个大院里,每个班抽调一个同学组成炊事班为大家煮饭。
高一下学期的学农劳动锻炼,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过集体生活。
农村分校的作息时间按照课堂学习与学农劳动各占一半的原则安排,课堂教学以一次4个班,在干校的大会议室轮流上大课。学生每周上三天课,课堂上多是讲授农林实用知识,课后布置的作业,通常是结合劳动实践写心得体会;学校老师还来干校举办讲座,主讲时事政治。
每周的其余三天,由学校老师和干校职工带领同学们参加田间劳动。每次4个班分批前往,其实所谓劳动并不干重活和技术性强的农活,无非是锄地、拔草、浇水等轻松的活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大家一点都不觉得累。田间地头常常欢声笑语不断,很是放松,形同儿戏。不过,虽然劳动强度不大,但普遍食量大增,感觉每顿定量的饭菜有点不够吃。
晚上,学校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有文艺爱好的同学自带乐器,自编节目,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很是热闹。天气暖和后,学校还在当地的水库组织了一次游泳比赛。
周末休息一天,同学们相互邀约,三三两两到堰塘自己洗衣服。我们的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小说,但小说只能偷偷看,同学之间也交换着看。
学校每月安排专车接送同学们回家一次。同学们便带来一些咸菜、肥皂、换季衣服等日用品。因为离家不是很远,没有感觉什么不方便。
1975年7月,我们结束了学农,也结束了高一学年的学习。暑假后,学生们终于回到学校教室,总算开始正常的上课了。
在高中阶段,高二的第一学期基本上是在课堂上课,老师对课堂教学重视度明显提高了,课堂测验也多了一些,还举行了一些闭卷考试。甚至还有老师给同学们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理念,激发了学生们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兴趣。我如鱼得水,更是发奋学习,暗暗刻苦读书,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普遍高涨。
高二的下学期,学校又安排各班学生结合社会实践进行学习,我们班被安排学习中医。这次社会实践与高一学期的学工学农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没有停课离开学校,还是以文化学习为主,只是每周学校专门安排一个半天,上中医知识课。
中医是国粹,中国人了解一点中医知识也未尝不可。可惜我们浅尝辄止,并没有学习传统的中医理论,也不研经络、诵脉诀、背汤头、识药理、学配方,又不练推拿、扎银针……只是在课堂上对照书本辨识常用中草药。
老师还安排时间,带领全班同学走出书斋,走访九龙公社的赤脚医生。中年赤脚医生将一大堆中草药摊开,一件一件的讲特征,讲药效,讲用途。学校还利用星期天,两次组织我们到北碚和南泉的大山上采草药,制标本。三个多月的中医学习,意外的收获是我认识了一些常用的草草药。
1976年7月18日,学校举办了高七六级学生的毕业典礼,我高中毕业,十年的学生生活就此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