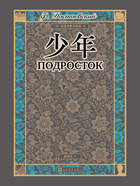
三
“……我不喜欢女人,因为她们粗俗,因为她们笨手笨脚,因为她们不能独立,因为她们穿的衣服不成体统!”我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结束了我那长篇大论。
“亲爱的,你就饶了我吧!”他叫道,简直高兴极了,这就更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
在小事情上我可以忍让,无所谓,但在大事情上我寸步不让。在小事情上,在上流社会的某些交际应酬中,人家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因此我常常诅咒我身上的这一弱点。出于某种好心肠的臭脾气,有时候,只要上流社会随便哪个花花公子仅仅用他的彬彬有礼迷住了我,我就会对他唯命是从,或者卷进一场跟一个傻瓜的争论,而这是最不可饶恕的。这都是因为我缺乏自制力,因为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长大的。我离开时往往怒气冲冲、赌咒发誓地说,明天再不会出现这一套了,可是到了明天又是老样子。因此有时候人家往往把我当成一个十六岁的孩子。现在,我非但没有培养出自制力,反而宁可更深地封闭在我那角落里,虽说采取的是一种厌恶人类的极端形式:“就算我笨手笨脚吧,但是——对不起,再见!”我说这话是严肃的,而且永不反悔。话又说回来,我写这些根本与公爵无关,甚至也与当时的谈话无关。
“我说这话根本不是为了让您开心,”我几乎冲他嚷嚷起来,“我不过是说说自己的看法。”
“但是说女人粗俗和穿戴不成体统,这话又从何说起呢?这倒新鲜。”
“粗俗就是粗俗。您不妨上剧院去,您不妨去散步,任何一个男人都知道靠右走,碰到一起,就各自让道,他往右,我也往右。可是女人,就是说太太小姐——我说的是那些太太小姐——却向您直冲过来,甚至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似乎您一定而且必须躲开,给她们让道。女人是弱者,我乐意为弱者让道,但是为什么这就成了权利,为什么这女人就那么自以为我必须这样做呢——正是这点太气人!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十分厌恶。而遇到之后,有人大呼小叫地说,她们受到了蔑视,要求平等;这哪儿来什么平等,这是女人把我踩在脚下,或者塞我一嘴沙子!”
“沙子!”
“是的;因为她们的穿着伤风败俗,对此,只有伤风败俗的人才视而不见。法院审理有伤风化的案子时必须关起门来,为什么在大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中,却允许这样呢?她们公然在自己身后塞个腰垫,以显示体态妖娆,是个大美人;简直明目张胆!要知道,我不会看不出来,连小伙子也看得出来,连小孩,刚上学的小孩,也看得出来:这简直下流。就让那些老色鬼去欣赏吧,就让他们垂涎欲滴地跟在她们屁股后面跑吧,但是我们还有纯洁的青年必须保护。凡此种种,我只能唾弃。她走在林荫道上,身后拖着一俄尺[2]半长的曳地长裙,扬起一片尘土,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办呢:要么跑步超过,要么就躲到一边,要不然,她就会满鼻子满嘴地给您塞上五俄磅[3]重的尘土。再说,这是绸裙,她在石子路上拖着它,蹭来蹭去地走上三俄里,仅仅是出于时髦,而她丈夫在枢密院供职,年薪才五百卢布:这就是贪赃受贿的根源!因此我才呸呸连声地啐唾沫,大声地啐,还骂人。”
虽然我略带幽默地写下了这次谈话,而且这也符合我当时的特点,但是这些想法我至今保持不变。
“居然太平无事?”公爵好奇地问。
“我啐了口唾沫就走了。不用说,她还是感觉到了,可是却不动声色地大摇大摆地走着,头也不回。我认认真真地骂人只有一次,是跟两个女人,她们俩都拖着尾巴,走在林荫道上——不用说,不是用脏话骂的,只大声说,这尾巴真恶心。”
“你真这么说了?”
“当然。首先,她践踏社会公德,其次,她弄得尘土飞扬,而林荫道是为大家服务的:我可以走,第二个人可以走,第三个人,费奥多尔,伊万,谁都可以走。这话,我就这么说了。总之,假如从后面看,我不喜欢女人走路的姿态;这话我也说了,但用的是暗示。”
“我的朋友,要知道,你会惹麻烦的,她们会扭送你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
“她们什么也干不了。她们没有上告的理由:一个人在一旁走路,自言自语。任何人都有权对着空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只是抽象地说,并没有对她们说。是她们自己缠住我不放,她们还骂人,骂得比我更不堪入耳:什么乳臭未干的混蛋呀,什么不该给他吃饭呀,什么虚无主义者呀,应该把我交给警察呀,又说什么我缠住她们不放是因为她们势单力薄,是弱女子呀,如果她们身边有个男人,我一定会夹起尾巴,乖乖地溜走呀。我冷冷地向她们宣布,让她们不要再纠缠我,我要到对面去了。为了向她们证明我不怕她们的男人,准备接受她们的挑战,因此我决定跟在她们后面,离她们二十步,一直护送她们到家,然后站在门前等她们的男人出来。我说到做到,就这么做了。”
“真的?”
“当然,这很蠢,但是我头脑发热。她俩带着我走了三俄里多,大热天的,走到贵族女子中学,进了一座木头平房——我得承认,这房子非常好——打窗户望进去,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花,两只金丝雀,三只一般的小狗和几张镶在镜框里的版画。我在房前的街上站了约莫半小时。她俩偷偷地向外张望了两三次,后来就把窗帘全拉上了。最后,从篱笆门里走出来一位上了年纪的文官;看样子,刚才在睡觉,是被人特意叫醒的;倒不是穿着睡袍,而是穿得随随便便,一身家常打扮;他站在小门旁,倒背两手,开始打量我,我也打量他。后来他挪开了眼睛,再后来他又看了看我,突然向我露出微笑。我就扭过身子,走了。”
“我的朋友,这倒有点席勒的味道!我一直感到奇怪:你这人红光满面,脸上透着健康——竟对女人,可以说吧,感到这么恶心!像你这样的年龄,居然会对女人毫不动心!我亲爱的,我还只有十一岁的时候,家庭教师就批评我,一到夏园[4]就盯着女人的裸体像,看得入了迷。”
“您巴不得我去找一个本地的约瑟芬[5]鬼混,然后再回来向您汇报。完全用不着;我才十三岁的时候就亲眼看到过女人的裸体,全身赤裸;从那时起,我看见女人就恶心。”
“此话当真?但是,亲爱的孩子,漂亮而又娇艳的女人往往像苹果一样芬芳馥郁,怎么会感到恶心呢!”
“我还在从前的图沙尔寄宿学校读书时,还在上中学以前,有一个同学,叫兰伯特。他老打我,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还多,我只好老老实实地伺候他,给他脱靴子。有一回,他去行坚信礼[6],修道院院长[7]里戈特地赶来,向他祝贺第一次领受圣餐,两人热泪盈眶地互相拥抱,搂住对方的脖子,里戈院长摆出各种姿态,把他紧紧地搂在自己胸前。我也哭了,而且十分羡慕。后来他父亲死了,他离开了学校,我有两年没看见他,可是两年后我却在大街上遇到了他。他说他会来找我的。当时我已经在上中学,住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家。有天清早他来找我,拿出五百卢布给我看,要我跟他走。两年前,他虽然老打我,但总也离不开我,倒不仅仅是为了给他脱靴子,他心里有事都要告诉我。他说,他偷偷地配了把钥匙,这钱就是从他母亲的首饰盒里偷来的,因为这钱是他父亲的,依法应当完全属于他,她不敢不给,他又说,昨天,里戈院长来开导他——一进门,站在他身旁,就哭丧着脸,向老天爷举起双手,描写受到上帝惩罚时的恐怖,‘可我却拔出刀子说,我宰了他’(他把‘宰了他’说成‘菜了他’)。我们坐车去了铁匠桥。路上他对我说,他母亲同里戈院长有一腿,又说这是他亲眼所见,他才不在乎呢,他又说他们对领受圣餐所说的一切全是胡说八道。他还说了许多话,而我则越听越害怕。在铁匠桥,他买了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狩猎袋,几发装好的子弹,一根驯马的鞭子,后来又买了一俄磅糖果。后来我们出城练习打枪,路上碰到一个提着鸟笼的小贩,兰伯特向他买了只金丝雀。在小树林里,他把金丝雀放了,因为这鸟在笼子里关过以后飞不远,他向它打了一枪,但没打中。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开枪,而他早就想买支枪了,还在图沙尔那儿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朝思暮想地想弄支枪。他像被烟呛着了似的上气不接下气。他的头发长得墨黑,他的脸色白净而又白里透红,就像戴着面具似的,鼻子长长的,像法国人那样微微隆起,牙齿雪白,眼珠则是黑的。他用线拴住金丝雀,绑在树枝上,然后举起双筒枪,对准了,距离仅一俄寸,连发两枪,打得这只金丝雀血肉横飞,到处飞散着羽毛。然后我们又回城,走进一家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开始吃东西、喝香槟酒;这时来了一位女士……我记得我十分吃惊:她穿得那么华丽,穿着绿色的绸裙。这时我就看到了一切……也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事……后来,我们又开始吃东西,他就开始逗她,骂她;她光着身子坐在那里,他把衣服抢走了,后来她就开始骂人,向他要衣服,她要穿上衣服,他就抡起鞭子,使足劲抽她那两只赤裸的肩膀。我站起来,揪住他的头发,十分灵巧地一下子就把他摔到地板上。他操起叉子,猛地一下戳进了我的大腿。这时,听到喊叫,人们跑来了,我溜之大吉。从那时起,我一想到裸体就感到恶心;说真的,那女人还是个大美女。”
随着我的娓娓道来,公爵的脸色也慢慢在变,由轻快渐渐变得十分忧伤。
“我可怜的孩子!我一直相信,你在小时候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
“请放心。”
“但是你自己也对我说,你很孤单,虽说有个兰伯特;你对此是这么描写的:金丝雀呀,含泪趴在院长胸前的坚信礼呀,然后,过了这么一年,他又讲到他母亲和院长私通……噢,我亲爱的,这儿童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太可怕了:眼下,这些天真烂漫、长着金黄色鬈发的小脑袋,在童年之初,就在你面前飞来飞去,看着你,带着开朗的笑声,睁着明亮的眼睛,就像一群上帝派来的小天使,或者像一群美丽的小鸟;可是后来……可是后来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倒不如他们压根儿没长大好!”

“公爵,您的心多软啊!倒像您自个儿有孩子似的。要知道,您没有孩子,也永远不会有。”
“恰好!”他的整个脸霎时变了,“恰好,有位叫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的——就在前天,嘿嘿!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西尼茨卡娅——约莫三星期前,你大概在这里遇到过她——你想想,前天,她忽然对我说,因为我说了一句笑话,如果我现在结婚,我至少可以放心,我不会有孩子了——她却忽然对我说,甚至是恶狠狠地说:‘相反,你肯定会有孩子,像您这样的人肯定会多子多孙,甚至从头一年起就会接二连三地生,您瞧着吧。’嘿嘿!而且所有的人不知为什么总以为我会忽然结婚;虽然说这话的人不怀好意,可是你得同意——这话很俏皮。”
“很俏皮,但也很气人。”
“好了,亲爱的孩子,哪儿来这么多气呀。我最看重别人的俏皮和风趣了,可是现在这股劲儿正在明显地消失,至于将来亚历山德拉·彼得罗芙娜会说什么——难道能把它当真吗?”
“什么,您说什么?”我抓住不放,“哪儿来这么多气……对,就是这么说的!不是任何人都值得把他的话当真——这是一个好极了的规则。我要的正是这一规则。我要把这记下来。公爵,您有时候真是妙语连珠。”

他顿时兴高采烈,容光焕发。
“是吗?亲爱的孩子,真正的妙人妙语正在消失,而且越往后越少。然而……我是知道女人的!请相信,任何女人的一生,不管她鼓吹什么,始终在寻求一个她能够对之顺从的人……可以说吧,这是一种顺从欲。请记住——无一例外。”
“完全正确,妙极了!”我十分赞赏地叫了起来。换了在别的时候,我们俩肯定会就这一话题高谈阔论,而且一谈就是整整一小时,但是这一回却忽然有件事猛地刺了我一下,使我的脸猛一下涨得通红。我不由得想到,我夸他妙语连珠,是否有在要钱之前竭力对他拍马逢迎之嫌呢,我当真开口向他要钱的时候他肯定会这么想。因此我不如干脆现在就把这事提出来。
“公爵,我恳请您现在就把这个月欠我的五十卢布给我。”我一口气说了出来,甚至怒气冲冲地近乎粗暴。
我记得(因为我记得这天上午的一切,直到最小的细节),就其现实真相来说,当时在我俩之间产生了一场最糟糕的状况。他先是没听懂我的意思,久久地看着我,不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钱。自然,他想也没想到我还要领薪水,——再说,我凭什么拿钱?诚然,后来他一再要我相信他忘了,当他明白是这么回事之后,就立刻掏出五十卢布,但是手忙脚乱,甚至脸都红了。我看出原来是这么回事,就站起身来,坚决申明,这钱现在我不能拿,人家告诉我关于薪水的事,显然弄错了,或者为了骗我,让我不要拒绝这门差事,我又说,现在我十分清楚,我没有资格领薪水,因为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公爵害怕了,开始一再说服我,我做了很多很多事,而且以后要我做的事还更多,又说五十卢布太少了,相反,他要给我加薪,因为他责无旁贷,这是他亲自同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谈妥的价钱,但是他却“不可饶恕地全忘了”。我腾地一下涨红了脸,斩钉截铁地宣布,因为我讲了几件丑事,说我怎么尾随那两条尾巴一直走到贵族女子中学,为此而领薪水,我觉得下流,再说,我不是雇来给他寻开心的,而是来做事的,既然无事可做,那就应当从此结束,等等,等等。我简直无法想象,他听了我这些话以后竟会这么害怕。不用说,结果是我不再反对,他把五十卢布硬塞给了我;一想到我收下了钱,我至今都感到一阵阵脸红!世上常有这样的事,最后总是以卑鄙告终,而最糟糕的是,他当时竟能几乎千方百计地向我证明,我无可争议地应当拿到这笔钱,而我居然愚蠢到信以为真,而且不知怎么,不拿这笔钱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他叫起来,一边吻我和拥抱我(我得承认,鬼才知道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差点哭出来,虽然我霎时就忍住了,甚至现在,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感到脸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就像我的亲人;这一个月里你好像成了我的心头肉!在‘社交界’就只有‘社交’,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的女儿)是个很出色的女人,而且我为她而自豪,但是她常常,我的亲爱的,常常使我非常生气……嗯,而这些小女孩(她们都很迷人)和她们的母亲常来祝贺我的命名日——她们也就会送我一些她们自己绣的十字绣,却什么话也不会说。她们的十字绣,我已经攒到足够做六十个枕套了,总是绣些小狗呀,小鹿呀。我非常喜欢她们,但是我跟你却似乎同亲人一样——不是像儿子,而是像亲弟弟,我尤其喜欢你反驳我的时候;你有文学修养,你读过不少书,你善于欣赏……”
“我什么书也没有读过,而且毫无文学修养。我只是碰到什么读什么,而近两年我根本就没读过任何书,而且也不想读。”
“为什么不想读呢?”
“我另有目的。”
“亲爱的……如果一个人在临终前只能像我一样对自己说:我什么都知道,可是却不知道任何好东西,岂不遗憾。我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活在这世上!可是……我非常感谢你……我甚至想……”
他不知怎么忽然打住了,无精打采,陷入沉思。激动之余(而激动的状态,他是时刻都会发生的,天知道因为什么),在若干时间内,他通常就会似乎失去健全的理智,不能自持;然而,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因此这一切无伤大雅。我们坐了片刻。他那厚厚的下嘴唇完全耷拉了下来……使我最感惊奇的是,他忽然提到了自己的女儿,而且态度还十分坦率。当然,我认为这是他心绪不宁的缘故。
“亲爱的孩子,我以你相称,你不会生气,是不是?”他忽然冒出了这句话。
“一点儿也不生气。我得承认,起先,头两回,我有点不高兴,也想对您本人以你相称,但是我发现这样做很蠢,因为您对我称你并不是因为您想贬低我,是不是?”
他已经不在听我说话了,已经忘记了他自己提的问题。
“嗯,你父亲怎么样?”他忽然向我抬起他那沉思的目光。
我蓦地一惊。首先,他把韦尔西洛夫称作我的父亲,这是他过去从来不允许对我这样说的,其次,他向我谈起了韦尔西洛夫,这也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
“没有钱,干坐着,闷闷不乐。”我简短地回答,但却十分好奇。
“是的,与钱有关。今天地方法院要开庭审理他们那桩官司,所以我在等谢廖查公爵,他一定会带点什么消息来的。他答应开庭后就直接来找我。他俩的命运都在此一举;这事关乎六万或八万卢布。当然,我一向希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即韦尔西洛夫)好,而且看来,这回他将胜诉,而公爵家将一无所获。法律嘛!”
“今天开庭?”我大惊失色地叫起来。
一想到韦尔西洛夫竟不屑把这事告诉我,这使我非常吃惊。“可见,他也没告诉母亲,或许,也没告诉任何人,”我立刻想到,“瞧他这德行!”
“难道索科尔斯基公爵在彼得堡吗?”另一个想法又忽然使我很吃惊。
“昨天就来了。直接从柏林来,特意赶在开庭之前。”
这消息对我也非常重要。“今天他也要到这里来,这个曾经给了他一记耳光的家伙!”
“那又怎么样呢,”公爵的脸色陡地大变,“他会一如既往地宣传上帝,而且,而且……说不定,又要去追女孩子,追那些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嘿嘿!现在恐怕又要出现一个十分逗乐的故事了……嘿嘿!”
“谁会宣传上帝?谁会追逐女孩子?”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呀!你信吗,他当时就像一片树叶似的老黏着我们大伙儿:问我们每天吃什么和每天想什么——也就是说,差不多是这样。他吓唬我们,帮我们清除杂念:‘如果你笃信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去当修士呢?’他差不多总是这样要求我们。这是什么想法!即使说得对,不也太严厉了吗?他尤其喜欢用最后审判[8]来吓唬我,在所有的人中,他尤其喜欢吓唬我。”
“我已经跟他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类事情我什么也没有发现呀。”我一面不耐烦地听他说话,一面回答。我感到十分懊恼,他的病还没好,嘟嘟囔囔,语无伦次。
“他这话只是现在不说罢了,但是,请相信,我说得没错。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无可争议,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的脑子正常吗?而这一切都是他在国外住了三年以后发生的。而且,我得承认,我感到很吃惊……他也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很吃惊……亲爱的孩子,我热爱上帝……我信仰上帝,尽我所能地信仰,但是——当时我却大光其火,怒不可遏。就算我当时采取的方法有欠周全吧,那也是我在恼怒中故意为之的——再说,我提出反驳的理由是严肃的,而且从开天辟地起就是严肃的:‘如果真有一个高级生物,’我对他说,‘而且作为一个人的形态而存在,而不是以某种造物主无所不在的圣灵的形念,不是以液态而存在(因为这更难理解)——那他到底住哪儿呢?’我的朋友,无疑,这问得很愚蠢,但是,要知道,一切反驳都会归结到这个问题上来。居住地——这事很重要。他勃然大怒。后来他在国外就改信了天主教。”
“关于他的这一想法我也听说过。想必是胡扯。”
“我敢以一切神圣事物向你保证。你再仔细看看他……不过,你说他变了。可是那时候他却把我们大家折磨得够呛!你信吗,他那神气就像他是圣徒似的,而且他死后定将出现圣尸[9]。他要我们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报告,我敢向你发誓,真的!圣尸!又是一个想法!嗯,如果他是个修士或者隐修士,那还好说——而这里,这人却穿着燕尾服,还有其他等等……忽然,又来了个他的什么圣尸!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居然有这么奇怪的愿望,老实说,还有这么奇怪的口味。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当然,这一切都是神圣的东西,而且一切都可能发生……再说,这一切属于不可知的领域,但是对于一个上流社会的人,这甚至是有失体统的。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有人希望我这样做,我敢发誓,我肯定会拒绝。比如我吧,忽然,我今天还在俱乐部里吃饭,以后却忽然——显灵了!这岂非让人笑掉大牙!这一切我当时就对他说了……他曾经戴过脚镣[10]。”
我气得脸都红了。
“您亲眼见过脚镣?”
“我倒没亲见,但是……”
“我要向您郑重申明,这全是胡扯,卑鄙的阴谋,恶意的造谣,仇家的诽谤,也就是说,他,就有一个仇人,一个最主要的,最无人性的仇人,因为他只有一个仇人,这人就是令嫒!”
公爵也腾地脸红了。
“我亲爱的,我请你,并且坚决请你,从今往后,永远不要再把小女的名字同这件丑恶的事连在一起了。”
我微微欠起身子。他怒不可遏;他的下巴都在发抖。
“这件可恶的事!……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永远不会相信,但是……人家对我说:请相信,请相信,我……”
这时忽然进来一个仆人通报有客来访;我只好又坐到我的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