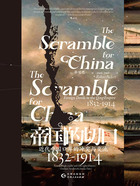
导言
李度(Lester Little)一直留到了最后。1949年,这名中国海关的第五任外籍总税务司宣布了自己即将辞职的信息——他将休假6个月,而辞职将在休假结束之后正式生效。随着李度的辞职,中国海关再无外籍雇员。[1]90多年来,共有1.1万名外国人任职于这个中国国家机关,而今这段历史在中国台湾岛上的难民收容中心里徐徐落下帷幕。美国人李度和与他一同工作的中国高级职员拍了最后一张合影,然后搭乘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轮船前往香港,再从香港乘船渡过太平洋回到美国。李度和与他一起合影的英籍私人秘书埃尔茜·丹森(Elsie Danson)都可以选择辞职回家或者另谋高就,而他们的大多数中国同事就没那么幸运了。194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斗志昂扬的军队日渐壮大,国民政府面临崩溃。国民党军队要么在战场上被击溃,要么就当了逃兵,或转而向他们昔日的敌人投诚。在上海的海关总部里,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正在准备接管海关的秘密组织。与此同时,海关的船只却满载金银前往台湾。1949年4月撤离上海之后,李度南迁广州,之后又于1949年10月被命令随着他的中国上司以及他们的黄金续程前往台湾。几周之后,李度大多数下属的驻地都成了解放区,所有的外籍雇员也都已被解雇,他本人亦再没有心思继续坚守这个岗位了。至此,李度感到自己的存在实属多余,遂提交了辞呈。对于中国舞台上的外国演员来说,谢幕的时刻已经来临。
今天来看,以上这段记述的某些情节或许有些超现实:一个外国人掌控着这个国家政府中最大的财政收入机关,而且,在90年间,他已是第5任掌控该职位的外国人了。这段时间里,还有另外1.1万名外国人任职于中国海关。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答这些问题,而解答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我们必须了解外国人在中国打造的世界,并且评估这个世界的影响和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它给当今中国以及中国的对外关系上带来的种种影响)。此外,这个世界所留下的成千上万的个人遗产也不应被遗忘。距离1949年已经过去近60年了①,如今,我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镇一个僻静小巷子的民居里,审视着眼前光滑桌面上摆放着的李度在华任职期间使用过的衣物和纪念品。原本摆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两面小旗帜被从楼上窗台带了下来,它们分别是“中华民国国旗”和总税务司(Inspector General,简称IG)旗。这个美国家庭的饭厅里本来就摆满了从中国带回来的各种装饰品和古玩,现在它更是成了纪念李度中国官场生涯的一个小角落。这些摆设品包括照片和嘉奖状、李度的个人信函和他所收藏的书籍,以及他的日记——一份充满个性化表述的私密记录,其内容则有关他为中国政府服务的那40年。李度的女儿为我准备了这一切,然后我们一边吃午饭一边聊起外国人在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海关的工作、她的童年,以及她成年后(20世纪40年代末)在上海的生活,当时她丈夫在一家美国银行里工作,他们生活在宽敞堂皇的总税务司别墅里。她办公室的墙上更是布满了剪贴簿,它们详细地记录了她童年的点点滴滴。剪贴簿里贴满了公交车票、歌剧票根、请柬和各种纪念品,以及她曾就读的上海美国学校的文件。在这些剪贴簿里,记录着一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被摧毁,其后又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世界。李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担任顾问,然后慢慢地彻底退出了纷纷扰扰的中国事务。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开始致力于对那一时期历史真相的还原,他向人们忠实地阐述自己在华服务的影响和性质,并向媒体投稿,与历史学家交谈,尽力促成有关中国海关及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地位的相关研究。1981年,李度去世。
总税务司的别墅保留至今,当年海关的办公室和其他建筑,也依然散布在早已焕然一新的上海。建于1927年的上海海关大楼富丽堂皇,其上还有耸立的钟楼,如今,它依旧岿然屹立在上海滩的江畔上,却已不再是上海天际线最亮丽的风景。海关大楼顶层还留有当年通过轮船从英国运来的五口大钟,但如今震耳欲聋的现代扬声器代替了它们,飘扬在城市交通的喧嚣之上,徒劳地为现代上海的“城市交响曲”做出贡献。黄浦江沿岸的浦东区的高楼大厦高耸入云,使曾经受万人瞩目的上海滩黯然失色。那些塑造了上海中外形象的老建筑群依然矗立在上海滩。曾经掌握上海命脉的商号——怡和洋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 Co.)——把它们的总部设在这些老建筑里,而它们的洋人经理也会在工作之余参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事务。如今这些老建筑大多成了高档商店和酒楼。[2]然而,曾经的海关大楼依然是现在上海海关的所在地。如今上海海关的工作人员依然会从正门大厅熠熠生辉的马赛克下走过,由马赛克拼成的历代帆船战舰图,足以让今人一窥李度的前任北爱尔兰人梅乐和(F. W. Maze)爵士一大吸引人的个人癖好(他曾请人制作各类中国帆船战舰的大型木质模型,如今,这些模型依然被收藏在欧美各地的博物馆里)。随着几口大钟的退役,曾经响彻上海的威斯敏斯特钟声从此消失。梅乐和的舅舅、最负盛名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铜像,也于1943年被小心翼翼地从底座上移除了,据传后期侵华日军因为金属短缺而将这座铜像熔化。然而,上海海关依旧在高效率地运作着,今日的工作人员,仍在使用他们的前任用过的办公室,尽管窗外景色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海关的大部分业务也已改在河对岸一栋崭新的大楼里进行。今人可通过李度、梅乐和与赫德三人的历史追溯整个中国海关的历史,同样,从1854年到李度离华,在这期间任职于中国海关的1.1万名外国人也可以提供还原这段历史的线索——由外国人主导的这段岁月完全应该被视为海关历史的一部分。
作为在华洋人的生活遗存,类似的收藏品散布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包括所有有欧洲人移民并定居的地方)的家家户户中。当时在华工作的成年人,今天大多已经过世,但他们的子女却仍然健在,依旧收藏着他们父辈从那个迥然不同的中华世界里带回的随身物品和纪念品。在1949年之后成立的新中国里,所有旧的糟粕都遭到了唾弃,此时尚未离去的洋人,也缓慢地、一步步地走上了离华之路。大公司上缴了它们的资产、建筑和工厂,并召回了它们的外籍员工。银行成了党员总部,赛马俱乐部被改造成博物馆。新社会对旧时代的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进行了彻底改造。于是,淳朴的民歌取代了夜总会的爵士乐,会员包厢的墙上则布满了写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绘画。[3]20世纪90年代及其后的城市重建中,中国城市被工人们重新改造。即使被刻在建筑正面石头上和基石上的外国公司名称也常常会被削去,虽然它们仍不时会浮现出来。当然,这些用花岗岩砌成的建筑本身,其实也见证了另一个世界。尽管中国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与日俱增,但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些建筑,这些建筑常常会向我们诉说19世纪中叶之后(即鸦片战争结束后),那些踌躇满志的洋人是如何深入中国并取得可观成就的。这些建筑和中国复兴后兴建的那些钢筋水泥建筑物相比,自然是小巫见大巫,但它们也曾辉煌一时。
本书重访了那个世界。这并非本书首创,在中国的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你可以轻松地找到回顾这段历史的诸如《百年国耻》一类的书。你甚至可以找到一本使用起来十分便利的“国耻一览大全”(书名为《国耻辞典》)[4]。读者随便翻一翻,就能查到某次“大屠杀”、某个“条约”、某个“事件”。虽然某些历史事件的细节有待查证,但说到这段历史的宏观叙述,也许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倒背如流。无论是在学术著作还是通俗读物里,在博物馆还是学校里,在日常对话还是网络空间里,这类叙述一直被不断地重复。叙述的脉络大体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用他们的坚船利炮,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这些条约被胆小懦弱的汉奸走狗、腐败封建的清朝君主、军阀以及万恶的官僚资本家所接受。强加的这些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偏离了原本的轨道。中国国土沦丧,主权也遭受严重损害。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他掌管中国海关,完全是为了实现英国在华的野心。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侨民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法律对他们毫无约束力,因为他们只需遵守本国法律,服从本国的领事和外交人员——他们因此为所欲为。中国的沿海城市(甚至是深入内陆的地区)遍布着几十个受外国控制的“小国”。帝国主义者或在中国的街道上趾高气扬、顾盼睥睨,或乘坐人力车到处闲逛。他们在事业和日常生活上的一切享受,毫无例外地来自于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侮辱(比如剥削饥寒交迫的人力车夫)。此外,他们还对中国的领导层拉拢腐蚀,使后者趋于堕落。受到外国传教士的蛊惑和煽动,一些中国人开始与自己的文化和社群发生决裂。神州大地上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战争或外国侵略,以及其可怖的余波所带来的饥荒。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争非常频繁:先是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接着是中法战争(1883—1885)和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然后是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当时来自8个国家的军队入侵华北地区,之后俄军强占东三省,而八国联军则发动了旨在“惩罚”中国的血腥的军事行动。国耻还远远不止这些:其后,日本从1931年起侵占东三省,1937年更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04—1905年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中国领土,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1939年又在诺门罕兵戎相见。英国、日本和德国于1914年在青岛进行大战。人们惨遭战争荼毒,文化也未能幸免于战争的浩劫。许多无价之宝和历史古迹遭到抢掠或毁坏,许多图书馆被付之一炬。统治中国的皇帝兴建了金碧辉煌的圆明园,英法联军为了“惩罚”战败的清廷,于1860年恶毒地、有计划地将之烧毁。货车承载着从中国掠夺的宝物驶向海岸,继而运往欧美。作为清朝统治权力中心的北京紫禁城,于1900年被外国军队攻占。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进出紫禁城的各个大门,军官们则争先恐后地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留影。近40年后的1937年12月,历史重演,日本军队再一次侵入中国首都——这次,是饱受蹂躏的南京。日本人对中国及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无所不用其极——科技的进步,也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不设防的城市惨遭空袭,细菌战使得中国军民深受其害。中国国力日渐衰弱,在亡国的边缘徘徊。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许多人担心中国会灭亡,随着日本和欧洲掠食者对中国的蚕食和瓜分,他们尤其担心中国将会步波兰后尘,被列强完全瓜分。《国耻辞典》篇幅很长,该书厚度超过3厘米。
然而,在华外国人却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有关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并在不同的场合诉说着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被呈现在各种纪念活动和仪式上、公共聚会上,以及在给外交人员的措辞严厉的私人信笺里。在华外国人自然没有编纂能与《国耻辞典》相对应的工具书,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成就以及在华外国人中的杰出代表大书特书,此外,他们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凸显他们显赫的地位和巨大的成就。[5]他们这样认识并记录中国社会:这是个封闭且充满敌意的社会,外国人被城墙拦在城市外,被投石于街道中。清政府很不情愿地遵守着条约中的条款,把寸草不生的海滩淤泥地划给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而后者却努力经营这些“沼泽荒地”,使之繁荣发达。他们兴建了道路、沟渠、码头、现代银行、繁忙的洋行(办公楼)、仓库、教堂、学校以及俱乐部。他们建立了高效、民主的上海工部局,该局既负责疏导交通,也负责监督警察部队、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学校的运作,并最终行使了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的大多数职能。他们非常乐于回忆自己是如何兴建优质港口、在水边筑堤、清除港口淤泥、安装照明系统、制定合理手续,从而使人员的进出和货物的吞吐通畅无阻的。他们兴建铁路,绘制地图和图表,使一切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他们给中国带来了秩序、理性、卫生改善和救赎,更带来了科学和文化,使中国人得到启蒙开化。他们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曾经辉煌的文明正日趋衰弱,成了“亚洲病夫”,于是,他们拯救了这个文明。赫德和他的属下致力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清政府的刁难以及群众的仇外情绪有时还是会酿成排外事件,而这些事件只能由外国的坚船利炮解决。根据外国人的回忆,他们并不想和中国人兵戎相见,但是,一旦遇到不得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他们则会堂堂正正、全力以赴地作战。他们来华,是为了帮助中国,并使其走向世界。他们对善良朴实的中国人民充满了同情,对腐败无能的中国统治者却充满了鄙视。这些西方人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而为了捍卫这些权利,他们陈情、游说,有时甚至向清政府示威。他们声称自己了解中国并努力在为中国发声,而且他们还十分理解中国人,甚至比中国人对其自身的理解还要透彻。他们包揽了对中国的一切报道,为中国的领导者和各地军阀出谋划策,对中国的货币进行改革,此外,他们还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救治中国人的肉体。对于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引以为傲。他们声称自己一手兴建了上海,在发出恶臭的滩涂地上,建立了这座繁荣的大都市,开设了医院和大学,并且创造了许多的工作机会,他们还大力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革与现代化。令他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明明是他们把中国从内忧外患中救了出来,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感激他们?
中国近代史是如此复杂,要理清这些头绪纷乱的叙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根本就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6]即使删除《国耻辞典》中最严厉的措辞,该书列出的长长的“国耻”清单中的绝大部分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足以令哪怕是对中国的立场持有保留态度的观察者都犹豫再三。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那些带有强烈反帝色彩的叙述,关于民国时期外国在华事业的档案和各种文件(甚至包括那些丝毫不起眼的文字材料)读来依然触目惊心。与在华洋人相关的种族主义事件、奸淫案、谋杀案,以及各种残暴行为(包括战争及和平时期)和不公审判的证据堆积如山。盘踞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洋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行使的殖民主义暴力也许危害更大。他们思维模式僵化、言辞刻薄、行为粗暴而又血腥。在华洋人流连于他们所兴建的酒吧、夜总会、澡堂、公园、花园、滨江草坪以及游轮客舱,这些场所往往实行隔离政策。上海滩的公园一度挂有“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的告示。然而,即使是文盲,也很清楚那些使用公园设施的告示虽然看似无所偏袒,实际上却有所暗示。1933年,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沙逊大厦洗手间门外的告示上赫然写着“绅士”和“中国人”。[7]在洋人家里,大小姐或许会和厨师大吵一顿,洋人雇主也动辄会对佣人拳脚相向。他们大部分的交流犹如鸡同鸭讲,因为他们一般都缺乏共同语言。这种情景,就和在非洲或印度上演的一样。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做的一切有个朦胧的印象,对于相关细节,却所知甚少。尽管西方一般大众都熟悉当年鸦片对中国的祸害,但他们却更愿意把中国人本身塑造为毒品危害的源头,而非受害者。[8]唯有日本侵华战争足以引起外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因为二战期间欧美各国也同样深受日本之害,日军在1941—1942年的突袭,以及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各种罪行(包括虐囚行为),使洋人与中国人产生了共鸣。战争时期欧美和中国同仇敌忾、并肩作战,掩盖了中国与这些新盟友之间、中国人与西方来客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然而,我们今天往往会自我定位为后帝国主义者,认为我们距离那个年代已经足够遥远,旧日的疮疤早已愈合。有人或许会提出建议(也确实有人这么做了),忽略老一代中国通们的溢美之词(老一代中国通们的确言过其实,我们今天也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所说的话吧。或许我们还能在另一点上达成共识:考虑到时代背景不同、评价标准迥异,这些老一代中国通们不过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不应该用21世纪的标准衡量他们。他们在中国进行了建设性的工作,把新思想和新事物介绍到中国,也带来了新的办事规则和新的机遇,他们为塑造现代中国出了一分力。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和一些中国人达成了共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各种机构和企业都重拾自己曾被废止或摧残的外国遗产。“新中国”接管了“旧世界”,而且通过中英两种语言实现了这一点。青岛啤酒——中国最大的啤酒品牌——于2003年举行百年周年纪念,在对国内和全球的宣传中,他们都充满自豪地强调,该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当年的盎格鲁-日耳曼啤酒公司(Anglo-Germania Brauerie Company)。2001年,在上海交响乐团对自己120余年历史的追溯中,他们详细回顾了其乐团名称是如何在60年里从“镇交响乐队”“上海公共乐队”演变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并成为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啤酒还是交响乐团,其起源都具有鲜明的国际色彩。[9]他们丝毫没有谴责外国人,更没有和外国人翻反帝国主义的旧账,只是列出了老一代中国通们本身也可能提及的史实。这时,老一代中国通们或许会感叹,我们做出的贡献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我们终于盼到了迟来的感谢。
他们或许还会说,除了那些不断翻旧账的、迂腐的历史学家,今天肯定没有人还采用那种早已过时的思维分析这一切了,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在英国,这或许标志着公共记忆对不平等的对华关系的一种重温高潮,或者说,这至少使人们重温了历史上中英关系的轮廓。然而,香港政权的交接毕竟只是一个瞬间,人们对香港早期历史以及后来历史的了解仍然相当肤浅。最后一任香港总督登上最后一艘皇家游艇,黯然离开香港——这个画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仿佛时空错乱,并没有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印象。况且总体而言,英国人对其帝国时代的历史印象,大多止于印度、非洲,或者是很多人并不知晓的一些其他的英语世界地区,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前英国领地。欧洲大陆各国的记忆里更是缺乏中国的位置。德国的青岛租借地、上海法租界、比利时和意大利在天津的租借地鲜少在大学校园之外被提及,有的甚至是近年来才引起人们的关注。随着冷战的来临,美国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被蒙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及其支持者在华的影响力大于其他西方列强。[10]随着中国恢复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随着全球中国热日渐升温,这一切必将成为纯粹的历史,成为外国人眼中尘封的历史。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成为人们真正的关注点,而非过去的中国。我们希望了解中国社会如何运作,中国人如何思考,中国接下来又将会何去何从,以及中国究竟将会带我们走向何方。我们都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日渐强盛和富裕的中国将会给全球政治带来哪些变化。那么,关键的问题仍然在当下,而不是那段被淡忘得差不多,并鲜少被回忆起的过去。中国历史上的耻辱无关未来。
实际上,尽管表面看来,中国的过去仅仅是纯粹的历史,但如果我们不了解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那个动荡的世纪,就无法理解今天中国的复兴,更无法理解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冷静或激烈或严厉的态度。这是因为,即使只是纯粹的历史,在当今中国也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远未终结。不仅青岛啤酒厂和上海交响乐团还记得历史,国家更是如此。在官方语境中,中国人民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之后,才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从而拯救了日渐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对于这段中国民众的自我定位及其所阐述的自身存在的理由都带有国耻时代的深刻印记。[11]毫无疑问,当年在华洋人留下的遗迹其实无伤大雅,大多数甚至不太起眼,这些建筑物也不过于华丽,建造者并不希望以此来吹嘘自己辉煌的过去,或是回顾那段支离破碎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国难和外国侵略接踵而至的历史,而在其中,洋人扮演的都是负面角色。然而,这些建筑物曾经的主人们——当中包括诸如李度和埃尔茜·丹森一类的人物——却似乎和上述的负面角色扯不上任何关系。确实,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一百年,人们可以进行多种解读。对于这些洋人们来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很多人),作为理想主义者,参与并介入中国事务,并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帮助中国及中国人民(尽管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条件提供这种帮助的)。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因为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才阴差阳错地来到中国。随着外国在华事业蓬勃发展,这些事业成了19世纪日渐成形的世界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普遍的求职之处——无论是当护士、教师、打字员、海关官员、警察、推销员还是书记员。早在当时,世界就已经迎来了一阵中国热,大家以为只要能到中国待几年,趁机捞一笔,就能发一笔横财。实际上,等待这些淘金者的通常都会是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有秩序的、可预估的世界。身为一名速记员和私人助理,埃尔茜·丹森怎么可能如那些卷帙浩繁的“国耻实录”所描述的那样对近代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呢?所以,想要理解现代中国的思维模式、掌握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就务必要调和不同版本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经验——一般的、巧合的和充满创痛的。
本书将从意义深远的1832年开始叙述中西之间充满交流、对峙和混乱的百年历史。这一年,运载传单、布料和鸦片的英国船只从珠江三角洲出发,向北驶入禁止外国船只进入的中国水域,由此掀开了接下来几十年中国社会变化的序幕。其中3艘船属于1950年把李度运离中国的那家公司——怡和洋行。这家公司今天依然活跃于中国,其总部则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世界,其中的连续性自然很重要,但是其中并不存在什么宏伟计划或阴谋诡计。除非19世纪的欧美历史本身就可以被称为一项宏图伟业,否则,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和什么帝国主义的“宏图伟业”没什么关系。故事里的角色确实具有一些明显的倾向性,他们的某些反应也确实遵循着一定规律,这使得我们常常过分注意他们言行举止的重复性,而忽略了随机事件、机遇,甚至是失败,这些元素也同样塑造着这个世界。事实上,列强们很可能并没有一个详细而步骤明晰的瓜分中国的计划,而本书要叙述的,其实也正是这样一个混乱的过程。传教士、商人、雇佣兵都参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帕西人(Parsee)以及马六甲华人等世界各地人士也蜂拥而至。虽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在1832年之前并没有禁止一切对外交流,但是清政府严格监控着这种有限的交流,并且将之限制在沿海边缘地区的其中一隅。1842年之后,随着清政府大幅度放宽这些限制,由洋人及其中国合伙人组成的聚落形成于主要的沿海城市,并往北扩散,甚至远至滨海城市天津。本书试图探讨这些聚落的发展、经历的波折及其对中西关系的影响,从而解释这段时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意义和重要性。举例来说,为什么海关总税务司这样重要的职务,在1943年之前会一直由英国人担任,甚至还通过双边外交协定确立下来?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关这些问题的报告将会是一份来自内部的报告,一份来自一只怪兽肚子里的报告。这里并不属于大英帝国或法兰西帝国的正式领土,而是一片灰色地带。清政府统治着这个独立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又并非完全独立。这个国家疆域之内存在着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又与越来越多的西方帝国存在着紧密联系,并依托这些西方帝国茁壮成长。列强占领了不少中国领土,并在法文、英文、俄文、日文和其他语言印制的地图上堂而皇之地将之标示为本国领土。与此同时,列强的在华事业却又是多元性的,使用着不同语言的各国都参与其中,但是,当然,英语(毋宁说是不同版本的英语)始终是一枝独秀,其影响力也最大。尽管这个新世界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但通常视野狭隘,着眼于当地。作为一项多国事业,它的影响力和实力在1913年夏达到了顶峰。那时洋人对中国政府财政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正在演变的地方和全国政治也在有效地挑战着在华洋人之前的种种美好设想,削弱着他们的雄心壮志。我将会带领读者一起重新审视这一系列事件——从1832年那个决定性的一刻,直到西方在华事业达到顶峰的一刻,然而物极必反,这个顶峰也就是中国近代史这个黑暗而复杂的篇章走向结束的开始。
毋庸置疑,李度本人来到中国,也许就纯属机缘巧合,他当初肯定想不到自己会在中国度过四十多年光阴。1914年10月,他加入中国海关时,该机关正处于其权力和影响力的巅峰。就在那个月里,另六名美国人、九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芬兰人、一名意大利人、两名挪威人以及一名瑞典人也加入了中国海关,此外,这里还有五名中国人。这是一个相当具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调查,而在这份调查里唯独缺少的是德国人。此前每年都会有不少德国人在青岛的德国海军基地服役结束后不立刻回国,而是选择加入中国海关。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日趋激烈,选择留下的德国人减少了。事实上,英国人和德国人一直共事于中国海关,直到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李度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留意到了中国海关这个机构。他日后戏称:“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去中国还是和登月差不多。”[12]到中国工作,似乎是个不可思议的选择。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海关,更是难以适应该机关浓厚的英国色彩。一开始李度的确感到陌生和不自在,但很快他就习惯了中国海关的工作环境。开头提到的那张在台北的合影,是一条漫漫长路的终点。他先是在南京学习中文,然后被派驻厦门、北京、天津、上海,并于1934年担任了人人都梦寐以求的驻广州专员,最后从1943年开始,他承担起了管理中国海关的棘手任务。在1914年10月加入中国海关的这一批人当中,李度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这批人中,除了一名港口稽查员任职不到一个月之外,其他人的任期都超过三十年。与李度形成对比的是埃尔茜·丹森,她既是海关人员记录簿上屈指可数的外国女性,同时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上海外侨。她于1931年3月开始在海关担任速记员,两年后,她的妹妹也加入了海关。两姐妹的父亲乔治是矿主之子,他在由洋人掌控的上海工部局做了十五年警察,直到1905年被辞退。其后他又任职于港口管理局,直到1937年在上海逝世。[13]埃尔茜于1949年离开海关,这标志着她的家族结束了六十年侨居中国的历史。
埃尔茜·丹森是从上海警察部队下层起家的。乔治·丹森(George Danson)娶了一名海员托儿所的保育员,他们的子女把握住了当地环境提供的机会,在上海这个他们唯一了解的地方自力更生。他们极少回到英国。他们是众多侨居海外的英国家庭当中的一个,而英侨是继华侨和印侨之后,人数最多且分布最广的侨民群体。相比之下,李度有一个更明确的家乡定位。大学一毕业,他就选择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地方去碰碰运气。侨居中国的这段时间里,他始终和自己的家人,以及位于罗得岛波塔基特市的老家保持着紧密联系。李度第一任妻子是他老家的邻居,于1917年和他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在华事业规模日增,这使得在华美国人也越来越有底气,李度也积极参与其中。结果海关把出生于中国的“上海佬”埃尔茜·丹森和受过大学教育、具有全球视野却又恋家的美国人李度安排到了一起。解放战争最终迫使两人离开中国,李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埃尔茜则前往了陌生的英国。1842年之后洋人创立的在华事业,让李度、丹森家族以及和他们一样的数千名洋人来到中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工作;这里的一座座新建成的教堂见证了他们的婚礼和洗礼;这里一片片开拓出的坟地埋葬了他们死后的躯体。
1949年之前,洋人的在华事业所造就的世界以及那个世界所留下的种种遗迹,将会是本书探索的一个重点问题。那个世界仍然存在于那些石头和砖块砌成的建筑物里,也被记录在照片、图纸、地图、油画和水彩画里——尤其是中国画家卖给外国人的千篇一律的画作(这些画作往往绘有展现江畔建筑物风貌的经典场景)。从家庭相簿和林林总总的书籍里,也还能一窥当年那个世界的点点滴滴。在易趣网上可买到当年的文物,包括价格不菲的旧上海纪念币和老照片。中国的富豪都觊觎并热衷于收藏旧中国沿海地区的这些文物。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市政府把中国沿海地区和景点商品化的同时,海外的收藏家也用上海的文献资料开拓了一片新的市场。这些年,中国沿海城市里所谓的“老街”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旅游景点有时就位于崭新的购物中心里,那里有很多摆满古董复制品的复古餐馆和酒吧。于是,在中国这个摩登的国度里处处可见被重塑的过去。[14]然而,那个旧时代也被妥善地保存在档案文件里,这些档案有的像老一代中国通一样散布全球,有的则被收藏在离它们诞生之处不远的中国图书馆里。传教士的笔记、海关文件、庭审记录、领事通信等文件记录着那个时代的精彩片段和日常公事,记录着守法之人和不法之徒,记录着种种相关论证信息和统计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日记了解那个时代,无论这些日记是沉闷的还是带有桃色意味的;我们也可以读那个时代的个人自传,包括纪实自传和胡乱吹嘘的所谓自传;我们还可以看纪实小说,看谐趣诗或引人入胜的日志;更可以看流传至今的一些文物——剪贴簿里的戏票、请柬、邀舞卡和菜谱,它们无一不诉说着另一个世界业已逝去的时光。我并不想利用这些资料找出那些与洋人合作的中国人,并发掘他们的罪状,我只是想解释这一切为何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1832年珠三角一群时而漂泊海上,时而栖居在陆地的商人是如何向内陆挺进,如何软硬兼施地进入中国城市,并在城里修建马路和堤坝,还在路旁和堤边兴建各种设施的。蜂拥而来的人可谓鱼龙混杂,既有基督教的卫道士,也有市井小民;既有理想主义者,又有市侩的淘金者。他们并不只是创建了贸易据点,而是在主权国家之内建立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各有自己的宪法,人文历史也各不相同。这些“小国”构成的系统贯穿全国,它从沿海港口城市,沿着道路和河流深入内陆地区。
1832年,剧变前夕,洋人沿着中国海岸进行侦察的各种行动意义深远,这也是在本书的开头我将要进行叙述的内容。然后在接下来两个章节里,我会探讨19世纪30年代初外国商人和清帝国这两个对比鲜明却又紧密联系着的世界。接着我会阐述建立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新社群以及它们在各方面的发展,同时,我还将讨论催生出这些社群,并且推动这些社群发展的各种反复发生的战争和条约。商人、领事和传教士率先进入中国,其他人紧随而至。主权国家的部分地区被硬生生划为了边疆:在沿海地区,在护城河的城墙外的地区都属于所谓的“边疆”,之后“边疆”的分界线甚至也划到了郊区和农村。混乱随之而来,但洋人也创造出维持秩序的新体制,其中就包括赫德执掌的海关。本书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既然存在维护秩序的新体制,那为什么冲突依然一再发生,为什么华洋双方还是始终存在着敌意?相互间的不了解和信息的错误传递,一直严重影响着清帝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荣誉”在这个故事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尊严”也同样至关重要。中西交流的难题部分地源于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无论如何,双方都不可能给对方足够的尊严;第二,当其中一方感到受委屈时,另一方却不愿持理解同情的态度;第三,当其中一方完全没有蔑视和侮辱的意思时,另一方却认为自己已经受到了冒犯。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迎来了迅速的变化,但是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因为整个19世纪就是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纪。19世纪全球化的动力推动了清帝国的变化,清帝国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了全球化的动力。新科技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轮船、新式武器、电报技术、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介,这一切都决定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在这个时代,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既发生在全球,也同样发生在中国。快速演变的国际背景不断地给中国重塑着各种难题,但另一方面,中国的难题也在不断地塑造着整个国际的背景,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将是本书要讨论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同时,本书还将讨论新建立聚落的特性,以及促成这些聚落形成的条约,甚至是中国和欧洲文化的交汇究竟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中国的难题的。作为一份多国参与的“事业”,1913年之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日益瓦解。就在那一年,有一组外国利益集团——一个外国银行团——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笔巨额贷款,外国势力对中国行政控制之严苛,因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与此同时,另一组外国利益集团——管理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商人——企图扩大其控制范围的长期努力却遭遇挫折。中国20世纪的故事并不是这本书要探讨的主题,除了几个例外:本书仍将阐述人们对漫长的19世纪的理解是如何影响到20世纪的,又是如何影响到通往1913年的那条关乎胜利与失败的道路的。
在华外国侨民一向都十分在乎既有的历史,因此他们力求保持现状,而他们既有的历史也为此提供了依据。同时,在他们看来,这段历史还为各种各样而又永恒不变的那些中国特征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19世纪30年代及以前的种种事件经常被作为实行这项或那项政策的依据,又或者是反对这项或那项改革的依据。在洋人看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印象更强化了他们来华的使命感。[15]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这种想法促使他们采取行动,也决定了他们具有某种倾向性——他们往往声称:我们上次功亏一篑,我们太容易满足了,我们本来可以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下次当我们有机会时,我们务必要贯彻始终。一个社群往往会因为对自身历史的认同(或对自身历史的相同叙述)而团结起来——而这种历史,未必是成天泡在档案馆里的那些学者发掘或书写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之后组织起来的社群塑造了自己的历史。然而,在面对来自其他历史版本的挑战时,他们自身原有的历史版本最终还是被其他叙述取代了。对于一些人来说,某个事件或许值得欢欣鼓舞,而对于另一些人,此事却应当口诛笔伐。历史,向来既是公共行为,也是个人兴趣。当李度于1949—1950年间的冬天离开中国时,他一定会缅怀自己在华的三十五年时光,他或许也会思考这些中国的建筑物和遗迹是如何默默地讲述着他本人的过去的。海关在广州的临时总部位于前租借地沙面岛的海关大楼里,从1934年到1942年,他曾作为税务司住在这栋大楼里。感慨之余,他喟然长叹:“回忆啊,都是回忆,快乐的、悲伤的,那些回忆围绕着这栋老房子,这座历史悠久的岛屿,以及这座历史还更加悠久的城市,挥之不去。”他在此成婚,又成了鳏夫,还在此遭到五个月的囚禁——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他被软禁在家里的那段“寂寞的日子”。[16]伤感之余,他依然十分清楚这座“历史悠久的岛屿”所带给他的一切:“位于新教墓地里历史悠久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以及租借地本身美观的街道——那可是名副其实的林荫大道,道路两旁种了成排的樟树。广州几乎是一切的起点——在19世纪悄然来临之际,急于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以澳门为根据地,在这里敲开中国的大门。在1949年9月的香港,他发现自己身边尽是那些在中国服务多年的洋人家庭——其中一家有四代人在中国服务,另外还有两家则有五代人在中国服务。在中国服务了五代人的那两家人当中的一家和19世纪60年代“戈登”的“常胜军”有着紧密关系(“常胜军”曾代表清朝统治者,在上海郊区与太平天国的军队展开大战),另一家则与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相识,这家人通过这层关系,认识了整整三代的海关大员。[17]就在故事接近尾声之际,李度开始和人讲述那段历史并随身携带记载着那段历史的手稿中的一部分——他离开上海时,把赫德和赫德在伦敦代理人之间长达四十年的往返书信的完整誊抄稿,安全地藏在了他的行李箱里,这些誊抄稿翔实地记录了海关的历史,以及由此可以窥探的更大范围内的中外关系问题。在旧中国日渐崩溃之际,李度在广州阅读了这些誊抄稿并与赫德其中一名下属的女儿通信,讨论她为父亲的回忆录寻找出版商的事宜。[18]就在李度卸下总税务司职务隔天,偕叡廉博士(George William Mackay)就登门拜访(偕叡廉之父系1871年第一位赴台传教的加拿大新教传教士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马偕后娶台湾女子为妻,生下偕叡廉)。偕叡廉告诉李度,他至今还能“清楚回忆起”1895年日本人到来之前的台湾,自己曾目睹当时的海关专员美国人马士(H. B. Morse)“端坐在轿子上,由4个身穿白色制服的轿夫抬着”,一直从家坐到办公室。[19]就这样,正当旧世界已然消逝之际,两个耄耋老人在下着细雨的元旦,坐着回味早已远去的轿子时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让他们在彼时彼处相聚的那个世界,最初又是怎样被建立的?
注释
[1]Confidential Despatch to Minister of Finance, no. 98, 5 December 1949, in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L. K. Little papers, Ms Am 1999.18; I.G. Circular no. 21 (Canton–Taipei series), 27 December 1949; L. K. Littlediary, 5 December 1949-14 January 1950.
[2]介绍上海滩过去和现在的一本翔实的指南是Peter Hibbard的The Bund Shanghai: China faces west (Hong Kong:Odyssey, 2007)。
[3]介绍这个过程的一部经典之作是Beverley Hooper, China Stands Up: Ending the western presence, 1948-1950 (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刊物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新旧社会之间的冲突,这类刊物包括《上海今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
[4]本书和之前的《百年国耻》都是真实存在的。《百年国耻》1992年由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国耻辞典》(当时的书名叫《简明国耻辞典》)1993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5]诸如此类的叙事在大众历史著作和回忆录里十分常见。这本书后面会提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们的作者通常也参与了历史事件。读者也可参见Carl Crow, 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0); O.M. Green, The Foreigner in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42)以及J.V. Davidson-Huston, Yellow Creek: The story of Shanghai (London: Putnam, 1962)。
[6]旨在详细考察并调和这两个不同立场的一部早期著作是Hosea Ballou Morse的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0-1918)。考察时间范围更小,却同样十分详尽的一部著作是Henri 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 [History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Powers], 3 vols (Paris: Felix Alcan, 1901-1902)。考察条约口岸洋人社群社会文化生活的几部当代著作之一是Frances Wood的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 (London: John Murray, 1998)。James L. Hevia’s survey,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则探讨欧美外交辞令的特征以及在更广的殖民背景下,欧美外交家如何在中国使用这种外交辞令。
[7]Robert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 444-66; ‘“Gentlemen” and “Chinese”,’ People’s Tribune (NS) 5, 16 August 1933, pp. 68-9.
[8]参见Marek Kohn, Dope Girls: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drug underground (2nd edn, London: Granta, 2001)。
[9]参见阴山、纪卫华主编:《百年青啤》,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陈燮阳主编:《上海交响乐团建团120周年(1879——1999)纪念画册》,1999年。
[10]Harold R.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1958)(Armonk: M.E. Sharpe, 1980)至今读来仍然十分精彩,该书着重描写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力。
[11]关于当今中国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国耻”目前在中国的生命力,请参见William A. Callahan, China: The pessoptimist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Conversazione’ transcript, 16-17 December 1971, G.E. Bunker, K.F. Bruner, L.K. Little: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John King Fairbank papers, HUG (FP) 12.28, Box 4.
[13]Danson family information: various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and related records; L.K. Little, ‘To whom it may concern’, 6 January 1950 in L.K. Little Papers, Ms Am 1999.14; and courtesy of Joanna Helme.
[14]Hanchao Lu, ‘Nostalgia for the Future in China: The resurgence of an alienated culture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75:2 (2002), pp. 169-86.
[15]拙作《英国在中国》探讨了这个现象,参见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2.
[16]L.K. Little diary, 30 April 1949.
[17]L.K. Little diary, 12, 13 September 1949.
[18]L.K. Little papers, Ms Am 1999.18; Little to Evelyn W. Hippisley, 4 June 1949.
[19]L.K.Little diary, 1 January 1950.
①此处应指作者写作此书时的时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