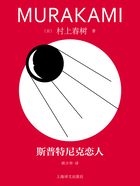
斯普特尼克:孤独的恋人 恋人的孤独(译序)
林少华
恋人,相爱相恋的人,是处于最为快乐幸福人生阶段的年轻男女,理应是最不孤独的人,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河滨海滩,成对成双。然而这本书中的恋人竟是那么孤独——无他,因为他们是斯普特尼克恋人。斯普特尼克,Sputnik,一九五七年苏联相继发射的世界第一颗、第二颗人造卫星的名字,发射后再未返回。六十多年过去了,想必早已在茫无边际的宇宙中化为孤独的金属残渣,沦为失去归宿的太空遗物。而在地球这颗太阳系第三行星上仍是活着的存在,其形式就是这本《斯普特尼克恋人》。只是,其含义不再是“旅伴”,而大体是“旅伴”的反义词:“孤独”——孤独的恋人、恋人的孤独。
应该说,孤独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那时我懂得了:我们尽管是再合适不过的旅伴,但归根结蒂仍不过是描绘各自轨迹的两个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上我们不外乎是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当两颗卫星的轨道偶尔交叉时,我们便这样相会了。也可能两颗心相碰,但不过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就重新陷入绝对的孤独中。总有一天化为灰烬。”
是的,“我”、堇、敏,“我”和堇分明是再合适不过的恋人,两颗孤独的心相碰在大学校园,碰出美丽的火花,在校园路上、在宿舍里相互倾诉不尽的心事和幽思,精神上是那般若合符契。然而不巧和不幸的是,堇是同性恋者,对于男主人公“我”如岩浆一般迸发的激情全然无动于衷:“老实说,我理解不好性欲那个玩意儿。”“我”告诉她性欲那东西不是理解的,只是存在于那里。随即“堇像注视某种以稀有动力运转的机器一样端详了好半天我的脸”。相反,对于比她大十七岁的同是女性的敏,堇却爱得如醉如痴要死要活,“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迅猛的恋情”。然而同样不巧和不幸的是,敏不是同性恋者(甚至已不再是异性恋者),对她的恋情毫无反应。在常规恋爱中热辣辣有无限吸引力的性,在这里则沦为将两人冷冰冰分开的“隔离带”,以致“我”、堇、敏成了斯普特尼克,只能沿着各自的轨道运行,也曾交叉,也曾相碰,但只是一瞬之间,下一瞬间即两相远离,在无限黑暗的宇宙中再次陷入各自的孤独中。
性与爱的分离、灵与肉的分离,或精神与本体的分离,以及性爱与性别的分离,这本来是村上文学主题之一,此前此后在其他作品中屡见不鲜,但都不及这次这般一以贯之。孤独则堪称村上文学的母题,但密度如此之大的也为数不多。这里的孤独,已经没有了《且听风吟》中“海潮的清香”和“女孩肌体的感触”;已经不能像《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中那样化为微茫情绪进而升华为审美对象;也已不再带有《舞!舞!舞!》中可以把玩的都市“小资”情调。一言以蔽之,已不再是相对孤独,而是绝对孤独——好比与地面失去联系的斯普特尼克,“被孤单单放逐到漆黑的太空”。于是“我”只能强行抑制自己身上几乎势不可遏的冲动,“堇”只能像烟一样消失不见。至于敏,则“由于某种缘由彻底一分为二”,在“这边”的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或“半个我已去了那边”——自己同自己的分离、自我分离,自我割裂。
为什么人们都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我思忖着,为什么非如此孤独不可呢?这个世界上生息的芸芸众生无不在他人身上寻求什么,结果我们却又如此孤立无助。这是为什么?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
这不仅是“我”的疑问,而且是堇和敏的疑问。进一步说来,也不仅是“我”、堇、敏三人的疑问,甚至也是和“我”保持情人关系的性取向毫无问题的那位家庭主妇的疑问。“我”是小学教师,半是因为无法和堇身心融为一体,遂与若干女性保持权宜性的性关系,其中一位就是那位主妇——自己班上一个男生的母亲。而在处理完这个男生奇特的超市扒窃事件之后,“我”更加觉得不宜长期保持这种关系,果断提出最好别再见面了。“既是问题的一部分又是对策的一部分是不可能的。”对方告诉“我”不能相见对于她是相当痛苦的。随后带着哭腔说了这样一番话:
“还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主动跟我说话,给我讲种种样样的事情,愉快的,美好的,神秘的。可是过了某一时间分界点之后,再也没人跟我说话了,一个也没有。丈夫也好孩子也好朋友也好……统统,就好像世上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有时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身体都透亮了,能整个看到另一侧了。”
你看,这是多么似乎虚幻而又深切的孤独!这位长相大概不错的中年主妇,当年想必也曾怀有五彩缤纷的梦想,周围充满无数浪漫的可能性,觉得人世那般温馨可爱,而今一言难尽,就连唯一能够交谈并给予欢娱的人也要弃她而去,给出的理由是“这不是正确的事”。当她一再追问什么是“正确”的事或“正确的事是什么事”的时候,“我”也没有回心转意。是的,作为教师——小学教师,大学教师恐怕不至于——同所教学生的母亲发生男女关系,无论谁怎么看、也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都是“不正确的事”——“正确”与孤独之间,作为公职人员,作为教师,“我”选择“正确”当然正确,而把孤独留给了女方、留给了那位家庭主妇。而且那不是一般的孤独,孤独得“身体都透亮了,能整个看到另一侧了”。至于留给她这样的孤独是否“正确”,则不是“我”能回答和解决的,毕竟每一个人都不过是宇宙中描绘各自轨迹的孤独的金属块儿,“远看如流星一般美丽,而实际我们不外乎被幽禁在里面的、哪里也去不了的囚徒”——绝对的孤独。
对了,可想知道“我”这个教师是怎么做通那个问题男孩儿即情人的儿子的思想工作的?“我”向男孩儿讲了自己从小到大的孤独感:“心情就像是在下雨的傍晚站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久久观望河水滔滔流入大海。你可曾在下雨的傍晚站在河口观望过河水滔滔入海?”
还有,书中有一只作为绝对孤独意象的小猫。那是堇小学二年级时养的一只三色猫,一天傍晚一溜烟蹿上自家院里一棵大松树,“抬头一看,小小的脑袋从很高很高的树枝间探出来”。不料猫再未下来。“我觉得猫正紧抱着树枝战战兢兢,吓得叫都叫不出来了。”猫就那么消失了,“简直像烟一样”。而这未尝不可视为一种暗示,一种征兆——后来堇也从希腊一座小岛上消失了,杳无踪影,“简直像烟一样”。
是的,“另一侧”,敏和那位主妇不同——前面也说了——敏不是看到“另一侧”,而是有一半去了“另一侧”,去了“那边”。村上二〇一七年在对谈集《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坦言:“如果没有那种忽一下子‘去了那边’的感觉,就不会成为真正让人感动的音乐。小说也毫无二致。不过那归根结底只是‘感觉’、‘体感’,而不是能够逻辑性计划的东西。”的确,村上小说中的确有不少人忽一下子“去了那边”。《舞!舞!舞!》中的“我”在海豚宾馆里眼前忽然漆黑一片,随即见到了“那边”的羊男,又在夏威夷去了“那边”见到了喜喜和目睹六具白骨;《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田村卡夫卡跟随一高一矮两个士兵穿过茂密的森林,翻过山脊后很快沿下坡路进了“那边”——“那边”有小镇、有为他做饭的十五岁少女;《奇鸟行状录》里的“我”几次在井中、在走廊里忽一下子穿壁去了“那边”;《刺杀骑士团长》中的男主人公所进入的地下迷宫和又黑又窄的地下隧道明显是“那边”无疑。至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简直可以互为“这边”与“那边”,而演示更多的无疑是主人公进入的“那边”的风景、那边的营生。凡此种种,所谓进入“那边”,换言之,即进入异境或超自然天地。以中国文学语境来说,大约就是进入了“桃花源”,只是未必“土地平旷,房舍俨然”,未必那么让人“怡然自乐”。顺便说一句,日语称“桃花源”为“桃源郷”。
关于“超自然”,二〇〇三年作者村上回答俄罗斯一位读者提问时这样说道:
我的小说中出现的超自然现象,……归根结底是一种隐喻(metaphor),并非实际发生于我的人生的事。不过在我写故事的时候,那些现象则完全不是隐喻,而是那里实际发生的事,在我眼前、在我心中实有其事。我可以活生生感同身受,可以实际目睹和描绘。
写小说,可能和做梦相似。尽管不是真人真事,然而对于做梦人来说,映入眼帘的梦境都是实际发生的事。换个说法,可以说小说家就是醒着做梦的人。我想那是一种资格、一种特殊能力。(访谈录《每天早上我都为做梦醒来》)
自不待言,《斯普特尼克恋人》是一个恋爱故事,准确说来,一个同性恋故事。而这里说的“超自然”也好隐喻也好,其实都和幻想有关。于是有一位法国人具体针对这部小说问是不是恋爱故事与“幻想次元”相互碰撞的结果。村上回答,书中的三角恋爱关系并未遵循这种模式,因为其中含有同性恋因素。随即谈及想象力:“我对同性恋一无所知,所以驱使了想象力。觉得自己能够知道两名女性之间将会出现怎样的事态。《斯普特尼克恋人》讲的是‘死亡之恋’,从一开始即被宣判有罪。不知为什么,我很中意这样的故事。”(出处同上)而在回答前面提到的俄罗斯读者时又以虚构一词谈起这种想象力、这种“幻想次元”:“(小说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不曾实际体验过的。我本人的实际人生是相当乏味、相当平静的。但是,无论多么不值一提的日常性事物都能从中提取又深又大的戏剧,我想这就是作家的工作。从细小的、日常性现象里边发掘其本质,将其本质置换为别的东西——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东西,所谓虚构(fiction)就是这么回事。”
无须说,无论虚构还是想象力抑或“幻想次元”都是文学创作、文学阅读上不言自明的常识。而村上则由此往前推进了一步,“忽一下子‘去了那边’”。《斯普特尼克恋人》里面,最典型和匪夷所思的,是敏从小镇摩天轮上用望远镜在远处自己所住酒店的窗口看见了自己:小镇上的一个外国男人正赤身裸体地玩弄和侵犯一丝不挂的自己,而自己居然任其玩弄,甚至把自己的身体“毫不吝惜地在他面前打开”。作为结果,从此失去自己的另一半,另一半“去了那边”,敏随之失去了性欲,失去了激情,失去了爱的能力,头发也变得雪白雪白。任何读者看到这里都要满脑袋问号——怎么会这样?无论如何也太离谱了!这意味着,村上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拒绝常识、拒绝理解、拒绝回答的小说。若勉为其难,回答只有一个:超自然!
重复一句,从虚构、想象力或“幻想次元”往前推进一步就是“超自然”。不仅如此,村上还在另一领域往前推进一步:尝试文体(语言风格)的变革。这点他早在二十年前的二〇〇三年就强调过,二〇一七年又一次说关于《斯普特尼克恋人》“动笔时就想对以前的文体(style)来个总决算”。同时承认“对文体来个总决算进而创造新的东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毕竟不能马上使用从未用过的肌肉。只是作为心情把文体转往新的方向性。新的文体催生新的故事,新的故事加强新的文体。这样的循环再让人开心不过。”为此必须先把此前的“村上春树文笔”即运用比喻的轻快笔调彻头彻尾用到极致,而后“引出不同文体”。其最初的表现即是接下去写的《海边的卡夫卡》。至于这一文体变革——这倒不至于“忽一下子去了‘那边’”——是否成功,老版译序已有表述,这里恕不重复。
不过既然这里说到文体,那么还是让我索性再就文体铺排几句,说一说村上的文体或文体家村上,尽管已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据村上本人介绍,他的小说已在世界各地被译成五十多种语言。一次接受《朝日新闻》采访,记者问其小说何以如此一纸风行的时候,他说:“(获得世界性人气的)理由我不清楚。不过恐怕是因为故事的有趣和文体具有普世性(universal)渗透力的缘故。”(2008年3月29日《朝日新闻》)故事之所以有趣,一个原因想必在于他对于小说创作、对于文学的特殊认识和实践。而文体或语言风格的“普世性渗透力”,应该主要来自文体特有的艺术性,即其作为文体家的特殊性。
应该说,小说家比比皆是,而文体家则寥寥无几。因为文体家必须在文体上有所创新,用独具一格的表达方式为本民族语言、尤其文学语言做出经典性贡献。记得木心曾说文学家不一定是文体家。他还说,“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鲁迅祭》)二〇一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在文体方面也有明确的认识:“毫无疑问,好的作家,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家,肯定都是文体家。”他还表示:“我对语言的探索,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因为我觉得考量一个作家最终是不是真正的作家,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他有没有形成独特的文体。”
实际上村上也是极为看重文体的作家并为日本作家轻视文体的状况表示气恼。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宣称“文体就是一切”。(参阅日本《文学界》1991年4月临时增刊号)。二○○八年五月,他就其翻译的美国当代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长篇小说《漫长的告别》接受日本主要报纸之一《每日新闻》采访当中,再次不无激动地表达了他对文体的推崇和迷恋。他说自己为“钱德勒的文体深深吸引”,“那个人的文体具有某种特别的东西”。而他之所以翻译《漫长的告别》和重译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目的就是为了探究其“文体的秘密”。同时指出,文体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节奏或韵律(rhythm)。并在比较菲茨杰拉德和钱德勒的文体之后提及自己的文体追求:“想用更为简约(simple)的语言传达那种文体的色泽、节奏、流势等等。”最后断然表示:“我想用节奏好的文体创作抵达人的心灵的作品,这是我的志向。”(参阅2008年5月7日《每日新闻》)在那之前接受日本另一家主要报纸《朝日新闻》采访时他也提到文体,认为文体是其作品在世界各地畅销的一个主要原因。还说写作是相当累人的活计,为了在每一部作品中拓展新的可能性,必须每天坚持跑步——“一是身体,二是文体”。(参阅2008年3月29日《朝日新闻》)。亦即从身体和文体两方面“去掉赘肉”。
村上在长篇小说《刺杀骑士团长》问世两个月后出版的对谈集《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再次强调文体的重要性:“我大体作为专业作家写了近四十年小说,可是若说自己至今干了什么,那就是修炼文体,几乎仅此而已。反正就是要把行文弄得好一点儿,把自己的文体弄得坚实一些。基本只考虑这两点。至于故事那样的东西,每次自会浮现出来,跟着写就是。那东西归根结底是从那边来的,我不过是把它接受下来罢了。可是文体不肯赶来,必须亲手制作。而且必须使之天天进化。”并且强调“笔调就是一切”。村上还说日本文坛不怎么看重文体,很少有人正面对待文体。相比之下,认为主题第一重要,其次是心理描写和人格设定之类。“我考虑的,首先是文体。文体引出故事。”
那么村上的文体特征表现在哪里呢?
我想是不是主要有四点。一是简洁或洗炼(シンプル),二是诙谐或幽默(ユーモア),三是音乐性或节奏感(リズム),四是三者共通的异质性。
简洁者,如《挪威的森林》第一章开头部分:
Δ我扬起脸,望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Δ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快满二十岁的时候。
幽默者,如《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开篇第一页关于电梯的描写:
我现在乘的电梯宽敞得足以作为一间小办公室来使用,足以放进写字台放进文件柜放进地柜。此外再隔出一间小厨房都绰绰有余,甚至领进三头骆驼栽一棵中等椰子树都未尝不可。其次是清洁,清洁得如同一口新出厂的棺木。
如何?不管谁怎么看,电梯都是现代社会最不幽默的、以实用为唯一目的制造的器械,而村上硬是让人始而怦然心动,继而会心一笑。即使“棺木”的比喻也并不让人产生多么不快的感觉。对了,《挪威的森林》有个比喻可谓异曲同工:主人公渡边也说“我的房却干净得如同太平间”。这样看来,村上的文体未必只有英文翻译腔、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味儿——村上有一本插图随笔集《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也未尝没有日本传统俳句、俳谐的酵母包含其中:诙谐、机警、不动声色、暗藏机锋。
关于节奏、节奏感,《舞!舞!舞》中主人公“我”对拒绝上学的女孩雪说道:
学校那玩意儿用不着非去不可,不愿去不去就是。我也清楚得很,那种地方一塌糊涂,面目可憎的家伙神气活现,俗不可耐的教师耀武扬威。说得干脆点儿,教师的百分之八十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虐待狂。满肚子气没处发,就不择手段地拿学生出气。繁琐无聊的校规多如牛毛,扼杀个性的体制坚不可摧,想象力等于零的蠢货个个成绩名列前茅。过去如此,现在想必也如此,永远一成不变。
笔底生风,一气流注,而又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节奏推进如爆豆一般。听得本来就不愿意上学的女高中生更不上学了——我想,这本书肯定不会被教育部列为中学生课外读物。
最后,关于三者兼具的异质性。显而易见,村上尽管是日本作家又不同于其他日本作家,尽管深受欧美作家的影响又有别于欧美作家,其作品尽管被翻译成了中文,而又无法混同于中国本土原创作品。一句话,村上就是村上,自有其独特的异质性和陌生美。这里仅以《斯普特尼克恋人》中几个关于月亮的比喻为例:
Δ可怜巴巴的月亮像用旧了的肾脏一样干瘪瘪地挂在东方天空一角……
Δ白光光的月如懂事的孤儿一般不声不响地浮在夜空。
Δ月犹如闷闷不乐的司祭一般冷冰冰地蹲在屋脊,双手捧出不孕的海。
Δ无风,不闻涛声,唯独月华默默地清洗地表。
Δ从山顶仰望天空,月亮似乎惊人地近,且桀骜不驯,一块久经动荡岁月侵蚀的粗暴岩球而已。
喏,肾脏、孤儿、司祭,原本哪一个都和月亮无关,村上却偏偏有本事使之和月亮发生关系,让人始而费解,继而释然,再而莞尔,明显有异于日本以至中国常规的或传统的比喻手法。第四句不说常说的“月华如水”,最后一句的“岩球”说的倒是实话,但说在这里反而成了戏谑,别有妙趣。总之,无论对于村上的母语日语,还是对于我们的母语汉语,这类比喻都消解了惯常性、本土性或熟识美,而带有别开生面的陌生美、带有出人意表的异质性,以及由此生成的恬适静谧而又不无诡异的超验性艺术氛围和审美体验。
村上甚至这样说道:“文章修辞这东西,是一种锋利而微妙的工具,一如刃器。或适可而止,或一剑封喉,用途不一而足,其间无非一页纸的距离。如果对此了然于心,或许就等于了解了自己。……忘乎所以地一心致力于文章打磨,就会倏然产生得以俯瞰自己意识天地的瞬间,仿佛阳光从厚厚的云层一泻而下。”换个表达方式,文体或文章修辞即是我们本身,即是我们同外界打交道的姿态。人云亦云的庸常修辞,所表现的往往是一个人才气的不足、精神的懈怠或者态度的傲慢;而令人耳目一新的修辞,则大多是卓尔不群的内心气象的折光。是的,好的修辞、好的文体是对自己的内心和世界的谦恭与敬重。
与此相关,我笔下的村上,较之小说家村上,更是文体家村上。从而给汉语读者带来一种异质性语言审美体验,同时多少拓展了汉语的疆土边界,为现代汉语的艺术表达带来某种新的可能性和启示性。进而影响了一些文艺青年说话的调调、写作的调调以至做人做事的调调。或者莫如说这不是我的贡献,而是翻译的贡献,汉语本身的贡献。
三句话不离本行,作为翻译匠总要最后讲几句翻译。这本书是二〇〇一年寒假翻译的,二月二十六日发给上海译文出版社。那时我像斯普特尼克一样从广州孤单单流移到青岛不是很久,必须说,是《斯普特尼克恋人》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朝朝暮暮的孤独与孤苦。因此,数年后的二〇〇七年二月和现在这两次重校和撰写译序当中,当时的记忆与情思都带着特定的温度倏然复苏过来。一本值得感激的书,一次令人沉醉的翻译旅程。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杏花春雨万象更新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继荣休的沈维藩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的姚东敏副编审和我联系,希望重校之余重写译序。十五年前的译序,侧重依据自己接触的日文第一手资料提供原作的创作背景,介绍作者的“创作谈”和相关学者见解。此次写的新序,则主要谈自己的一得之见,总体上倾向于文学审美——构思之美、意境之美、文体之美、语言之美。欢迎读者朋友继续来信交流。亦请方家,有以教之。来信请寄: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浮山校区离退休工作处。
[斯普特尼克]
1957年10月4日,苏联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拜科努尔宇航基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1号。直径58厘米,重83.6公斤,每96分12秒绕地球一周。
同年11月3日又成功发射了载有小狗莱伊卡的斯普特尼克2号。卫星未能回收,小狗莱伊卡作为遨游太空的第一个生命体,成了宇宙生物研究的牺牲品。
(据讲谈社《编年体世界通史》)
(1)俄语CПУTHИK的音译,意为“旅伴”——译者注。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