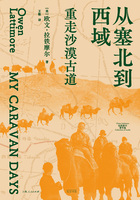
1929年版序
我将这本书命名为《从塞北到西域:重走沙漠古道》,是因为旅途中所走过的路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那些穿越蒙古,或者从蒙古通往西域的所有商队路线上的沙漠地带。它在商队中的独特名称是“绕路”(Jao Lu或Winding Road),即“蜿蜒之路”;但是,与其他地方相比,无论是在草地,还是在“明地”(放垦地带)的边缘,这条沙漠之路都一直引人注目。我在通往西域的沙漠之路上,度过了四个月的时光,这是我从北京到印度的陆路之旅的第一篇章。我在1926年独自完成了蒙古之旅,到了来年初,我的妻子在西伯利亚边界附近的塔城(Chuguchak)与我会合,我们一起穿越了中国西域,并越过喀喇昆仑山前往列城、克什米尔和印度。
在第一章中,我对蒙古商队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充分的概述,为叙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另一方面,我已经尽量在故事中不对古代商贸路线及其对如今使用的商队路线产生的影响进行过多专门的讨论,同时除了对中国和俄国之间那些遥远和鲜为人知之的经济和政治变迁作粗略评述之外,也不会再涉及更多的内容。
由于这次所涉各地区的人名拼写依然是一个尚未得到权威性解决的难点,因此我认为有理由选择自己的标准。在突厥语名称的拼写方面,我遵循了皇家地理学会名称委员会的建议。然而,对于汉语名称,我已经背离了如今已被广泛接受的中国邮政式拼音。邮政式拼音体系表面上具有现成的一致性优势,尽管很便捷,但它不是基于连贯的单一转写方法。因此,我采用了韦氏转写法,可在名称的音节划分上,我有自己的判断。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我的关注点:
兰州(Lan Chou,“兰”是这座城市的名称,是正确的发音,而“州”则是古代王朝体系下的一种行政级别)
归化(Kuei-hua,这两个用连字符号串起来的单字,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名称,它的行政级别常常在人们使用口语时被遗漏)(1)
古城子(Ku Ch’eng-tze,古是“古代”的意思,“城子”则指“城市”,自然就成为一个双音节名称)(2)
我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合理化的是,这些汉语地名,尤其是在遥远的内陆地区,主要为两种理应得到更多关注的人带来好处:一种是了解当地语言知识的旅行者,正如我所知道的,他们常常顾名思义,从名称含义上得到线索,进而获得帮助;而另一种则是仍然不甚仔细的人,他们喜欢通过名称线索帮助自己查字典找到那些地名。我还自然而然地保留了几个名词/地名,这些都已经有很完善的英文版本了。强行将“Tientsin”(天津)转回原本的“T’ienching”,就像是使“Wien”(维也纳的德文拼写)回到“Vienna”一样,没有什么意义。至于那些我所经手的名词/地名,我在本书索引当中已经用其他的拼写作了补充,对于“Lan Chou”(兰州),我写成“Lanchow”,对于“Kuei-hua”(归化),我写成“Kueihuating”(归化厅)或“Kueihuacheng”(归化城),并将“Ku Ch’eng-tze”(古城子)写成“Kuchengtze”或“Guchen”(古城)。对于这些地名之外的汉语名,我也使用韦氏拼写,但是有那么一两次,我没有将这些词汇从一种方言形式转换为更为典雅的北京“官话”。
还有一些蒙古语名字与词汇,大部分我都不得不按照语音拼写出来了,但愿我听到的发音是正确的。对于这些名称和词汇,我没办法故作精确或者具有权威性。我在正文中可能提到过,在处理蒙古语词汇时,我将表示黑色的词汇拼写为Khara,例如Kharakhoto(喀喇浩特),即黑城或黑水城。但是,更古典的Kharashahr(喀喇沙尔)(3)的意思也是黑色的城市,我将其替换为QaraShahr,为的是遵循皇家地理学会的体系,因为这里的Qara并不是蒙古语,而是突厥语。在此,我希望近期出版的关于蒙古地区的一幅官方地图,能够为转写提供一种权威方法。
总而言之,对于这两种拼写形式,我们必须特别加以关注。我所确信的是,在指称巴里坤湖和巴里坤山脉的时候,最好写成分开的Bar Köl,而Barköl则最好用来指称城镇,完全省略汉语指称城镇的官方名称——“城市”,其口语名称Pa-li-k’un(巴里坤)不过是Barköl的讹变。
我的“权威”,即我对之前旅行者的参考,我已经在脚注中作了明确的说明,而不是将它们一股脑儿放到本书最后的书目里面。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走向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是我在阅读现代旅行作品时注意到的,但这些作品中只有少数几本是真正的好书。一种极端是将所有的东西都读过,包括那些毫无用处和毫不相关的东西。另一种极端则是一种倾向,很遗憾,我自己的同胞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那就是忽略所有的参考文献,从而造成了很恶劣的假象,即一个人一直在完全未被探索和未被测绘的地带旅行。因此,在每一处我受惠于某本书的地方,我都会指出我所受何惠。对那些对蒙古地理感兴趣的人们,我会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哪些地方是迄今为止尚未探索过的。我应该补充一点的是,由于没有科兹洛夫(Kozloff)作品的英文版,我能利用的只有《地理》(La Géographie)杂志对他探险之旅(我也到过他的那些区域)的概述。
如今,在中国腹地进行旅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我自己的旅行,虽然孤身一人且小心谨慎,但如果没有许多人的帮助和善意,这次旅行也不可能成功。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本书的出现将表明他们的帮助没有白费,这也体现了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但是,我还必须特别表达对《京津时报》时任编辑伍德海先生(H. G. W. Woodhead)的敬意,感谢他最初的鼓励与支持;还要感谢潘绮禄先生(Pan Tsilu)在西域的友谊,并提供舒适的办公室;也要感谢我的前雇主们——天津安利洋行各位收货人的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前往其内地贸易代表处的介绍信。我还要感谢位于罗马的地理学会、位于巴黎的地理学会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它们慷慨允准我在回来后使用相应的书籍与地图。
(1)归化是呼和浩特的旧称,此处应指呼和浩特老城。呼和浩特源自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明建归化城,清建绥远城,置归化、绥远二厅,1912年改厅为县,1913年二县合并为归化县,1914年改归绥县。1928年绥远建省,以归绥县城区设归绥市,为省会。1952年起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1954年改今名。——译者注
(2)又名古城,在今新疆奇台县。——译者注
(3)即今新疆焉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