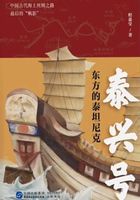
第9章 1821年 东石陈家船厂
庆瑜仍然每天都被渔歌叫醒,每天都会闭着眼听那海浪涌来拍打海岸的声音,再迷迷糊糊徘徊于半梦半醒之间。但奇怪的是,自从新道台来了之后,就很少见到父亲的身影。不知怎的,父亲和他就好像错开了时辰,很少碰到面了。庆瑜晚上睡着的时候,父亲经常还没有回来,早上他醒来的时候,父亲大都在卧室里睡觉。餐桌上大家也都很安静地吃饭。虽然以前碍于父亲的威严,大家吃饭的时候也很安静,但现在的安静和以前的安静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安静只是暂时的安静,大家的心里都是含着期待,轻轻压抑着清晨的雀跃,而现在的安静是毫无期待的,也是毫无生气的安静,仿佛不知道朝阳已升,万物醒来,尘世间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庆瑜偶尔还庆幸,父亲这样就没有闲暇来管他了。父亲也的确好长时间都没有过问他的事了。他有没有去周先生那里上课,他每天都在干什么?父亲好多天都没有过问了。但,父亲对自己不闻不问,庆瑜又有些失落,觉得自己像失去了指明灯的船,在海上毫无目的地漂泊。
这一日,庆瑜决定无论多晚都要等父亲回来。
夜已深,一片寂静,庆瑜卧室里的灯还亮着。他坐在椅子上,手捧着一本书恹恹欲睡,终于趴在桌子上睡过去了。但因为心里的执念,外面的轻微响动还是惊醒了他。是父亲回来了!他立刻起来扔下书,跑出去。
正是父亲。他微微有些醉意,正要向卧室走去。
“爹爹。”庆瑜跑过来扶住他。
“庆瑜啊,怎么还没睡?”因微微醉意,父亲的眼神里比平常多蕴含了些慈爱。
“我在等爹爹。”庆瑜说。
“哦,有事吗?”玉平遥问。
“也没什么事,就是想等爹爹回来。”庆瑜犹豫着说。
“哈,我这阵子都没顾上管你,你不是应该很开心吗?”玉平遥想了想,就在厅堂的椅子上坐下来。
“爹爹说笑呢。”庆瑜由衷地说。
“嗯,最近都按时去周先生家上课了吧?”玉平遥又问。
“都按时去了。”庆瑜点点头。
“周先生可还好?”玉平遥又问。
“他很好,还让我问你好。”庆瑜说。
“嗯,有机会请他到家里来一叙,也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对了,前日有人从京城给我带了几罐好酒,明天你给你先生带去一罐,再给谭伯伯送去一罐。”玉平遥若有所思地说。
“好的,爹爹。明天我送过去。”庆瑜说。
“爹爹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帮爹爹分担一些的。我看爹爹最近都好忙啊,是不是新来的道台不好应付啊?”庆瑜忽然又说。
“唉,新来的道台呢,是钱督抚的亲信。他一来,钱督抚就有了帮手,之前的那些旧账就都翻出来了,他是来帮钱督抚跟我们算总账来了。麻烦得很哪!”玉平遥沉默了片刻,抚额说。
“爹爹,他们是要银子吗?”庆瑜问道。
“当然是要银子。”玉平遥惆怅地说。
“要多少才够?”庆瑜又问。
“哈哈,大概要东石每家都倾家荡产,他们塞进自己腰包才好吧!爹爹之所以不想让你做生意,就是因为这个。我大清朝官大于商,无论我们经商作出多大努力,挣下多大的家业,究竟抵不过一纸文书,这偌大的家业甚至可能会在顷刻间毁于一个口谕,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啊。”玉平遥叹息道。
“天哪!”庆瑜惊叹。
“也没那么严重。”玉平遥勉强地笑笑。
“爹爹,我来帮你吧。需要我做什么,你就说。多一个人,多份力量。”庆瑜立即又说。
“眼下,爹还真有件事让你去办。你哥哥也没有工夫去。不如,这几天你去看一趟我们的新船吧,有日子没有去人了,也不知道新船现在造到什么程度了。”玉平遥思忖了一下说。
“爹爹,是泰兴号吗?”庆瑜提高了嗓门。
“对,就是泰兴号。你要是找不到船场,让邱伯陪你去。”玉平遥点点头。
“啊,太好了,爹爹。不用,我找得到,之前大伯带我去过。”庆瑜惊喜地说。
“呵,我就知道,你大伯背着我没少宠溺你。”玉平遥嗔怒道。
“嘿嘿。爹爹,时间不早了,我扶爹爹去睡吧。”庆瑜喜滋滋地说。
“我哪里老到需要你来扶。”玉平遥笑道。
庆瑜还是将父亲扶进卧房,母亲还没睡,见父亲进来,忙起身扶着他上床躺下。庆瑜这才回了房间。
不过,庆瑜因为窃喜又失眠了。
次日上午,庆瑜便按照父亲的吩咐,带着酒罐去了周先生那里上课。周先生很高兴,还倒了一小杯跟庆瑜同饮,连连称赞酒好甜。可庆瑜并没品尝出来甜味,他的心里长了草,只想快点结束,他还要去告诉昭儿,他要带她去看他玉家巨大无比的新船。
庆瑜带着酒罐来到谭家的时候,已经是午饭过后。谭家仆人给他开了门,告诉他小姐在后面的染坊,让他在厅堂等候,小姐一会儿就过来。庆瑜将酒罐交给仆人,自己去染坊找她。
走过几个回廊,庆瑜就来到了谭家染坊附近。染坊外面,宽阔的场地上,数十排青蓝印花棉纱被高高挂在栏杆上,整齐地迎风飘飞,远远望去,那些印花像蓝色的蝴蝶成群飞舞,蔚为壮观。阳光正好,这些飞起的棉纱在地上映出长长的影子,那些影子也在地上荡来荡去,甚是好看。而就在这些影子中间,现出一个窈窕的人影,庆瑜笑了。他开始寻找这个窈窕的身姿。这身姿就隐藏在这若干青蓝印花之间,他走过去,走过一排排的栏杆。这青蓝棉纱像故意跟他玩耍,因风舞动,不时蒙住他的眼睛,他用手拂开遮在脸上的棉纱,再去寻。那窈窕人影明明就在那里,他却怎么也找不到她。日头很大,他的额头已经渗出汗来。他有些急了,却听“咯咯咯”的笑声从对面那排栏杆传来。然后,昭儿从两排青蓝棉纱中走出来。她步履轻盈,双手背在后面,两眼含笑。阳光洒在她的面颊上、头发上,她被笼罩在毛茸茸的光晕里。忽地,两排棉纱又被风吹起,掠过她的面颊,她伸手轻轻拂开散落下来的发丝,继续走向他,笑意盈盈地走到他的面前。
庆瑜看得呆了。
“庆瑜,你怎么来了?”昭儿笑道。
庆瑜恍惚了好一会儿才说:“哦,我来给谭伯伯送酒,是有人从京城给我爹带回来的,我爹让给谭伯伯送一罐来。”
昭儿:“哦。那谢谢玉伯伯了。”
“昭儿。”庆瑜又压低声音,看了看四下没人,贴着她耳朵说。
“怎么了?”昭儿小声说。
“昭儿,我明天带你去看我家那大船。”
“真的?!”昭儿惊喜道。
“当然是真的。我其实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庆瑜挠挠头说。
“那太好了!不过我爹娘明天都在家……有了,我就说我去看铺子。”昭儿思索着说。
“那就说定了,明早吃过早饭就去啊。”庆瑜道。
“好。吃过早饭。”昭儿道。
“那我先回去了。”庆瑜快乐地说。
“好。”昭儿点头道。
第二天庆瑜起得很早,很少见地和大家一起吃了早饭。奶奶奇怪地问庆瑜不睡懒觉吗?庆瑜说父亲让他去看看新船的进度,没想到筱女嚷着说要一块儿去。好在母亲说,筱女就要考试了,还是让庆松送她去书院,以后有机会再去。筱女不高兴,庆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奶奶又说让邱伯陪着同去,庆瑜急忙说不必,自己去就行。庆瑜草草吃过早饭,便匆忙出去了。奶奶担心地塞给他几个杧果,一边喃喃道:“要走十里路呢,带着吃,免得口渴,天这么热。”“我坐船去。”庆瑜说。
庆瑜心里欢喜着、雀跃着。他一路小跑跑进竹林,等候昭儿。半刻钟不到,昭儿便来了。她一身杏色丝绸罗裙,淡红色薄纱半掩面颊,匆匆赶来。
“昭儿,你来了。”庆瑜欢喜地说。
“是呀,庆瑜,还好我娘相信了我的谎话。”昭儿笑道。
“我们去坐船!”庆瑜说着便大步向前走去。昭儿小跑几步跟上。
两人穿过竹林,向海边走去。刚好海边停泊着一条小船,庆瑜拉着昭儿跑过去。船家问去哪里,庆瑜说不远,就邻镇。小船便向东南方向驶去。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在海边,远处有个身影正凝神看着小船远去的影子。
半个多时辰,小船就到了邻镇,在岸边停泊下来。庆瑜和昭儿下了船,往镇子里走去。
从海岸边往镇子里面,地势越发低下来,举目望去是林林总总的木质桅杆和高耸入云的船帆,直将那些灰瓦翘檐也压了下去。
“哇!这里都是造船的吗,庆瑜?”昭儿惊讶道。
“对,整个镇子都是以造船为生。所以你看,到处都是船,造好的,修理的,废弃的,都有。你看,这里,每个区域都是一家的船,大家都有自己的区域。”昭儿举目四顾,海岸线上显然有很多家,各家的区域划分得很明显,中间都有很大间距。每一家的船只都停泊在一起,拥挤却很有秩序。
“哦,是这样啊。那我们去谁家?”昭儿问。
“我们去陈家,这里最厉害的就是陈家。”庆瑜拉着昭儿往前走。
“有多厉害?”昭儿问。
“你知道郑和下西洋吧?”庆瑜道。
“郑和谁不知道啊,当然知道。”昭儿说。
“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大船,其中就有陈家先辈建造的。”庆瑜停下来。
“真的吗?”昭儿不相信地说。
“真的!而且,后来郑成功施琅收复台湾的战船,也有陈家长辈的功劳。”庆瑜又急匆匆地拉着昭儿向前走。
“这都是真的吗?”昭儿问。
“当然是真的。”庆瑜道。
“那太厉害了!”昭儿说。
“是啊,所以玉老爷只用陈家制造的船。玉家的每艘船质量都是上乘,这艘新船,更是巨大无比,除了陈家,谁家也没有这等实力建造啊。”庆瑜又说。
“玉伯伯也好厉害!”昭儿说。
“到了,昭儿,就是这里了。”庆瑜驻足望了望,便拉着昭儿快步走进一个场地。
一个偌大的场地。场地里摆放着数不清的木料,它们长短不一、薄厚不同、形状各异,都是船上的组成部分,却都是未完成品。数十名工匠正在忙碌着,有搬运的,有打磨的。场地里的噪声很大,工匠们打磨木料的声音、搬运的号子声、彼此喊话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人应接不暇。
庆瑜拉着昭儿沿着场地的一边拐进一个高大的石门,石门里面是一个很僻静的庞大院子。昭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她听姨娘说紫禁城很大,大到从南到北要走上一个时辰,这个院子该不会有紫禁城那么大吧。从这里根本看不到院子另一边的尽头。在这个庞大的院子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船体,只能看出来是船体,没有船帆,没有桅杆,它的表面也还是木头的颜色,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它实在是太大了。
庆瑜拍了拍这艘巨船,说:“瞧,这个就是泰兴号。”
昭儿不免有些失望:“就这个啊。”
庆瑜看懂了她的心思:“别着急呀,这还没造完呢,早着呢!造完之后会很漂亮的,会比福临号还漂亮。”
昭儿“哦”了一声。庆瑜又道:“走,我带你去见个人,你就知道了。”
庆瑜带着昭儿快步走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一个大屋子,庆瑜敲了门。里面有人问:“是哪位?”
庆瑜道:“耀云在不?”
里面又应道:“哦,是三少爷来啦!快请进,快请进!”
庆瑜推门进去,昭儿也跟进去。
屋子很大,里面摆放着一些木料,应该是船的构架,但显然这些木料已经经过精细打磨,都很精致。屋子里有几个工匠在写写画画,都很认真,一丝不苟。陈耀云手里拿着毛笔,他的脚边放着十几个小铁桶,里面装着各种颜色的颜料。他的毛笔上蘸满红色颜料,正在往身旁的一块木板上涂颜色。
陈耀云见他们进来,便放下笔。
“三少爷,好久不见。”陈耀云起身行了个礼说。
“是啊,我今天带个朋友过来玩。谭昭儿。”庆瑜说。
昭儿解下面纱道:“陈公子好。”
昭儿只微微一笑,陈耀云便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撬动了,地动山摇。他顿了顿,缓过神来说:“该不是谭总商家的千金吧?”
庆瑜道:“还是耀云聪明,没错,就是谭总商的千金。哈哈,我爹让我来看看,我偷偷带她来玩的,别让我爹知道也别告诉谭总商。”
陈耀云:“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去给你们倒杯水来。”
庆瑜:“不必客气啦,你干你的,给我们讲讲。那艘大船,泰兴号,什么时候能造完?我刚才看还没有模样呢!”
陈耀云:“三少爷,您别急,造船哪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家虽然世代造船,像泰兴号这么大的船,我家这么多年也是头一次造。别的船还得造大半年呢,何况这么大一艘巨船。不过,也已经很快就有雏形了,再等几个月就能完工了。我爹说尽量在这个秋天完工。”
庆瑜:“不急不急,还是按照该有的速度,父亲交代,一定要造好。”
陈耀云:“那是自然,请玉老爷放心就好,我陈家世代造船,什么时候也没出过岔子。”
庆瑜:“好。对了耀云,你这是在干吗呢?给我们讲讲,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怎么就造出一条大船来了?”
陈耀云:“我在给这艘要完工的船上色。你看,这艘船,先要安放龙骨,这是龙骨,之后呢,安装这个隔仓板。这个是水密舱,根据船的大小不同,水密舱的设置也不同。之后呢就可以铺设‘肋骨’了,就是这些。然后再雕刻船壳外板,还有舱面甲板,还有上色。我现在就是在给这个船壳上色。最后才能安装‘龙目’,竖起桅杆和船帆。”
昭儿:“哦,这么复杂的呀。”
陈耀云:“是啊,很多程序的。”
昭儿:“这些花纹好像妈祖衣服的花边图纹啊?”
陈耀云:“对的,船侧身的这些花式,都是按照妈祖衣服花边的样式。”
庆瑜道:“还有这些。”
陈耀云:“对,这些是妈祖靴的花纹,雕刻在上面,都是保佑平安之意。”
昭儿:“每艘船都要经历这么多的工序最后造成的吗?”
陈耀云:“是啊,所以你们刚才来看见了吧,我们需要很多工匠,夜以继日地打磨,才能在大半年完成一艘大船。”
昭儿:“好不容易啊。”
庆瑜:“真是辛苦你们了,耀云。”
陈耀云:“辛苦是辛苦,高兴也真是高兴。每一艘大船出海,都是我们的荣耀。自己亲手打造的东西能够游行于这个世间,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
昭儿:“我听庆瑜说,陈家长辈还造过郑和下西洋的船,还有郑成功的船?”
陈耀云脸上浮现出一丝自豪,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说:“这是当时我陈家先人去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明成祖朱棣赠送的诗句。”那幅字因年深岁久,已经辨认不清,但它一直被挂在这里,是陈家的至尊荣耀,也是陈家精神之最高表征。陈耀云又走到角落一个桌前,从衣袖里掏出把钥匙,用钥匙打开抽屉,从抽屉里小心翼翼捧出一本泛黄的书来。
“瞧,这是我们陈家先人留下来的《尺寸簿》,每一页都详细记载着所有内容,什么船的每个部位什么尺寸,都有详细记载。我们陈家代代相传的。”
“真好。”昭儿满含敬意地说。
昭儿和庆瑜抚弄着那些即将成为船舷、船帆、仓板的精致木料,感叹不已。陈耀云还让昭儿涂了几下颜色。
陈耀云望着她,竟然想将藏了一辈子的话都说给她听,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直到庆瑜说,时间不早了,再不回去天黑之前就到不了家了。陈耀云发现自己竟然很舍不得这个女孩离开,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话都没来得及跟她说。而此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她,那些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跟她说了。只是,如果能再见,那些话自然会蹦出来吧!
陈耀云恋恋不舍地送别了两人,直送到海边两人上了船,看着那艘小船远去,又一个人坐在礁石上看着远方很久,才寂寥地慢慢回去。
回程的时候,昭儿一直看着乘坐的这艘小船。小船很小,只能乘坐四个人,并没有刚刚陈耀云说的那些复杂的构造,但昭儿一直盯着小船的每个部位看来看去,偶尔海面上有大船擦身而过,昭儿便更是看得仔细,直到大船遥遥远去。她蹙起眉认真的样子让庆瑜暗暗发笑。
已近黄昏。小船回到东石村,停泊靠岸。
等在海边不远处的阿元看见昭儿的身影,便撒腿向巷子口跑去。
就在上午,阿元来海边恰好看见庆瑜和昭儿上船,他望着两人乘船远去,便立刻跑回赵府向赵梦乾报告了此事。赵梦乾立刻怒了,骂他废物,问他跑回来做什么?还不乘船去追。阿元立刻又跑出去要乘船去追,赵梦乾又说罢了罢了,你跑回来折腾这么久,哪还追得上了。赵梦乾又想到两个人会不会是去私奔,便问阿元他们带了什么东西没有?阿元说没有,应该是去办什么事或者去哪里玩。赵梦乾咬着呀恨恨地说:“敢带着我的姑娘偷偷出去,看我饶不了你!”于是在午饭后,赵梦乾午觉也没睡,换了衣服,索性和阿元乘马车去了海边等候,又不想马车在海边太过突兀,就停在了海岸附近的一处巷子口。
直等到黄昏,赵梦乾在马车里睡眼惺忪,却听见外面噼里啪啦的声音。他掀开帘子,便看到阿元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少爷,他们……他们回来了,船马上靠岸了。”阿元说。
“好,我去看看。”赵梦乾睡意顿消,麻利地下了车,向海边跑去。阿元停了片刻,又跟在他后面跑。
两人一路小跑到了海边,就远远地看见一公子拉着谭小姐的手下船。那公子小心翼翼,谭小姐笑意盈盈,两人下得船来,相互对视,眉目含情。看来今日一行两人更是增加了许多情意。
赵梦乾越看越气,右手使劲合上扇子,左手攥紧拳头,咬了咬牙。
“少爷,那个男的就是玉庆瑜。”阿元凑过来说。
“知道。”赵梦乾哼了一声,便冲他们走去。
庆瑜和昭儿正有说有笑,迎面看见赵梦乾走过来,庆瑜下意识将昭儿拉到身后。
赵梦乾压抑着怒气道:“这么巧,在这儿遇见谭小姐和……这位公子是玉总商的公子吧?两位刚回来的样子,这是去哪里了?”
庆瑜:“赵公子查过我?有什么事吗?”
赵梦乾:“哦,只是碰巧,我来海边走走,也正好问下谭小姐,我上次想定的绸布,有货了吗?”
昭儿:“很抱歉,赵公子,定同样的绸布通常是没有的。那条街上绸缎庄很多,公子多逛逛,一定能找到好看的料子。”
赵梦乾:“我这个人啊,懒得很,就觉得谭小姐家的料子最合意,就懒得去逛别家铺子了。”
庆瑜:“赵公子,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一步。”说完便拉着昭儿走开。
赵梦乾:“谭小姐,我改天再去铺子看看。”
昭儿当没听见,没有回头,和庆瑜走远。
赵梦乾捡起一块石头使劲向海里扔去,却被忽然翻卷而来的浪花打湿了衣衫,脸上也被溅了水珠。他恼火地用衣袖擦了脸,大踏步往回走。
“回去!”他说。
“是,少爷。”阿元跟在后面不敢吭声。
赵梦乾和阿元回到赵府,赵府已经掌灯。赵道台已经回府,府上也到了吃晚饭的时辰。赵梦乾只吩咐阿元:“就说我头疼,先不吃了。”他回到卧室换了衣服,阿元将湿衣服拿走,便小心地退出去了。
赵梦乾在桌前坐下来,又气恼地将桌上的书和纸笔推翻到地上,而后,一个人对着桌上的灯,竟落下泪来。
站在门外的阿元听到房间里的声响,轻轻叹息道:“唉,少爷,这又是何苦呢!”他慢慢走远。
委屈、落寞、不甘。多年的情绪在赵梦乾的身体里堆积如峰峦,此刻就如要崩裂一般。对于父亲来东石任职道台一事他是很抗拒的,对于父亲他也是抗拒的。按照母亲的说法,她怎么也没想到,生出这么一个顽劣的少爷。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人真正懂过他。
他想念京城,想念京城的日子,更想念那个曾占据他全部身心的女孩。
五年前,他16岁,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在一个雪日。那一日,已经两年没有雪的京城忽然天降瑞雪,白色的雪花铺天盖地。父亲一大早就出去了。他和阿元偷偷跑出去玩,一路跑到紫禁城的附近。遥遥地看见紫禁城被白雪覆盖,那红色的围墙越发鲜红,显出不同于往日的气派和神韵。两人正在望着,就见一女孩身披红色斗篷,站在不远处,正在向里面张望。这女孩让赵梦乾想起《红楼梦》里的女子来。该是《红楼梦》里的哪个女子呢?黛玉?不好不好,也不像,这女孩神色自若,毫无自怜之态。宝钗?也不太像,这女孩看起来很纯净天真,毫无心机。那么探春?也不是,探春自带一种决绝和英气,这女孩温婉得很。惜春?那更不像。元春?啊,呸呸,不会,元春是嫁到宫里的,她不该是元春。她还是不要做《红楼梦》里的女子了,那些女子都没有好归宿。她就……她就做她自己就好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女孩,因戴着斗篷,看不太真切,却仍见其身姿轻盈,温婉灵动,双目顾盼生辉,因冷气而隐约含着晶莹。
赵梦乾呆望着她,那一刻,这世间只有纯白的雪花和红色的佳人,再无其他。此后,这一幕就在他的心上封了印,再也不曾抹去。
那一年她15岁,她那日是因为要看雪,央求父亲带她一起出去。父亲要去早朝,她便在马车里等候。但她忍不住好奇,便从马车里跑出来看被雪覆盖的紫禁城。她感觉到了遥遥的目光,便转身去看,就见一少年正呆望着她。她好奇地看了他一眼,像明白了什么,嫣然一笑。那笑容如一汪泉水注入了他的胸膛,他受到了鼓励,走向她问:“你是在等人吗?”
“是啊,我在等我爹爹。”
“你爹爹?”
“对,我爹爹在上朝。下了朝之后就会从这儿走出来。”
“哦,你爹爹是谁呀?”
“不告诉你。”
“哦。”
“你会玩雪仗吗?”
“我是女孩,我娘是不会允许我玩男孩子的游戏的。”
“哦。这样啊。”
“好冷,我要回车上去了。”
他追了过去,她上了车。
“嘿!”他在车下边说。
她掀开帘子看着他。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这紫禁城晚上闹鬼的事吗?”他说。
“你吓唬谁呢?不过我也不害怕,我又不住这里。”她说。
有很多官员从紫禁城里走了出来。她看了他们一眼对他说:“我爹爹他们下朝了,我该走了。”
“哦。”他看见有个官员往这边走过来,他便走远了一点。
忽然他又想起什么,又跑了两步过来对她说:“你还什么时候来这里?”
“我也不知道,也可能就不来了吧。我爹爹不会答应我总跟着他的。”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你为什么找我呢?到底有什么事吗?”
“就是,想跟你一起玩啊。”
“我很少出来呀,只是有时候会去沈绣娘的绣坊那里学刺绣。”
“那是哪里?”
“沈绣娘你都不知道?不说了,我爹就要来了。”她放下帘子。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蕊。”
她的爹爹走了过来,他只好走远。他看见马车遥遥地走远。
“蕊,你的名字真好听!”他大声地喊。他的声音被淹没在漫天飞雪里,雪花落在他的脸上又融化了。
这个他一眼就看中的女孩,他以为她会是他的妻,他想着等他到18岁就会娶她。可是,没有料到,两年后,这个女孩成了秀女,走进了紫禁城,便再也没有出来。
他不知道,当年那个雪日,她站在紫禁城门口是不是就已经注定了她将走进那扇宫门。看见她的那一刻他还曾在心里猜度,她究竟应该是《红楼梦》里的哪个女子更为合适?那一刻他最不希望她成为元春。没想到,老天如此捉弄,她真的成了元春,只是,或许还未及元春。她踏进了这扇门,步步惊魂,命运如何,一切都只是赌注。他与她从此相隔,这紫禁城尘封了她的人生。而他,绝无半点办法。她成了他心底无法祛除的烙印和疮疤。
选秀前日,他见了她最后一面,她带了小妹一起来。那小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一笑露出两颗小豁牙,很懂事地站在门口处给他们把风,听到声音就赶紧让他们藏起来。他和她挥泪告别,遗憾此生都不能在一起。他将他祖传的玉佩给她戴上。她送他亲手绣的锦囊。他知道,以她的样貌,被选为秀女是迟早的事,只是,没有想到,她第一次参选就入选了,一切来得太快。怎奈,一切已成定局,他无力更改,更无法想象,她成为人人艳羡的皇妃受皇帝的恩宠抑或她被人陷害沦为素人都与他毫无半分瓜葛。她和他在两个世界,绝无丝毫交集。
此后,他病了很久,对一切都很厌烦,尤其厌恶父亲对圣上和官员那一副卑微的样子。他更加游手好闲起来。他最喜欢的女孩都被剥夺了,他还有什么怕失去的,无非换来父亲的一顿家法和母亲喋喋不休的絮语与责骂罢了。他甚至讨厌起自己的家世来,他倒宁肯做一介草民,至少草民还会有很多朋友和玩耍的伙伴。而他,除了阿元,什么都没有。
如今,来到了东石,离京城更加遥远,深宫中的蕊更加遥不可及。曾经,听说蕊在深宫中得不到皇帝的宠爱,他是很开心的,他爱的女子,是应该属于他的。但他同时又对她的安危非常担心,得不到皇帝的宠爱,便意味着接下来步步凶险,孤苦无助,那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她承受的。可,又能如何?只能任由岁月在夜深人静之际在他心里千刀万剐。时间久了,就麻木了,也就不觉得疼了。至少,疼得不那么清晰。
一切的改观始于谭小姐的出现。他见她的第一面就觉得他们似曾相识。自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只有她能治愈他心里陈旧的伤疤。他如此渴望见到她,如此渴望她能陪在他身边,时时刻刻都不要离开。然而,这世间对他是何等的不公平,他好不容易又看中的女孩,为什么她早已心有所属,为什么那个玉公子会有机会陪伴她一起长大。为什么老天总是捉弄他,好不公平,好不公平!
他的心又开始绞痛起来,撕裂般疼痛。他捂着胸口抑制不住狂喊一声:“老天爷,你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