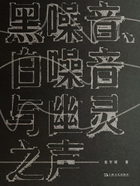
一、表象与在场:艺术的政治学
要真正理解卢梭的音乐哲学,有必要从两个视角出发。从大的视角看,音乐在卢梭的整个哲学体系(尤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之中占有着关键地位,甚至可以说音乐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一个本质性途径。但音乐何以能够起到此种作用?接下来还须将音乐作为一种具体的艺术形式,进一步阐释卢梭对于它的种种基本构成要素(尤其是旋律,和声和节奏三要素)的具体分析。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让我们先从前一个方面入手。
在《卢梭思想中的音乐、政治、戏剧与表象》(Music, Politics, Theater, and Representation in Rousseau)一文中,杜根与斯特朗(C.N.Dugan & Tracy B. Strong)详细深入解析了音乐与卢梭政治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们首先明确提出问题:既然卢梭集中将政治中的“表象”(representation)作为批判目标,那么,音乐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成功地挣脱了表象牢笼的解放性的艺术形式?
卢梭对“表象”的批判集中于《社会契约论》中对主权(souveraineté)概念的探讨。主权无非就是“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运用”。(7)而公意在卢梭含混复杂的文本之中至少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具体行动,二是超验原则。(8) 作为具体行动,它总要和不同的个体相关;但作为超验原则,它又指向着人民的总体。显然,在公意这个基本概念中,个体与总体之间的关联这一核心问题已明确提出。而主权正是实现这一关联的本质性纽带。卢梭对主权的基本界定有二:“不可转让”(inaliénable)和“不可分割”。而他对“不可转让”这一最基本的原初特征的论述则直接与表象问题关联在一起:“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被表象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被表象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9) 虽然卢梭的用意是针对霍布斯的契约论(如克里斯托弗·伯特伦[Christopher Bertram]所指出的),但这个论述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原则:公意作为一种意志,其自身是不可能被转让、给予他人的。原因很简单,意志的本性是自由和自主,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总是直接的(虽然会受到种种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影响):或是肯定性的,即实现为行动;或是否定性的,即未能实现、受到阻碍。你可以放弃行动的权力,接受奴役;你亦可以转让行动的权力,让别人代劳。但就意志本身而言,是断然无法被转让或放弃的。如杜根和斯特朗所敏锐意识到的,这里涉及的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难题,即在场性(10)。简言之,卢梭的论证要想成立,必先设定一个基本前提,即意志本身的纯粹在场性的可能。意志不可被转让因其不可被表象,这就意味着它不能通过其他的中介环节来呈现自身,而只能是纯然地、直接地呈现自身。“主权具有这样的特性,它只在当下在场并如此呈现给我们。”(11) 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引申出两个推论:一方面,从个体性的角度看,意志的实现始终指向具体的、当下的情境,由此体现出一种不可还原的偶然性特征,看似无法对其做出普遍、绝对的界定。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别种角度来理解意志的普遍性:意志是普遍的,并非因为它指向着某种抽象的理性法则,而是源自它的纯粹在场所体现出的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永恒”维度(atemporal nature)(12)。
这些论述又再一次从学理上印证了卢梭对启蒙的批判,或者说,以追寻普遍理性法则为宗旨的科学与形而上学“理论”显然无法实现他所追求的主权意志的纯然、直接的呈现。但当我们回归艺术之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艺术之中亦存在着表象艺术和非表象艺术之分。在卢梭看来,所谓表象艺术的代表正是戏剧。在《致达朗贝尔的信》(Lettre à M. D’Alembert)中,卢梭从这个角度对戏剧进行了尤为激烈的批判。他指出,戏剧虽然总能表达强烈的情感,也能够由此深深地打动观众,但问题在于,此种情感并非源自观众中的每一个不同个体的意志的真实表达。或许正相反,观众只是戏剧情感的被动接受者:他总是“被”感动,“引起”共鸣。戏剧看似总在营造着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共鸣,总在尝试着建立起群体之间的最为普遍的情感维系,但脱离了个体身上的意志在场这个源头和基础,所有这些营造都是虚幻性的。(13)在戏剧之中,如果说真有何者的意志得到表达的话,那就既不是观众,更不会是舞台上亦步亦趋的演员,而只能是背后操纵一切的作者。这就进一步导致两个恶果。在对柏拉图文本进行转译和阐释(其实更多是借题发挥)的《论戏剧摹仿》一文中,卢梭首先指出,正如(在柏拉图那里)摹仿隔开了事物和原型,在戏剧之中,表象同样也隔开了观众与真实情感,使得人们越来越满足于成为单纯的“看客”而非积极的参与者。(14)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表象和摹仿不仅隔开了真实,而且还遮蔽乃至扭曲了真实。(15)这主要是因为,不管是否出于明确意识,创作者的情感和偏好都在不断地或明或暗地左右着观众自身的真情实感,从而他的主观视角也就相应地取代了每个个体的真实判断。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亦越来越沦为作者意志的玩偶。这样也就导致个体的体验和判断的能力不断削弱,从而也就最终导致个体的意志力量的不断衰弱。(16)而且,作者为了让他的作品更有吸引力,更能“俘获”观众,往往会诉诸一些约定俗成的“套路”,得心应手地让观众们按照他自己所安排的方式来笑和哭。
如此描绘的戏剧无疑是令人生厌的。卢梭忆及他童年在日内瓦观看广场庆典的场景,并由此感叹,戏剧不是生活,唯有生活才能真正展现戏剧般的力量。舞台上的戏剧毋宁说是削弱、剥夺了真实个体的生活意志和能力(17),而唯有投入生活的戏剧之中,个体与群体之间才能形成真实的共鸣和融汇: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和狂欢的氛围,每个个体都真实地表达着自身的舞步,而彼此之间又形成了默契。这里,没有谁是别人意志的傀儡,大家也没有遵循着任何现成的套路和惯性的程式。“这里,每个成员都表现着整体,他们彼此需要,就像体验自身那般来体验他人。”(18)
那么,音乐何以能够产生此种直接沟通的力量呢?首先我们可以断定,对比戏剧,音乐具有诸多优势:它同时将“体验”“意志”和“判断”的力量真实、直接地还给每一个自由个体。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细读卢梭的《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摹仿》(Essai sur l’origine des langues, où il est parlé de la Mélodie, et de l’Imitation musicale,下简称《起源》)。这篇卢梭死后出版(1781年)的短论经由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的精妙阐发(有时又确实过于冗长拖沓),越来越吸引了卢梭研究者的目光(限于我们的论题,主要参考《论文字学》“摹仿”这一节)。而从“摹仿”的角度深入反思音乐的认知功能和本体地位,也越来越显示出深刻的启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