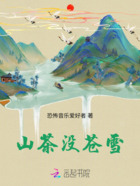
第25章 春日宴3
没有舞娘,没有乐团,今天这宴会上,献艺的无非达官贵人和勾搭达官贵人的俗子,说是意境欣赏,实则计谋颇多。
下座的参与者,只等着自家过继的哪个姑娘、哥儿被上座的人瞧上。
情投意合最好,露水情缘不赖。
只要是在这权势圈里留了芳名,自家的各路生意都会顺利好多。
若是真真遇上正缘,还可好好捞比大的,搁谁谁不乐?
献艺的人走了一波又一波,上座的人却都稳稳坐着,没有一个有要人的打算。全偷瞄着那个坐在高位的红衣小孩。
手上觥筹交错,口中汝善他善,心中算珠飞迸。哪还留的眼睛往这舞池里瞧上一瞧?
再美的人,再好的舞,再脱俗的曲子,哪里有自己项上人头重要?
于是下座的不明所以,尴尬的互推自家筹码。苍白无力的,试图唤起上座掌权者本能的欲望,好给自己牟利;
上座的人心惊胆战,或有胆大的,直接一错不错,盯着红衣小孩看,被凌昆叫去夜猎,不带一马一卒,可知凶多吉少。
或有胆小的,第一道敬酒共庆时就直直失禁在位子上,脸面丢尽,自己个儿投湖去了。
余下的,都是棋盘上固定的棋子,至于究竟是黑是白。
自是依靠生死来分。
凌司尘在叶芫落座一盏茶后才裹着纱布匆匆到来,落座是还极气愤地瞪了木白一眼,这才把心思放在宴上。
木白瞧见叶芫的疑惑,委屈巴巴地把裹满黑褐药膏的纱布自袖中扯出一截,再往自己脸上一指,任谁都能晓是凌司尘受伤不敷药,反把木白怪罪。
这才在帐中耽搁了时辰,白白让这宴席上背地动作不断的人慌张这些时候,可不是白白丢去了半条魂?
叶芫浅淡一笑,眉眼忽就璨然,看得宴席上人无一不暗叹其容貌只之惊艳。
叶芫本坐高台,这四下一扫,各眼中何中意思自是看得分明。却也不多理睬,只略略转头,向盘腿坐在侧后方的陌梅微微抬手,示意其可离去一叙。
本身就受了伤,更何况还满身是血的带伤回帐,怎得不让木白慌乱?
陌梅和木白得应允后,再不顾自家主子需要否。自己个儿跑到偏殿外的花园里嬉闹去,就着年纪来看,实在不像是半大的少年。
凌司尘瞧着木白扯着陌梅衣袖,俩人一前一后,一个步履如风,一个踉跄不止,头也不回地从侧门离开,心中烦躁更起。
“究竟谁是主子?”
凌司尘心里如是想到,一双丹凤眼却不由自主地,随着席上大众的视线一起转向一卷红毯对岸的红衣孩童。
恰巧,这视线就不期而遇的,交汇在席间纷杂烟火气间。
像春天时,波澜不惊的河流忽地解冻,哗啦啦就一片冰凌。冰凌在烟火气息处稍稍止息,又因人间温暖而化冻,在河流中互相碰撞。
奏乐一曲春,奇赏一番人间。
坚冰都能倚春息而化冰凌,更况这艳春的人和一颗凡人心?
凌司尘匆匆移开视线。
只觉心尖颤动不停,连带着呼吸都不稳,一抹抹绯红也悄然漫上脸颊,热得慌。
“这纱布未免缠的太多,怎就给人将心捂化了去?”
太热,太热。
凌司尘止不住扯松纱布的手,眼睛也似有外在丝线牵引,只寻那抹歌舞喧嚣中过分鲜艳的红。
哪知就双双移了眸,在一曲红尘里隔着舞女的纱衣花袖对上视线。
怎个惊喜?
叶芫本也只觉木白走的太过随意,想着这位的主子表情定然丰富。哪知这就撞上了视线,自己深习礼仪,自是知晓此举冒失。
谁知自己还未羞愧,对方倒先低了头。
这酒似乎是太烈,一杯就放倒了这胡乱跳脱的四殿下。
叶芫想着凌司尘过往跳脱行径,又瞧瞧那趴在桌上一动不动的人。
嘴角不免微微上扬,漆黑的眸中不免多了些荡漾的光彩,灿耀斑斓着,倒映着席上跳跃的光,迷了痴嗔人的眼。
桃花眸,微启春光潋滟。
朱丹唇,玉贝隐,字句珠玑。
坐错位置的人,笑盈盈说出祝酒词后,不知情的端举酒盏。
灯烛灿耀,芬香四溢,只见那玉人朱唇一抿,酒液晶莹滑入,随着酒液流入的,还有着贪痴着的欲念,无穷无尽。
一饮而尽地,不止于谷物酿造的浆液;
抬眼所见的,岂止故封在这皮囊之表?
杯酒进,续盏来,祝酒词顺先前意,真酒假酒何所辨。
只一个红衣美,杯杯醉,不堪计谋施;
只一个龙袍缚,帧帧明,难解小孩意。
酒本是特意选调好的,交由凌昆派人送入后厨每人专门的备餐处。大抵凌叔叔枕边风不打抵用,这些小仆役就被慕容丽清一一收买,偷摸运送情报了。
怎就偏偏漏了这一点?
叶芫在酒杯来来往往的影子里模糊了眼,眸中波光流转。
似溪流,似温酒,似柔波,在名为春的宴席里,向春而去,就好像一朵红灿灿的山茶花,非得要落下了,胜利或惨败了,才会在终局里隆重谢幕。
跌跌撞撞,叶芫着红衣走过舞池,走过帐帘,走过最后一点火光,入了寂静的、危机四伏的、月色流淌交织成雾的夜色里,再不见半点踪迹。
凌昆瞧着计划跑偏,心中焦急,面上八风不动。只轻转了转右手中指的墨玉扳指,荧荧幽光闪现,身边那个公公就被一暗卫极快地从帐中带走,酒醉的众人或清醒或迷离,只单单觉得自己脖子一凉,背后冰倚,手中酒杯莫名的沉重。
仔细看那舞娘的红裙,怎得就没了色彩?
是月色溪流里飘零的红,是暗处杀手无声息的击刺,还是那龙椅上的人手中被血浸透的扳指?
这宴席,终是让知情者再举不起杯,让攀权势者再不敢言。
营帐外,叶芫走在月色的河里,红衣倒显得凄凉起来,像个失去所有的、从墓地里掘土出现的未亡人,仓皇地、怯懦地想要逃离那荒诞的热闹。
凌司尘放心不下,匆匆告辞,也退出了这离了叶芫就索然无味的佳肴与歌舞。
行在月色下,那人的背影如此寂寥,是如何的岁月,酿造的这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