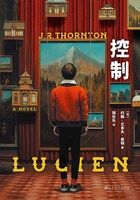
第2章
我的父母生于一个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国家。念大学时,他们相识于布拉格,坠入爱河短短数月便订了婚。当捷克斯洛伐克变成捷克与斯洛伐克时,他们已经远离故土,前往美国追求全新的人生,搬进了巴尔的摩我姑姑家的地下室。正是在这间地下室里,我降生到了人世。初抵美国的时候,我父母只会说寥寥几个英语单词。父亲持有捷克理工大学的机械工程高等学位,但没过多久他就发觉:从东欧获取的学历,其实在这个全新的国度派不上多大用场。他在一家影院里找到一份工,每逢电影收场,他就打扫爆米花和客人丢掉的杯子、糖果。母亲最开始在一家酒店当女佣,等到英语说得好些了,她就在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城一家捷克人开的咖啡馆里当女招待。我出生数月后,父母离开姑姑家,搬到同一条街上的一居室小公寓里。
我两岁时,父亲因胃癌过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模糊。我似乎确实能够回想起关于父亲的一幕场景,至少是一抹残影:那是一张匆匆闪过的面孔,胡子拉碴,在黑漆漆的屋里俯视着我。我说不清那到底是记忆中真实的一幕,还是我老早以前做的一个白日梦,越是琢磨,就越发笃信是后者——那是我的潜意识拼凑出的海市蜃楼,是老照片与想象力孕育而成的赝品。
当时,我并未发觉自家很穷,因为富人的世界并不在我的眼界之内,周遭所有人的境遇都跟我们家差不多。我穿的是二手的旧衣,鞋子从来没有超过两双。直到有人开始买我的画,又带我到宫殿般的豪宅中出席各种活动,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世人并不都像我们一家那样过活。
我母亲根本付不起日托中心和课后辅导的费用,因此不上学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待在她打工的咖啡馆里。也正是在那家咖啡馆,我与绘画结了缘——当我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幼童时,我就爱用蜡笔在菜单的背面乱涂。本来,这是我母亲的绝招,用来哄好既没有朋友又没有玩具的我。但没过多久,我便一头扎进了绘画之中,像一脚踏进了世外桃源。
回忆童年,我便只能记起这些,记起我埋头绘画的年年月月。小时候,我家有一盘名叫《毕加索之谜》的录像带,是一部一九五〇年代的法国纪录片,片中录有毕加索在某间画室现场作画的镜头。影片采用了定格摄影、特殊的用光方式和半透明纸张,因此观者可以见到那支笔,见到笔下的一划又一划神奇地出现在屏幕上。我听不懂那部纪录片的旁白,但我拜倒在屏幕画面之下。毕加索画的是一只只飞禽走兽、一张张滑稽的面孔、一个个奇异的怪物,让年少的我一见倾心。但这部纪录片让我如此钟情,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那些粗粗的黑色线条仿佛在自行现身,画面逐渐在观众的眼前展开。最开始像是一团纠缠的黑线和一抹色彩,眨眼间却变成了鸽子或公鸡。那部纪录片我恐怕看了上千次,每每盘腿坐在电视机前方,手里拿着蜡笔和一沓纸,一遍又一遍地照搬着我从电视屏幕上看见的图像。
世人总说,天才源于勤奋,对吧?换句话说,正是数千个小时的勤练与重复,才诞生了天才——我对此颇有异议。我向来笃信:勤练可以让人变得极为优秀,但单单只是勤练,永远不会诞生天才。要担得起“天才”的名号,还必须具备别的特质,某些天生之能,融入DNA的非凡才华。只要栽培得当,会使人具有惊世的能耐。当拥有卓越天赋的人发掘出自身的使命,真正的天才便会随之诞生。
我还不满八岁时,人们已经给我冠上了“神童”的称号。十岁那年,我在某次全市大赛中夺冠,评委是来自马里兰艺术学院的学界人士。获奖一事引起了好一番轰动,该比赛本来是为高中生举办的,但冲着奖金,母亲偏偏帮我投稿参了赛——两千美金的奖金,足以支付州内大学的学费。评审委员会发现我年龄不符后,投票取消了我的参赛资格,但其中一位评委——出生于牙买加的画家马库斯·鲍威尔随后跟我母亲取得了联络,表示评审委员会的决定让他很失望。他还对我母亲说,希望跟我见上一面。
马库斯·鲍威尔的工作室位于巴尔的摩皇家山火车站旧址,那是一栋花岗岩与石灰岩建筑,带有陶瓦铺就的屋顶和高达五十米的钟塔。我还记得,初见时我心里暗想,它看上去真像一座城堡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里兰艺术学院从“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手中买下了这座停用的火车站,改造成了艺术工作室。马库斯在大楼前台接到了我和母亲,一行三人朝拐角处的一家餐厅走。
等到点完餐,马库斯给了我一只大手提袋,袋上印有马里兰艺术学院的简称——MICA。手提袋非常沉,我忍不住朝里偷瞄。袋子里装着好些画笔、彩色铅笔、粉蜡笔、水彩颜料、素描速写本和一顶绣“MICA”字样的棒球帽。我抬头向马库斯望去,只觉得一头雾水。
“是给我的吗?”
“你赢了比赛,就该得奖,这才公平。”他说。
“噢,您真是个大好人。”我母亲说,“你该怎么回答人家呢,克里斯托弗?”
“谢谢!”
“大家一起来瞧瞧吧。”马库斯提议道。他伸手越过桌子,从手提袋里取出素描速写本和那罐彩色铅笔,又撕掉塑封,砰的一声打开彩色铅笔的包装罐。“我跟你妈妈先聊聊天,你不如拿这些去画几笔?”他说。
我一边把玩着刚刚到手的宝贝,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听他们聊天。马库斯有一肚子问题:问我母亲跟我住在哪儿,问我念的是哪所学校,问我是怎么学会画画的。我还听到马库斯问起父亲,而且他提及,他也自小丧父。
突然间,我发觉马库斯已经不再发问,他们两人都一声不吭。我抬起头,发现他们都在观察我画画。
“看来有人玩得很开心。”马库斯嘴里说着,伸手指了指我画中一个身负双翼的人物,“那是伊卡洛斯吗?”
“谁?”我问。
“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你知道伊卡洛斯是谁,对不对?”马库斯又问。
我摇摇头。
“伊卡洛斯飞得离太阳太近,太阳烤化了他背上的翅膀。”他解释道。
我听完不禁皱起了眉。“可是,翅膀怎么会被烤化呢?反正我画的只是个天使。”
马库斯哈哈大笑。“哈,一个天使,那是当然。”他说,“克里斯托弗,你愿意让我教你艺术课吗?不是那种枯燥的课,很有趣。刚才我跟你妈妈聊过了,我们一致认为,你可以趁周末到这里来学画画,你愿意吗?”
于是,我的学画生涯就此开启。随后五年,每逢星期日,我母亲便会在早晨七点半叫醒我,再把我送上12路公交车。那辆大巴经常迟到,冬季的清晨冷飕飕又阴沉沉,我坐公交车赶到霍华德街巴士站,马库斯会在车站等着接我。我们一起步行走过五个街区,走到马里兰艺术学院校内,余下一整天我都待在马库斯的画室里。他教我诸多绘画技法,比如光源与透视,比如如何排线、如何混色;他先教我水彩画,再教我油画——教我这么多,他却没有收一分钱。我母亲本打算尽我们所能付他一些费用,可他偏偏一分钱也不肯收。
我渐渐在马里兰艺术学院攒了点名气。马库斯麾下的一帮硕士生很宠我,我频繁出入马库斯的画室,技艺也飞速提升,让他们既惊艳又开心。其中几个拿我打趣,照着剧集《天才小医生》给我安上了“小天才”的绰号,不然就依着巴勃罗·毕加索的大名叫我“小巴勃罗”。于是风声不胫而走——马库斯·鲍威尔收了一个年纪轻轻的神童门徒。眨眼间我便成了各家媒体关注的宠儿。
我十二岁时,本地CBS电视网旗下媒体在晚间新闻时段播放了一则关于我的报道。这期节目被一名华盛顿艺术代理人看在眼里,打了个电话联络我母亲,问我是否已经雇了代理人。他先把我夸得天花乱坠,夸我多有才华,并夸口可以把我捧成“下一个毕加索”。他还声称,他手里握着一大把阔气的主顾,乐意豪掷千金买我的画。尽管马库斯给我们母子敲了警钟,声称这位艺术代理人名声不佳,母亲却还是答应雇他作代理人。
次年,我便接受了一大堆采访,动不动就上电视节目。那一年我画画并不多,但《华盛顿邮报》刊载了我的专题报道,我又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某期关于神童的特别节目里露了面。艺术代理人信誓旦旦地说,接下来就会让我上奥普拉[1]的节目。奥普拉的节目最终没有去成,但艺术代理人领我出席了他在乔治敦自家画廊里举办的盛大聚会,让我去社会名流和达官富豪面前亮相。芭芭拉·史翠珊和皮尔斯·布鲁斯南都买过我的画。
假如当初我的年纪再大上几岁,假如当初我母亲再精明几分,我们母子或许早就猜出艺术代理人在背地里狠宰了我们一刀。事实证明,我的画从他手里卖出去的价格远远超过他跟我们交代的价格。除此之外,他还瞎吹了一大堆开销、费用和税费,通通算到我们头上,常常要我们等上好几个月才能收到钱。当支票终于寄到手里时,钱款少得不可思议。代理人向我们保证,这情况再正常不过。等到母亲终于发觉他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已经来不及了。各大媒体对我的追捧已经烟消云散:日子一天天过去,每过一天,我便离童年又远了一步,世上又有谁会愿意掏钱买过气神童的一幅画?
等到读高中时,我的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是巴尔的摩艺术学校,要么是埃利科特城的森特尼尔高中。森特尼尔高中就在我住的城市,在马里兰州诸多高中里排名第二,不仅设有AP课程,还设了“资优班”。马库斯极力主张我去念森特尼尔高中,放弃巴尔的摩艺术学校,因为他自己念的就是艺术学校,他觉得我理应接受较广泛、较常规的教育。学校放学后,我依然可以跟他一对一学画嘛。马库斯声称,开阔视野乃是头等大事,若要当个伟大的艺术家,你必须熟知历史、哲学与文学。只懂画技,我只能原地踏步,伟大的艺术万万缺不得深邃的思考和对过往的洞见——正是这些,将意义赋予了艺术作品。
可惜,我跟森特尼尔高中格格不入,在校一直像是个局外人。倒并非因为我不愿意融入,只是实情使然。确实有过几个朋友,但既没有交情过硬的至交,也没有女友,身边连一个亲近的人也找不出来,而我无比渴盼深情厚谊。话说回来,世上又有谁不渴盼呢?
造成这种局面,多半是因为本校其他学生拿不准该怎么跟我相处。不少同学自小一起长大,要么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要么在同一个队里玩体育。谁知道,学校里居然冒出来一个来自市中心的家伙,有着诡异的口音和不凡的天赋。高中生中为人熟知的那些身份标签跟我都不搭:我不是戏剧迷,不是书呆子,也不是运动健将,更不是万人迷。我只是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便代表着孤独。
绘画,正是我的逃避之法。一拿起画笔,周遭万物便成了一片沉寂,我的眼前只有画布。正如你沉浸在拼图游戏中,某一个刹那,你的心中只在乎一件事:找到能够补全左上角的那片拼图。眨眼间,你的目标变得十分明晰,生活也顿时变得简单。画画的时候,我不孤独。我就是这样熬完了高中生涯。
过去,我还常常做些白日梦,想象着有朝一日,我的生活中充满艺术展与画廊开幕式,身边簇拥着诸多杰出人士,人人过着有趣而精致的人生。我想象着自己住在某处别致的宝地,比如纽约、芝加哥,甚至欧洲。我想象着自己重返森特尼尔高中的校友聚会,让当初的同学刮目相看——长大成人以后,他们想必会在没劲的地方过着没劲的人生,干着没劲的职业吧。我想象着逃离,想象着幸福的生活。
不过,我并没有具体方案,不如说,心里只有个泛泛的念头。我明白,我正沿着某条轨迹前行,此路的尽头是一片应许之地。至于细节,就交给马库斯吧,他清楚要抵达目的地,我该采取哪些步骤。马库斯才是掌舵的人——我对此没什么意见,因为终点处自有大好前途在等待着我。
可惜,即将读十一年级的那年夏天,一切突然变了样。当时马库斯领我出去吃了顿午餐,告诉我他在哈佛大学找了个职位,准备搬去波士顿。
回到家,我忍不住哭了一场。当时我还在用青春少年那自我的视角看世界,无法理解马库斯怎么能说走就走,转眼把我抛到脑后。那我们的宏图大志怎么办?就是为了马库斯,我才放弃了入读巴尔的摩艺术学校的机会。要是没人教我画画,我又怎么提高?假如我天赋不足,无法在艺术这一行取得成功呢?假如艺术之路走不通,我又该怎么办?我可从来没有考虑过别的出路。
马库斯向我保证,他去哈佛教书,是对我们两人都有益的一步。他拿到了哈佛大学一份为期一年的讲师合同,并有望晋升为助理教授,有望获得终身教职。身为教授,他可以为我入读哈佛出一份力,游说招生办公室,并联络艺术界各路朋友给我撰写推荐信。与此同时,马库斯对我还可以继续远程教学。
马库斯说,哈佛大学并不期盼学生全是成绩拔尖的优等生,也欢迎在体育、音乐和艺术等领域成就卓著的学生——而这条路,便是我迈向哈佛的直通车。假如想被录取,我和马库斯只需向哈佛招生办公室证明,我是本国同年龄段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
马库斯动身前往波士顿之前,他和我定下了一份为期两年的课程表,着重于古典技法的训练,其核心在于通过模仿进行学习。我将照着大师巨匠们的素描和油画进行仿画,将其技法烂熟于心,在潜移默化中吸取精髓。马库斯将会继续指导我,每隔几个星期查看一下我的进展。此外,就靠我自己用功了。
马库斯领着我从巴洛克时期的绘画大师学起,渐渐学到印象派。马库斯借给我艺术书籍和绘画作品集,书中尽是卡拉瓦乔、鲁本斯和委拉斯开兹等大师的素描与油画。我将这些作品集上的素描临摹了数百遍,直到能够感觉大师的手引领着我的手握住铅笔从纸上画过。在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我与扬·凡·戈因[2]及安东尼·凡·戴克[3]的画作一起消磨了一个又一个下午,我带着一本摊开的素描本坐在一幅幅杰作前,比如《雷那多和亚美达》。一心沉浸于大师画作中时,我感觉每一位大师仿佛在我心中变得无比鲜活:我熟知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怪癖,甚至想象得出他们的嗓音。
我埋头练习厚涂法,又尝试一幅画只用寥寥几种颜色,依靠对比效应营造色差感;我埋头钻研埃德加·德加与莫奈的画作,随后更进一步,学习点彩画派,照乔治·皮埃尔·秀拉的《马戏团》仿画了一幅与原作大小一致的版本。不过,我最心仪的还是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兰、劳尔·杜飞[4]、亨利·马蒂斯。我痴迷于该画派大胆的用色——一幅幅画作绽放着醒目的青、黄、紫,充满活力与动感。每逢面对野兽派的画作,一种自由感便扑面而来,真是无比有趣。
马库斯教了我一些窍门和技巧,等到踏进哈佛校门的时候,我的技艺已经颇为精湛,马库斯声称,若不是精于此道,只怕出自我手的仿画就会被当作真迹呢。
醉心临摹的日日夜夜中,我从未想过将这些技艺用到歪门邪道上。我哪里想得出这种主意呢?跟大多数情况一样,又是路西恩做的主。
注释
[1]奥普拉·温弗瑞(1954— ),美国主持人。她主持的《奥普拉秀》是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脱口秀节目。
[2]扬·凡·戈因(1596—1656),荷兰画家,擅长风景画。
[3]安乐尼·凡·戴克(1599—1641),比利时画家,巴洛克时期的佛兰德宫廷画家。
[4]劳尔·杜飞(1877—1953),法国野兽派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