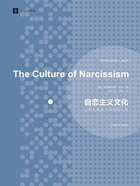
自白和反自白
自白风尚的盛行自然证实了贯串于整个美国文化的新自恋主义的存在;但用这种风格写出的最好作品却恰恰是通过自我表露来取得一种与自我之间的批判性的距离,并获得对以心理形式再现出来的历史力量的洞察。正是这种历史力量使自我这一概念越来越成为问题。写作这一活动本身就已决定作者与他的自我之间要保持一段距离,而正如对自恋主义所作的心理分析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个人个人体验的具体表现又使“存在于人们意识底层的喜欢夸大炫耀的特点——在经过一番适当的掩饰本意、驯服和中性化之后——有可能得到满足”。(11)然而,小说、新闻和自传诸文体间日益流行的互相渗透,不容置疑地表明许多作家已感到要保持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与自己的距离已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现在既不把个人材料小说化,也不把这些材料重新安排,而是喜欢按材料原来的样子不经消化加工就发表出来,让读者按自己的意思理解小说。许多作家现在已不再根据记忆写作,而是依赖自我表白来保持读者的兴趣。他们不是想让读者理解作品,而只是依赖于读者对著名人物私生活所怀有的不健康的好奇心。梅勒及其许多模仿者的作品开始时是对作者自己雄心的批判性的反映,并被毫不谦虚地宣布为不朽文学的一次尝试,而结果这些作品往往都以作者喋喋不休的独白而告终。这些作者就利用自己的声名,在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夹入了要不是因为出自一个响当当的名字的话就引不起任何注意的东西。一个作家一旦已处于令人瞩目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现成的市场兜售真正的自白。就这样,当埃里卡·荣格(Erica Jong)因为以一个男人才能有的冷漠写了性生活而大出其名后,她立即又推出了一部关于一位年轻女子的小说,致使那位女子也一下子成了文学上的名人。
即使是最好的自白作家也只是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沉溺之间徘徊。他们的作品——如梅勒的《为自我作广告》、诺尔曼·鲍德霍雷茨的《成功》、菲利浦·罗斯的《波特纳的不满》、保尔·茨威格的《三次旅行》和弗莱德里克·埃克斯雷的《一个球迷的笔记》——在经过痛苦锤炼后得来的个人启示与仅靠描写对作者本人有直接兴趣的东西来吸引读者的那种浮夸的自白之间摇摆。眼看就要获得真知灼见了,而这些作家却退回到自我戏弄般的模仿,企图先发制人地解除对他们的批评。他们试图用一些手段迷住读者,而不是靠他们杰出的叙述来赢得读者。他们运用幽默与其说是为了使自己与材料间隔开一定距离,还不如说是为了讨好自己并让读者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同时又不必严肃地对待自己及其作品。唐纳德·巴赛尔摩的许多小说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十分出色、感人至深,但因他动不动就对事情一笑了之而失去了许多光彩。如在《帕佩塔》中,他用嘲讽的笔触描写一对刚离异的夫妇,为消磨时间广泛社交,并追求虚假的自由“生活方式”。但结果他的嘲讽仅流于毫无意义的俏皮。
听完音乐会……她穿上小羊皮牛仔裤和一件用许多块色彩绚丽的围巾缝制成的衬衫,戴上木雕手镯,套上了“达塔格娜”出品的镶银线的斗篷。
帕佩塔记不清今年是哪年,去年又是哪年。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呢还是很久前就已发生?她遇到许多陌生人。“你是与众不同的,”帕佩塔对桑妮·玛琪说,“我所认识的女孩中,极少有人把福奇元帅的头像刺在背后的。”
伍迪·艾伦是一位对精神治疗的陈词滥调和因之而引起的自我关注进行讽刺性模仿的大师。然而他却常常因为沉湎于已经广泛成为美国人谈话风格的那种草率的、必不可少的、自我贬低的幽默,而染上了他正要嘲讽的同样毛病。当他嘲讽一个在《没有羽毛》——即没有希望——的世界里进行虚假反思的人时,因为滥用俏皮话以致减弱了本来应该有的讽刺意味。
天啊,我为何总是有内悯感?是不是因为我恨自己的父亲?也许是因为巴马牛肉那件事件。嗯,它在爸爸的皮夹里干什么来着?……他多惨啊!当我的第一个剧本在学园戏场上演时,那天夜里他是穿着燕尾服,头戴防毒气罩来看首场演出的。
究竟死亡有什么会让我如此烦躁不安?也许是因为时间。
看看我吧,他想。50岁,过了半个世纪。明年,我就该51了。然后就是52。用这样的推算方法,他可以推算出今后5年里他每年的岁数。
自白形式可以使像埃克斯雷和茨威格那样诚实的作家对我们时代的精神颓败作出令人心悸的描叙,但也可以使一个懒惰的作家沉溺于“大言不惭的自我表露”,这种表露与其说是自白倒不如说是掩饰。自恋主义者对自己的虚假认识往往通过心理分析的陈词滥调表现出来,并成了他用以逃避批评,拒不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种手段。丹·格林伯格在《得胜: 性体验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意识到这本书的男性沙文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可是,我能告诉你些什么呢?……我是说,我们过去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什么是新鲜的呢?我并不是要原谅这种态度,我不过是如实写出来罢了。”格林伯格在一处描述了他如何与一个因喝酒过多、神志不清因而无法自卫的女人做爱,然而他却在后一章对读者说,在他整个叙述中“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你现在觉得怎样?你高兴了吧?刚才与艾琳发生的那件纯属想象的事是不是太令人厌恶以至于你不想再把这本书读下去了?我猜你不会这么做,因为你显然已在读这一章了……
也许你觉得受骗了,也许你会开始想,假如在一个地方我对你说了假话,在别的地方我也会这么做。然而我还没有这么做过——本书的其他地方……是绝对真实的,信不信由你。
唐纳德·巴赛尔摩在《白雪公主》里也如法炮制,又一次用作者的臆造蒙蔽了读者。作者在该书中间部分放进了一张调查表,以征求读者对故事进展的意见,并提醒读者注意该故事与原来的童话故事的不同之处。当T·S·艾略特给《荒原》附上参考注释时,他成了提醒读者注意作者对现实富有想象的转化的最初几位诗人之一。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加深读者对这种引喻的意识,为了创造出一种更深沉的想象共鸣——而并非像这些近期作品一样去破坏读者对作者的信任。
不可靠的、半盲的故事叙述则是长期以来另一种流行的文学手段。然而,早先小说家们采用它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让叙述者对事物的不正确看法与作者自己更准确的观点之间的具有讽刺性的并存效果。而今天,在很多探寻性写作中,小说化的叙述者这一传统已被废弃。作者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但同时却提醒读者他的真理未必可信。库内特·冯内古特(12)在《猫的摇篮》一书的第一页就宣布:“本书通篇皆是假话。”这样作者使读者像注意一个表演者似的注意起他来,但同时他也就削弱了读者对他的信任。作者把真实与虚幻的界线搞模糊,要读者既不是因为作品是真实的、也不是因为作者声称他的作品是真实的,而仅仅是为了作者声称作品看来可能是真实的——至少部分是真实的——才相信他的作品。作者放弃了让读者认真对待的权利,同时他也逃避了被认真看待所带来的责任。他并不想求得读者理解,而只想得到读者的溺爱。读者一旦接受了作者对自己撒谎的自白,那他也就等于放弃了要作者为他作品的真实性负责的权利。就这样,作者不再努力使读者信服,而是努力设法迷住读者,企图依靠虚假的自我暴露所带来的刺激来保住读者的兴趣。
这种躲闪回避的状况使自白作品堕落成为反自白作品。对内心生活的记录成了漫不经心的对内心生活的滑稽模仿。这样一种貌似探索内心世界的文学体裁事实上恰恰向我们表明内心生活是最不必认真对待的。这又解释了艾伦、巴赛尔摩和其他一些讽刺作家为什么故意把滑稽的模仿作为一种文学策略,来频繁地嘲讽早年那些坚信自己的内心搏斗是大千世界一个缩影的艺术家们写作时所用的自白风格。今天艺术家们“自白”的唯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其平庸陈腐。伍迪·艾伦按照凡·高致其弟的书信写了一部讽刺性模仿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艺术家成了一名整天埋头于“口腔病预防法”,“齿髓管治疗法”和“正确刷牙法”之中的牙医。探索内心世界的历程最终发现的只是一片空白。作者再也看不到生活在自己意识中的反映。相反,他把世界,甚至包括世界的空虚,看作是自身的投影。在记录他的“内心”体验时,他并不力图对某一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情景作一客观记叙,而是诱使别人给他以注意、赞许及同情,并靠这些来勉强支撑他那摇摇欲坠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