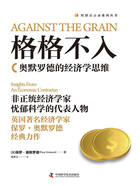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
与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被分成多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的领域非常简单。一篇学术论文或者演讲要么是关于“微观”经济学的,要么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
美国幽默作家派翠克·欧克鲁(P.J.O’Rourke)在他的《吃掉有钱人》[2](Eat the Rich)(O’Rourke,1998)一书中,相当简洁明了地抓住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媒体对宏观经济学十分关注。例如,明年的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会有多大幅度的增长?通货膨胀率会是多少?是否应该放弃紧缩政策?经济学家在这些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
但实际上,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微观层面上的。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它研究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个体如何在不同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在这一领域,无论是在大学、商业企业、金融市场还是在中央银行,专业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远大于分歧。
我对这两个领域的看法很容易概括。在我看来,过去的几十年里,微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宏观经济学就不一样了,它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经倒退了。
此外只有一个略显技术性的观点是合适的。上述几个段落提到了个体行为。这一理论不仅仅适用于人类个体。
经济学家经常提及“主体”而非“个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运用一种相当复杂的说法描述经济学家是一个单独的决策单位。所以,决策单位既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家公司、一个政府、一家中央银行、一个监管机构。
经济学家意识到,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实体。公司内部如何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一家公司的决策如何影响其他经济主体及其员工、股东和供应商等。换句话说,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些决策如何对公司的外部环境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做了一个简化的假设,把企业看作一个单一的决策单元,一个单一的主体。我们通常将研究公司内部如何做出决策留给其他学科。同样地,正如我们不关心个体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感兴趣的是经济环境下的决策对其他主体产生的影响。我们并非试图对所有的事情做出解释。
经济学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对许多经济和社会现象做出哪怕是片面的解释。
这可能是整个社会科学中唯一的普遍性规律:主体会对刺激的变化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如果主体所面对的刺激发生变化,主体的行为也可能发生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有关刺激的一个例子是司机在接近超速摄像机时的行为。即便是对经济学理论持最激烈批评态度的人也很有可能会放慢速度。司机可能一直在超速行驶,因为他认为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察发现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当司机发现有超速摄影机时,他认为被警察发现的可能性会急剧上升。司机面对的刺激已经改变,因此他的行为也随之改变。
以上是一个关于因为被罚款的可能性增加从而产生金钱刺激的例子。但在本书的许多文章中,我给出了非金钱刺激也可以对行为产生强大影响的例子。认为刺激只和价格有关是对经济学的一种讽刺。
与五十年前相比,微观经济学为刺激原则的运作方式提供了比流行的“理性经济人”观点更加丰富、更加现实的观点。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神秘的个体会坚决地收集大量信息,并以类似计算机的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之后,从旋转的大脑中蹦出对那个个体而且只对那个个体而言最好的决定。经济学对人性的残酷的描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微观经济学确实已经弱化了锋芒,现在在其理论模型中展现了一幅更加容易识别的人类画像。
我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政策制定领域极具影响力。主体绝对无法了解关于某一特定问题的全部信息,只能获得有限数量的信息。此外,一些主体可能比其他主体了解得更多。
这个概念是由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的。两位经济学家因开拓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相关的新闻稿报道说:
监管机构的大量工作都与试图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有关。经济学家喜欢使用夸张的短语,但这仅仅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同的主体可能拥有不同数量的信息。
继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他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3](Amos Tversky)于20世纪70年代的原创性成果之后,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行为经济学将理性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作为自己的参照点,并从这种行为中寻找经验偏差。泰勒(2015)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和成就做了出色的述评。
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像泰勒本人那样专注于行为经济学。自从泰勒在研究生阶段受到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早期成果的启发以来,他就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仍持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例如,如果观察到对于理性的偏离,这一偏离是否只局限于这一特定的情况?我们是否会在其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类似情况中也发现这样的偏差?另一个常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主体最终是否可以学会变得理性?我们可能会看到主体暂时偏离理性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体可能会纠正这一错误。
我在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学术期刊《经济事务》(Eco-nomic Affairs)上发表过一篇书评,其中包括我对行为经济学的优缺点的看法(奥默罗德,2016)。
除了这些成果之外,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分析包含个人信息和个人决策的大规模数据库的统计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和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可能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两位学者,他们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项研究的数学色彩过于浓厚,这里只对其成就给予肯定。它在许多本科和研究生经济学课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微观经济学向前发展了,那么宏观经济学就不能这样说了。从对经济周期、经济总产出波动的认识来看,宏观经济学在过去40年里强加给自己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宏观经济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微观经济理论初级模型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就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模型基础之上。这很讽刺,因为在同一时期,微观经济学在推动自身模型实现更现实的行为描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从数学角度来看,这些宏观模型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复杂,研究这些模型对于学者来说其纯粹学术吸引力显而易见。
但政策制定者往往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在经济危机期间担任欧洲中央银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长的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表示:
我的观点是,关于商业周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已经倒退了,这一观点反映在一些发表于《金融城早报》的文章中。我经常对宏观经济学的这一方面进行批判,因为它的失败预测,以及它没有将债务作为其模型的中心特征。
资本主义经济有两个特征,这两个特征使其不同于所有以前的以及现在实际存在的经济制度。其中一个特征是商业周期,即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持续波动。
第二个特征是经济随时间的推移呈现稳定而缓慢地增长这一事实,这在很多方面都是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通过采用这一经济制度实现产出和生活水平提高。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比1900年时要好很多。但当前十年政治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许多经济体在21世纪末的崩盘之后,增长不够迅速。
经济学并没有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市场均衡的理论,而增长必然涉及变化和毁灭。
从19世纪中叶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到20世纪中叶的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一系列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均以这种毁灭为主题。熊彼特创造了“创造性毁灭的飓风”这一短语来描述创新带来的毁灭性转变。
这些经济学家以及像凯恩斯和哈耶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描述性的。然而,现代经济学家已经热衷于建立形式模型。1956年,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建立了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索洛的模型中,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三样东西: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使用的资本数额以及索洛所说的“技术进步”,即创新的同义词。
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去做。从这当中得出的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是,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创新是该模型中未加解释的部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遗留问题”。因此,我在《金融城早报》的这些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创新的重要性。
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都面临着网络经济这一新的挑战。面对海量的选择,我们在互联网经济中究竟该何去何从?我们不可能处理所有的可触达的信息。例如,在我写到这里时,我在谷歌上搜索了“移动电话”这个词语。我得到了“大约155000000个结果”。1.55亿个网页!
我们无须抛弃理性选择模型,但是为了提升效率,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需要对这一模型加以修改。做出选择时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获取信息,而是我们应该丢弃甚至忽略哪些信息。
事实上,做到这一点的好方法是只考虑我们觉得可以信任的少数人所做的决定。其中包含的人会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我可能会因为餐馆评论认为某个网站的信息是可靠的,或者我的堂兄知道各家航空公司的优点。
这就引出了网络的重要性。我关注的人,我认为有用的网站,都是在特定环境中个人网络的一部分。就政治讨论而言,推特(Twitter)已经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回音室”。持相同观点的人会在推特上相互转发消息,却很少与持不同观点的人交流。
经济学家们终于开始意识到网络的潜在重要性。例如,中央银行对通过资产和负债模式将银行联系起来的网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一连串的失败可能会渗透到整个网络。顶尖的美国经济学会期刊《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在2014年的其中一期上刊登了关于网络的专题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