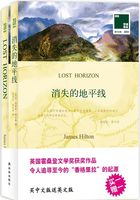
第1章 引子
雪茄烟即将燃尽,方才品尝到折磨我们的那种幻灭感:老同学长大后重逢时,发现彼此之间比想象中少了很多共鸣。卢瑟福在写小说,而怀兰成了大使馆的一位秘书。怀兰刚请我们在藤佩霍夫饭店吃了饭,席间,我感觉他兴致并不高,倒是始终带着一个外交官在类似场合总会持有的从容淡定。仿佛只是因为独身居住在一个异国的首都,我们这三个英国人才聚到了一起。同时,我感到,怀兰身上曾经那种隐隐的自命不凡经过这些年并未消失;我更喜欢卢瑟福,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不再是曾经那个皮包骨头的小男孩。想当年,他竟一边受我欺负一边又受我保护。看样子,他现在挣钱比我们俩都多,而且生活多姿多彩,这让怀兰和我有些妒忌。
不过那个晚上可不枯燥。我们坐在一起,观赏着汉莎航空公司从中欧各地而来的大型航班飞降机场的情景。傍晚将近,机场的弧光灯打开,一时间光彩辉煌,颇有一种戏剧效果。其中有一趟来自英国的航班,它的飞行员经过我们的桌子时,向怀兰打了个招呼。一开始怀兰没有认出他,待他想起这个人是谁后,便向我们做了介绍,并请他入座。这是个快乐风趣的青年,名叫桑德斯。怀兰向他道歉,说穿着飞行服又戴着头盔,实在让人很难辨认。桑德斯笑答:“哦,是啊,对这我再清楚不过,别忘了我以前在巴斯库尔待过。”怀兰也笑了笑,不过不太自然,我们后来便换了话题。
桑德斯的加入使我们这个小团体活跃了起来,大家一起喝了不少啤酒。大约十点钟,怀兰离席跟邻桌的人谈话去了,卢瑟福继续捡起刚才的话题:“喂,顺便问一下,你刚才提到巴斯库尔,我对这地方了解一点,你是不是想说那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桑德斯腼腆地笑了笑。“噢,不过是我在那里服兵役时经历过的一件令人激动的事罢了。”但是他毕竟年轻,还是忍不住说道,“是这样的,一个阿富汗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人,劫走了我们的一架飞机,接下来发生的事不难想象。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无耻的行径。那混账家伙拦住飞行员,一拳把他打昏,扒了飞行服穿上,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爬进了驾驶舱。他还给技师们发出了正确的信号,滑行,起飞,就这么大模大样飞走了,麻烦的是,他再也没有飞回来。”
卢瑟福看起来很感兴趣。“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嗯,怎么也得是一年前吧,也就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因为爆发了革命,我们正把平民从巴斯库尔疏散到白沙瓦,也许你还记得,那里当时局势混乱,否则也不会出这种事。可是,它确实发生了——某种程度上是这套飞行服让他得逞的,你说呢?”
卢瑟福仍然很有兴致。“可我以为,当时你们至少得有两个飞行员负责一架飞机吧。”
“没错,普通的军用机确实如此。可这架飞机有些特殊,是为一些印度邦主设计的一种小型飞机。后来,印度的勘探人员一度用它在克什米尔一带的高海拔地区搞勘测。”
“也就是说这飞机根本没有到过白沙瓦?”
“据我所知,没有。而且也没有在别的任何地方再降落过。这确实令人迷惑。当然,如果劫持飞机那家伙是那一带的土著,也许他把飞机开进了山里,把那些乘客当人质,勒索赎金。我估计他们都被撕了票。在前线很多边界地区,飞机坠毁了根本没人知道。”
“的确,我知道那种地方。飞机上有几个乘客?”
“我想有四个,三位男士和一位修女。”
“其中,有没有一位叫康维的男士?”
桑德斯很惊讶。“嘿,没错,确实如此。‘光荣的’康维——你认识他?”
“我曾和他在一个学校读书。”卢瑟福不大自然地说道。纵然事实如此,他还是觉得这么说有些勉强。
“以他在巴斯库尔所做的一切来看,确实是个讨人喜欢,很不错的小伙子。”桑德斯接着说。
卢瑟福点点头。“是的,这毫无疑问……可是,多么离奇……多么诡异……”他恍惚片刻,接着说道,“这事从没有在报纸上报道过,否则我早该有所耳闻。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时间桑德斯显得有些局促不安,我甚至觉得他有些愧疚。“老实说,”他答道,“有些东西我是不该说的,不过,也许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我是说这已经是陈年旧事,没多少人还在关心;后来事情也没有再张扬,我的意思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不太光彩。政府方面只是宣布有一架飞机失踪了,提到了飞机的机型名称,仅此而已,局外人对这种事不会有更多的兴趣。”
这时,怀兰又回到我们中间,桑德斯有些歉意地说:“我说,怀兰,他们几个刚才一直在谈论‘光荣的’康维,我恐怕把巴斯库尔的事说出去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怀兰一脸严肃,尽力克制自己,他不想当着同胞的面失态,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自己作为政府官员的形象。“我不得不说,”沉默了片刻,他慢条斯理地说,“把这事儿仅仅看做一桩奇闻逸事真让人遗憾。我原本一直相信你们这些空军弟兄不会这样不顾信誉,会把事情泄露出去。”对这个年轻人一番斥责之后,他又和蔼地转向卢瑟福,“当然,你的心情我理解,同时我相信你也明白,某些时候,有必要让前线地区发生的事儿保留点神秘色彩。”
“可是,”卢瑟福冷冷地说,“人们总会想去了解真相。”
“对于任何有必要知道真相的人,这事儿并未隐瞒。当时我就在白沙瓦,这点我可以保证。你和康维很熟吧?我是说,你们在学生时代就相识了吧?”
“在牛津大学时打过交道,那之后见面机会便少了。你常和他见面吧?”
“在安哥拉驻扎期间见过一两次面。”
“你喜欢他吗?”
“我认为他很聪明,但又有点懒散。”
卢瑟福笑道:“当然很聪明。他在大学里很出色,只可惜后来战争爆发了。他在学生会里可是个响当当的重量级人物,还是获得过蓝色荣誉的划船队员,各种奖励也得过不少。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棒的业余钢琴家,的确,一个了不起的全才,大家都觉得他会成为未来的总理候选人。不过,老实说,自牛津大学分别后,我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自然是战争中断了他的事业。当时他还很年轻,我猜他多半是从戎参战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伤了,要不就是出了别的什么事儿。”怀兰说道,“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混得很不错,在法国还获得了特等勋章,他后来回牛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员。我知道他一九二一年去了东方。他会几种东方语言,因而不费周折就找到了工作,此后还担任过几个不同的职务。”
卢瑟福爽朗地笑了。“这么说,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历史永远不会让世人了解那些破译情报密码工作中所取得的业绩,也不会透露公使馆里茶话会上的唇枪舌剑。”
“他是在领事馆,不是在外交部工作。”怀兰冷冷地指出。他显然无心打趣,而且,对于那些调侃的话,也没有发表任何异议。这时卢瑟福起身要走,他也并无挽留的意思。毕竟时间也不早了,我说我也要走了。告别时,怀兰仍旧彬彬有礼,高高在上,而桑德斯却很热诚地表示希望再见到我们。
我第二天天不亮就要去赶横贯大陆的火车离开。在等出租车时,卢瑟福问我可愿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打发这一小段时光。他说他的房间有个起居室,我们可以坐下聊聊。我欣然接受,于是他说:“好吧,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聊聊康维,除非你对他的事情没什么兴趣。”
我说尽管说不上了解他,但对他很感兴趣。“我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他就离开了学校。之前他确实很关照我。我是个新生,找不到理由对我那么好。虽然只是些平常小事,但我一直没忘记。”
卢瑟福表示同意:“没错,我也十分欣赏他,虽然长期以来我们鲜有见面机会。”
接着是一段令人难堪的沉默。很明显,我们都在回想一个对我们产生了很深影响的人,而这种影响又远非这种短暂邂逅的三言两语能够说透的。从那以后,我常常注意到,人们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场合,哪怕短短结识过康维,都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确实是个很出色的青年,而我是在崇拜偶像的年龄认识了他,自然对他的记忆更富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面目俊朗,作为一个运动健将,能轻易获得学校里的各种奖项。那位易动感情的校长曾用“光荣的”来赞扬他所取得的成绩,由此,他便得到“光荣的”这一雅号,恐怕也只有他这样的人才配得上这般称号。我记得他曾在毕业典礼上用希腊语发表演讲,还曾是校园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演员。他多才多艺,英俊潇洒,才智和力量的完美统一使他更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杰出人物,或者像菲利普·西德尼。当代文明却很少能造就出这般人才。
我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卢瑟福,他回答我说:“的确如此。人们常用‘半吊子’这个贬义词来形容那些博而不精的人,大概某些人,比如像怀兰这种人,会把它用在康维身上。我对怀兰这种人不太感兴趣,他的一本正经和自负让我无法容忍。不知你是否留意到,他功利心太强,他的那套什么‘人们终会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不会把事情泄露出去’,就像是皇帝驾临圣多美尼克教堂。我最看不起这类外交官。”
又是一阵沉默,车子穿过了几个街区。这时,他又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一晚没有白费。对我而言算是个特别的经历。桑德斯说的巴斯库尔的那事儿,我以前也曾耳闻,但没有太相信,以为不过是个离奇的惊险故事而已,无法让人绝对相信,或者说使人信服的理由只有那么一点。而现在,有了两个不起眼的理由说服我相信了。你能看出我并不是一个容易轻信的人。我走南闯北的生涯不短,我知道这世上无奇不有——要是亲眼所见,你绝不会怀疑。若只是道听途说,不会太过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到这些话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便笑了起来。“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不愿同怀兰推心置腹。那就像不愿给《逸闻》杂志推荐一部史诗一样。我更乐意跟你交交心。”
“你恐怕太抬举我了。”我说。
“你的书可没让我想到这点。”
我还没有提到过我那故弄玄虚的作家生涯(毕竟,精神病诊所并不是人人都能开的),却惊奇地发现卢瑟福居然对我有那么点了解。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了。卢瑟福说道:“没错,这也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康维曾经患有失忆症。”
到了酒店,他从服务台取来钥匙,到五楼时他说:“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可事实是康维并没有死——至少几个月前还没有。”
短暂上升的电梯似乎不是讨论这事的合适场所。于是一进走廊我便问他:“你肯定?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一边回答,一边打开了房间:“去年十一月我和他乘同一架日本客机从上海去檀香山旅行。”他说了一半便停下来,待到我们落座并倒上喝的,点上雪茄后才继续道:“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国旅行,四处游逛。当时同他已多年未见,也从未通过信。我并不常想起他,不过,只要有意识地在记忆中翻阅,他的形象总会很轻易地浮现。在汉口拜会了一个朋友之后,我便乘北平的快车返回了。火车上,我碰巧与法国慈善姐妹会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长聊了起来。她要去重庆,那儿有他们一个下属的修道院。我会两句法语,她便很高兴地同我谈起她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说实话,我对一般的教会机构没有多少兴趣,但同许多人一样,我能够接受他们,这些天主教徒自觉地站在了同一阶级的立场上,因为他们至少都在努力地工作,没有装腔作势地在普通人面前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顺便一提,这位院长在同我谈到重庆那所教会医院时,提到几星期前有个刚住进医院的伤寒病人,她们都认为他是欧洲人。病人没有说自己的情况,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穿的是本地的服装,而且是最穷的人穿的那种。修女护士们把他领进医院时,他病得很严重。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法语也十分不错,还有,这位院长向我保证说,在他认出修女们的国籍前曾用纯正的英语同她们交谈。我说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情形,我打趣地问她怎么能够判断一种她不懂的语言说得纯不纯正。我们就这些事情说笑了一番,最后她邀请我有机会到修道院去看看。当然,这就像要我去爬珠穆朗玛峰一样不可能。可是当火车到达重庆,同她道别时我却感到一种特别的遗憾,但一切到此为止了。巧的是,我在几个小时内又回到重庆。火车在离车站一两英里的地方出了故障,好不容易把我们又送回火车站,而我们了解到备用的发动机不可能让我们在十二小时内到达上海,中国铁路上的这种事儿倒不少。所以,只好在重庆逗留了半天——于是我决定去修道院拜访那位很不错的女士。
“没想到我去了之后,受到热情的接待。院长自然对我的到来感到有些惊讶。我想,对于一个非天主教徒,最难理解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够协调十足的刻板、严肃与一种随意宽舒的心境的矛盾。不过这无碍于那些修士修女们组成有趣的社团。待了没多久,我发现饭菜已经准备好,一个年轻的中国教会医生挨着我坐下。席间,他混着法语和英语同我谈笑,餐后又和那位女院长一起领着我参观了这所他们引以为豪的医院。我告诉他们我是个作家,而他们竟天真地认为我会把他们都写进书里去。我们顺着病床走过,那位医生一一向我介绍每个病例。医院非常干净,没有一点污痕,看来管理得很不错。我已经把那个说一口流利英语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方才想起来。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正在沉睡。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便问了声‘下午好’,但这并非我本来想要说的。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下午好’。的确如此,他的口音表明他是受过正统训练的。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认出了他——尽管他一脸胡须,容貌有了不少变化,而且已经那么久没有见过面。那是康维,我敢肯定是他。不过,假如我稍有犹豫,略有疏忽的话,说不定我倒会认定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当时我一时冲动,冒昧把他叫醒了。我喊他的名字,又报上我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盯着我,脸上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表情,但我已确信,我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奇怪地轻微抽搐了一下,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这情况,还有他那双眼睛一点也没变,当年我们常打趣说他的那双蓝眼睛比起‘牛津蓝’来更像‘剑桥蓝’。而除此之外,他还是那种不会轻易与别人混淆的人,那种让你一见如故的人。见此情景,医生和修道院长自然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他认不出我来可能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讶,但表示同意。之后我们一起就他的病情谈了很长时间。然而,他们实在无法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能来到重庆的。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两个多星期,希望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使他恢复记忆。但最终未能成功。不过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了,我们还聊了很多。
“当我如实告诉他,我和他各自的身份的时候,他很顺从,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隐隐约约表现出一种兴奋的表情,甚至似乎很高兴与我为伴。我提出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并不介意。这的确有些不正常,他很明显没有任何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离开。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一个密友,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确实,对我来说,为了康维,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让它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势必会引起拥堵,当然,我是指新闻报道的拥堵。
“我得说,我们是通过正规途径离开中国的。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而后乘火车到上海,当晚正好有一艘到旧金山的客轮,于是我们又急匆匆地上了船。”
“真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换了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的。”
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难以解释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同意道,“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回想起来就让人愉快,现在我仍然把他看做那个穿一身法兰绒的‘青年学生’。”
“真可惜,你没有在牛津认识他,他真是太了不起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了。然而,有人说,战后他变了,虽然我也有同感,可我又相信以他的天赋,他应该从事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在英王陛下手下做一个小职员,在我眼中并不算什么伟大事业,但康维确实很了不起,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我们都认识他,当我说我们不应忘却那段经历时,我认为我并没有夸大。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中部重逢时,虽然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之前的经历也迷雾重重,可他身上那种魅力非凡的特质却丝毫没有消失。”
卢瑟福沉浸在一种怀旧情绪中,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正如你想象的那样,我们在客轮上重拾起昔日的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听得很专注,那神态可以说有点可笑。来到重庆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他都清楚地记得。有趣的是,他并没有忘记他之前就会的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他相信自己与印度有某种联系,因为他会讲印度斯坦语。
“轮船在横滨上满了人,新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西夫金的钢琴家,他要到美国巡回演出,在这里换乘。他与我们同桌用餐,时不时用德语和康维交谈,可见往日的康维是多么外向而健谈;且不说他已经丧失了记忆,事实上,如果只是一般的社交接触,其实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离开日本已经数天,一晚,旅客们把西夫金请到甲板上举行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都前去欣赏。没什么好说的,他弹得十分精彩。弹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斯卡拉蒂的作品和许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维是如何聚精会神地欣赏着,那自然是因为他过去的音乐素养的缘故。到最后,音乐会在听众们的一次次返场的请求中继续着,钢琴家也欣然迎合,想必有些热情的乐迷甚至已经围拢到钢琴周围。他似乎特别钟爱肖邦,所以又弹了几首肖邦的作品。最后他离开钢琴,由一群崇拜者簇拥着向后门走去,显然他感到自己对这些乐迷已经够意思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康维径直走到钢琴前,坐下来弹起一段轻快的曲子。我没能听出这曲子是出自谁之手,不过它却吸引了西夫金,他激动地回到甲板,询问这是什么曲子,康维沉默了半天,样子十分古怪,然后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西夫金几乎叫了起来,他显得更加激动,说这简直难以置信。康维在那儿苦苦思索,最后说那是一首肖邦的练习曲。因为连我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当西夫金对此坚决否认时,我丝毫不感到意外。谁知,康维却突然怒不可遏,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到此为止,他还没有对任何事情表达过一丝情绪。‘亲爱的朋友,’西夫金辩解道,‘肖邦的所有作品我都了然于胸,我敢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很可能会写这样的曲子,因为这完全是他的风格,但他的确没有写过,你能给我看看这曲子的乐谱吗?任何版本都行。’康维严肃地回道:‘噢,是的,我想起来了,这曲子从没有发表过。因为我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从他那儿知道了这首曲子……我还会另一首没有发表过的曲子,也是从他那儿学来的。’”
卢瑟福一面用眼神暗示我别打断,一面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音乐爱好者,就算不是,我也敢说,你完全能想象出西夫金和我听到康维接下来弹的这首曲子时有多激动。我知道这是他过去的经历在现实中的一次突然又神秘的闪现,这也是找回他已丧失的东西的最佳途径。西夫金自然已完全沉浸到这个音乐问题中去了。实话说,这确实令人困惑,因为肖邦早在一八四九年就去世了。
“这一切如此蹊跷,让人难以置信。或许我还该顺便提一下,当时至少有十来人目睹了这一场面,其中有一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知名教授。当然,人们可以轻易地说从时间上来看,康维的解释根本就不可能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然而这曲子本身却让人无法解释。如果那两段音乐不是康维所说的两首肖邦的练习曲,那又是什么曲子呢?西夫金向我担保,说假如这两首曲子曾经发表出来,半年之内绝对会成为钢琴家们的保留曲目。这话听起来有些夸张,不过也表明了西夫金对这些曲子的看法。大家争论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而康维仍坚持他的说法。他开始显得有些疲倦,于是我马上带他离开了,让他躺下休息。最后,我们决定用留声机把这些曲子录下来。西夫金说他一到美国就会尽快安排好所有的一切。康维答应一起出席音乐会并登台演奏几首,可最终他没能信守诺言。我时常为此感到惋惜,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卢瑟福看看时间,对我说赶火车还早,而他的故事差不多快讲完了。“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就是钢琴独奏音乐会那晚——康维恢复了记忆。我们俩都上床休息了,可我却辗转难眠,而他来到我的舱室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紧绷着脸,不胜伤感,我只能这样描述,因为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悲伤,一种同普通人一样的哀伤,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那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没有任何特点,带着些许无奈,些许失意的表情。他说他什么都想起来了。正是在西夫金弹琴的时候,他开始回忆起一些东西,虽然只是些断断续续的片段。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我没有打搅他,让他慢慢回忆,然后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讲给我听。我说他能够恢复记忆,我非常高兴,但如果他本来就希望忘掉这些往事,我会很难过。他抬起了头,然后对我说了句我认为是很恭维我的话。‘谢天谢地,卢瑟福,’他说,‘你真是有想象力啊。’过了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让他也穿好衣服,随后相伴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个宁静的夜晚,满天星辰,而且很暖和,大海看上去一片苍白而显得黏滞,仿佛是凝结起来的牛奶。要是没有机器的轰鸣,我们简直就像在广场上漫步了。我任由康维继续自由地讲述他的故事,没有打断提问。黎明将近时,他开始不停地讲,滔滔不绝,等他讲完,已是早餐时间,太阳已经高照。我说他‘讲完’,并不是说他没有再告诉我更多的事。后来,有天夜里他还补充了一些很重要的信息。他心里很不舒坦,睡不着觉,于是差不多一直都在不停地讲。第二天半夜时,客轮按时到达旧金山,那一夜我们一直在客舱里喝酒畅谈。大约十点钟的时候,他出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的意思该不是……”我脑海里闪过一幅自杀的情景——一幅平静从容的自杀场面。那种场面我曾经在从圣卢岛到君王镇的邮轮上见到过。
卢瑟福大笑道:“噢,上帝,不是,他可不是那种人。他不过是趁我不备溜掉了而已,要上岸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若我派人去找,他一定会发现要逃避跟踪是很难的。当然,我的确也派人去找过他,可后来得知他千方百计登上了一艘向南航行到斐济运香蕉的货船,当了船工。”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再直接不过了,这是三个月后他从曼谷写信告诉我的,他还随信附了一张汇票,是为偿还我为他花费的一切。他在信里向我道了谢,并说他很好,正打算往西北方向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就这些。”
“他这是什么意思?”
“是呀,含糊其辞,可不是吗?要说曼谷的西北方向,地方可多了,柏林不也在曼谷的西北方向嘛。”
卢瑟福停了停,添满我的酒杯,给自己也满上。
“这故事相当离奇,要不就是他故意把故事讲得如此离奇,我无从知晓。那两首曲子的来历固然令人迷惑,可更让我不解的是康维是怎么到那家中国教会医院的。”我道出了我的想法。卢瑟福回答说:“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罢了。”“那他究竟是怎么跑到重庆来的呢?”我问道,“我想那晚在轮船上他一定告诉你了。”
“他确实跟我说了一些,可听起来很荒唐。跟你讲了这么多,剩下的我可要卖一下关子了。我只能说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在你去赶火车之前,恐怕连个大概都讲不清楚。不过,我这儿恰巧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我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并不太自信,可康维的故事确实让我深深沉醉,令我不由反复咀嚼,于是我着手把他在客轮上所谈的内容简略记录了下来,使我不至于忘掉那些细节,再后来,这个故事的几个地方开始占据了我的思维,一种创作冲动驱使我更进一步,把这些断断续续的片断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不是说我有所虚构或者篡改,因为他所讲述的内容当中已有足够多的素材。他讲话流利,而且颇有营造气氛的天赋,同时我感到自己已开始能够领会他的意思。”说着,他起身拿来一个公文包,取出一叠打印好的手稿,“给你,都在这儿了。我看,它们就任由你处置吧!”
“你是不是认为我不会相信这个故事?”
“噢,可别这么早下结论,不过请你记住,要是你果真相信了,那也是符合特图利尔的著名说法的——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天下没有不可能之事。但愿这辩证法不算太糟,总之,请告诉我你对于这一切的看法。”
我带上手稿,登上前往奥斯登的快车,在路上读完了大部分。我原本打算,等回到英国,要写封长信给卢瑟福,顺带把稿件寄还给他。但是这事被耽搁了几天,还没等我把信寄出去,卢瑟福却寄来一封短信,告诉我他又要去云游四海了,几个月内都不会有固定地址。他将要前往的是克什米尔,然后去“东方”。对此我倒是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