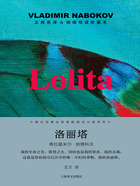
三、《洛丽塔》的巧妙手法
尽管,《洛丽塔》受到评论界很多认真的关注,但是小说所引发的批评,通常又一定会引出一篇与小说总体构思不协调而其实也不可能协调的论文。这复杂的构思——这个版本的注释部分有说明——使得《洛丽塔》成为这个世纪极有独创性的少数几部小说之一。很难想象,比如说,没有亨利·詹姆斯的叙述手法树立的榜样会有《吉姆爷》的创作,或者说,福克纳没有读过《尤利西斯》会把《喧哗与骚动》写成那样一部小说。然而,与《城堡》《追寻逝去的时光》《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微暗的火》一样,《洛丽塔》是想象所创造的、根本不在乎文学史家小心翼翼维持的整齐秩序的那些卓越的作品之一。极而言之,借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一句动人的话来说,它是那些创造了它们自己的先驱的作品之一。
因为纳博科夫不断地对“现实主义”和“印象派”小说的传统手法作诙谐的模仿,所以读者必须按照纳博科夫自己的主张或是接受他,或是拒绝他。如果依照任何其他主张来研究,他的许多小说将变得几乎毫无意义。然而,同时,即使纳博科夫的最热情的赞美者,有时候也一定对构成纳博科夫巧妙手法的细微、深奥的元素感到疑惑——五花八门的双关语、典故,以及在如《微暗的火》和《洛丽塔》这样的小说里俯拾皆是的蝴蝶联想。它们是有机的组成部分么?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图案么?亨伯特涉及面很广的文学典故岂止是“检验(我们的)学识”,正如亨·亨谈起奎尔蒂的类似做法的时候所说的。亨伯特的有几个典故如此精细地编织在叙述的花纹之中,除了非得寻根问底的注释者之外,谁都不会留意。然而许多出典是一目了然的,而且这些典故往往出自十九世纪的作家;一个及时的注释将表明这个典故是很重要的。但是,与典故不同——典故有时候仅仅是为逗趣——而文字之间的构成一定风格的相互参照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它构成了不被批评家所注意的小说的一个特色。
《洛丽塔》的修辞风格突出了小说的缠绕构思,并且确立了小说使用巧妙手法的基础。正如序文中所说,不打算在这里对《洛丽塔》作彻底的阐释。以下关于巧妙手法与游戏的评论也并非旨在表示小说的这一“层面”是最重要的;作这样的评论是因为至今还不曾有人认识到这一文字风格的重要性,或者它的意义(73)。正如纳博科夫的后记是在小说之前读的,因此,以下几页完全可以在查了注释之后重读,因为许多注释在这几页里已经提到了。
尽管与《微暗的火》相比,《洛丽塔》不是特别显著地表现出反现实主义的特点,但是这部小说别具一格,是既像那部较明显地多技巧的小说一样错综复杂,也像它一样是一部采用巧妙手法的作品。这一点并非即刻就看得分明,因为亨伯特是纳博科夫的自卢仁(1930)以来最“文明”的人物,同时,《洛丽塔》是三十年代早期以来“结局”保持完好无损的第一部小说。而且,纳博科夫曾说过,《魔法师》,即包含了《洛丽塔》中心思想的一九三九年那个短篇,之所以没有发表,并非因为题材的缘故,而是因为“小女孩不活。她几乎不说话。我是一点一点地让她有了一些现实的样子”。也许这似乎显得有些不正常,纳博科夫这样一个操纵木偶的人,又是《斩首之邀》和《庶出的标志》的虚假世界的创造者,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操心“现实”(无论是加引号的抑或不加引号的);然而,在纳博科夫身上一个极端并不排除另一个极端,而《洛丽塔》的独创性正是源于这一自相矛盾。木偶剧场从来没有倒塌过,但是在结构上处处都是裂纹,即使不说是裂口,它们犬牙交错,形式极为复杂,而目光深邃的人是不难看出的——即是说,受过纳博科夫小说训练从而习惯于小说错视画的人。《洛丽塔》是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同样,纳博科夫能很了不起地兼得正反两面,使读者一方面置身于既深深地打动人,又极其滑稽、逼真丰满的故事,另一方面又参与了一个游戏。这游戏之成为游戏是因为有交织的修辞变形,这样就破坏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使读者远离了小说的斑驳的表面,使这表面只留下一个棋盘的外表。
纳博科夫是一个讲课的教师,却有出色的表演才能,能以表演艺术家那样的技艺调动听课的人。他表演的果戈理临死时的痛苦,至今令人难忘:庸医们轮番替他放血、催泻,将他按在冰冷的浴缸里。果戈理孱弱得肚子上可以摸到脊椎骨。六条肥硕的白水蛭叮在他的鼻子上吸血。果戈理求他们把水蛭拿走——“求你们了,拿掉它们,拿掉它们,把它们拿掉!”——讲台此刻就成了浴缸,纳博科夫在讲台后身子慢慢地低下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就是果戈理,浑身哆嗦,两手被一个强壮的用人按着,仰着头,非常痛苦,非常害怕,鼻孔张大,两眼紧闭,哀求声传遍了整个大教室。甚至坐在教室最后面的一大批成绩勉强是C等的学生都不禁感动了。然后,稍作停顿之后,纳博科夫会轻轻地一字不差地说出他所写的《尼古拉·果戈理》中的一句话:“尽管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看到了令人气愤的人朝人恳求的场面,但是还是有必要再详细讲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里天才的那一面,即奇特地在肉体上体现的那一面。”
关于“靠不住的叙述者”已经写得很多,但是关于靠不住的读者却写得太少。虽然编辑小约翰·雷相当公正地告诫过那些“总希望追踪‘真实的’故事以外的‘真’人的命运”的“老派读者”,但实际上,纳博科夫似乎在构思《洛丽塔》“真实故事”中的每一“步”的时候心中都预想着这些读者的反应;而游戏因素就是依靠这样的自身反应行为,因为它在很多方面考验读者。亨伯特呼唤“读者!兄弟!”,他是在学《致读者》,即《恶之花》的序诗(“伪善的读者!——我的同伴——我的兄弟!”);确实,整部小说是在对波德莱尔(74)和其他许多谋求读者完全参与作品的作家作讽刺性的颠倒。“我希望有学识的读者都来参与我正准备搬演的这个场景。”亨伯特说。但是,这样的擅自参与会让读者老是处于受抑制的危险,甚至还会受到更粗暴的对待:“正如比我伟大的作家所说的那样:‘让读者去想象吧’,等等等等。转念一想,我还是让这类想象遭到意想不到的波折为好。”亨伯特直接招呼读者多达二十七次(75),诱使读者跌入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在纳博科夫的手中,小说于是就成了一个棋盘,在这个棋盘上,他采用诙谐模仿的手法,抨击读者的凭空臆断、狂妄自负,以及知识惯例,并通过游戏,实现并阐述他的相当于福楼拜要编一本Encyclopédie des idées reçues即一本《庸见词典》的梦想的翻版。
“讽刺作品是训诫,滑稽模仿是游戏。”纳博科夫说道;虽然《洛丽塔》的比较显而易见的妙语可以看作是讽刺性的(如:那些针对女校长普拉特的话),但是最有效的讽刺效果是通过诙谐模仿完成的游戏来实现的。纳博科夫创造了有着丰富的“心理”提示、但最终抗拒进而公开嘲笑深蕴心理学的分析的这么一个表层,从而能够打发掉“参与”构成小说前六十页左右的闪电战游戏的任何弗洛伊德信徒。设下的陷阱都有诱人的“引入歧途的嗅迹”,它们来自于纳博科夫《说吧,记忆》里所谓“性神话的警察国家”。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虚构的乱伦似乎暗示了一个经典的恋父情结,但是亨伯特后来把它叫作“乱伦滑稽模仿”。纳博科夫进一步暗示道,这个故事给出了一个“转移”理论,凭借这个理论,女儿将她的感情转移到另外一个相似的人身上,但这个人不是她的父亲,从而释放了她的恋父情结的紧张心理。倘若弗洛伊德的信徒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洛丽塔与奎尔蒂的私奔,那么,他们面对医院里的那一幕便要瞠目结舌了,因为当时亨伯特是这样说那个护士的:“我想玛丽准是以为滑稽有趣的父亲亨伯托尔狄教授正在干涉多洛蕾丝与她那位替代父亲、矮矮胖胖的罗密欧之间的恋情。”一个性感少女的男童性格特点诱使读者认为亨伯特的追求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性恋的,然而,当亨伯特说,在他的一次监禁期中,他如何开精神分析医生的玩笑,“用一些捏造的‘原始场景’戏弄他们”,以及“我贿赂了一个护士,看到一些病历档案,欣喜地发现卡上把我称作‘潜在的同性恋’和‘彻底阳痿’”(原书第36页)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依照通俗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做判断时就不会那样绝对了。倘若倾向于从医学角度看问题的读者接受亨伯特关于造成他的恋童癖的青春期“创伤”——不完全性交——的说明,那么,当洛丽塔必须在奎尔蒂的戏“自然高潮只有一星期就要到来时”离开它(原书第211页),他们应当会感觉到这打击多么有力以及他们自己的失落是怎样的形式。亨伯特的“创伤”还进一步给倾向于从医学角度看问题的读者设下了一个陷阱,因为这个事件似乎是纳博科夫自己天真得多的童年时代与柯莱特的恋情(《说吧,记忆》第七章)的一个诡秘的虚假的变形;而在那一章和《洛丽塔》里面都有的蝴蝶与《卡尔曼》典故的暗示,则加强了这种比较明显的相似之处。当那些受“精神分析行当的标准象征”滋养的认真的读者轻率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已有几个这样做了——并且立即得出结论说,《洛丽塔》确确实实是自传体小说,这个时候,陷阱已经起作用:他们这种随意简化的做法证明,这种纳博科夫式的诙谐模仿的确是必要的。纳博科夫以冷漠的文学执拗证明了他们的“真理”是虚假的;这里面的含义是相当深刻的。甚而至于,一个老练的读者试图通过揭示蝴蝶模式来寻找《洛丽塔》“意义”的注释工作也成了对于他的期望的嘲弄,因为他发现他是在追逐“正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象征的一个嘲弄性的逆向,这些象征,经确定之后,仍然可能是一个谜,说明不了什么,或者,像《微暗的火》口令高尔夫游戏一样,什么都没有说明。
直到《洛丽塔》几乎要结尾的时候为止,亨伯特“有罪”和“悲伤”的最充分的表达始终是受到限制的,如果说不是被完全破坏的话,而临近结尾的这些段落代表了另外一系列的陷阱,在这些陷阱里纳博科夫通过让忏悔者亨伯特说出读者想听的话,又一次嘲弄了读者的期望:“我是个五只脚的怪物,但我爱你。我卑鄙无耻,蛮横粗暴,十分奸邪,等等等等。”迫切地读着亨伯特的“忏悔”,读者突然间绊着了罕见的词儿“奸邪”,然后又猝不及防地遇上什么都可指的荒唐说法“等等等等”,这样一来,使整个这一连串话,如果说不是读者,显得很荒谬。忏悔是容易的,然而我们如果在忏悔时如此随便地使用关乎道德的词汇,那么,其含义就会跟亨伯特的滑稽模仿一样浅薄。
亨伯特自己的关乎道德的词汇似乎可以在克莱尔·奎尔蒂身上找到一种理想的表达媒介。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亨伯特一直都受到奎尔蒂的追踪,不管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比喻的意义上。奎尔蒂一会儿可笑又荒唐,一会儿阴险又古怪。有一阵子,亨伯特心中肯定,他的“影子”和复仇者是他的瑞士堂兄,特拉普侦探,而当洛丽塔对此表示赞同说“也许他就是特拉普”的时候,她是在总结奎尔蒂在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奎尔蒂无处不在,因为他编织了亨伯特的圈套,引发他的犯罪、他的羞耻感和对自己的恨。然而奎尔蒂象征的是“真理和对真理的讽刺”这两者,因为他既是亨伯特犯罪的形象体现,又是对于一个在心理上与亨伯特酷似的人的诙谐模仿;“洛丽塔玩的是两面游戏”,亨伯特这句话,一语双关,既指洛丽塔打网球是对酷似者的模仿,也指诙谐模仿作为游戏的作用。
酷似者主题在纳博科夫全部作品中有着显著地位,从三十年代早期的《绝望》和《黑暗中的笑声》(小说中欧比纳斯—雷克斯组合是在排练亨伯特—奎尔蒂对子),到《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直到《庶出的标志》、短篇《连体怪物的生活场景》、《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微暗的火》中的两个酷似者(说得确切一点,是三个酷似者)是绝妙的。这部书可能是所有酷似者小说中最复杂深刻的,它的创作正是在现代文学中关于酷似者的主题似乎都已经写完了的时候,而这一成功很可能是因为有纳博科夫在《洛丽塔》这部书中关于这一主题的不厌其详的模仿才能取得。《洛丽塔》中的这一模仿重新树立了他对于又一个文学手法的艺术功效的认识,一个“过去曾经是光彩照人的,但是现在已经磨损得丝丝缕缕的手法”(《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第91页)。
纳博科夫让克莱尔·奎尔蒂明显有罪(76),意在抨击酷似者的传统故事中所见善与恶“双重个性”的惯例。亨伯特也许会让我们一些人相信,他在第二部第三十五章杀死奎尔蒂,是诗人的善驱除了怪物的恶,然而两者最终还是不能明显地区分:亨伯特和奎尔蒂搏斗的时候,“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我们滚来滚去。”虽然这一诙谐模仿的高潮出现于这场“两个文人之间的一场默默无声、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但是它在小说中自始至终持续不断。在传统的描写酷似者的小说里,代表备受指责个性的酷似者往往被描写成一只猴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1871)中斯塔夫罗金对维尔霍文斯基说,“你是我的猴子”;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1886)中海德先生玩弄“猴子似的诡计”,怀着“猴子似的愤怒”和“猴子似的怨恨”攻击人和杀害人;坡的短篇《摩格街谋杀案》(1845)中的犯罪分子本身真的是一只猴子。但是“善良的”亨伯特破坏了这一对子,因为他常常说自己是猴子,而奎尔蒂不是猴子,而他们两人面对面的时候,奎尔蒂也说亨伯特是猴子。亨伯特说自己像“海德先生”一样,到处奔走,他的“手指还在作痛”。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1902)中,克尔兹是马洛的“影子”和“鬼魂”。虽然亨伯特把奎尔蒂叫作是他的“影子”,但是亨伯特的名字一语双关(亨伯即ombre,就是影子),说明他跟奎尔蒂一样,也是影子,而且他跟安徒生《影子》(1850)里追踪教授的影子化身一样,穿的是一身黑装。奎尔蒂其实最初认为亨伯特可能是他自己的“某个熟悉而无害的幻觉”;在小说即将收尾时伪装的叙述者招呼洛丽塔,并完成了这一转变:“不要可怜克·奎。上帝必须在他和亨·亨之间作出选择,上帝让亨·亨至少多活上两三个月,好让他使你活在后代人们的心里。”这部书原是可以由“克·奎”来叙述的,即把这一对子换个位置;“亨·亨”只是个比较好的艺术家,比较有可能会掌握“颜料持久的秘密”。
倘若说亨伯特—奎尔蒂对子是有意识诙谐地模仿《威廉·威尔逊》(1839),那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坡的这个短篇在描写酷似者的故事中是特别的,它与惯常的情形相反:弱与恶的化身倒是主要人物,受到善的化身的追踪,但善为恶所杀。而纳博科夫更是深入一步,以令人头昏目眩的气势颠倒了传统:依照十九世纪时候酷似者的故事,甚至消灭奎尔蒂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亨伯特在到奎尔蒂的帕沃尔府去之前,已经向洛丽塔求婚,而且他在叫不再是性感少女的洛丽塔与他一起走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他的迷恋。虽然亨伯特无条件地表达“有罪”是到小说结束时出现的,但是按照事态发展的先后,那也是在他杀奎尔蒂之前。作为一个“象征性”举动,杀人是没有理由的;诙谐模仿的构思至此已完成。
奎尔蒂对于他的象征角色表示迟疑是有道理的:“别人犯了强奸罪,我可不负责。真是荒唐!”他这样对亨伯特说,而他的话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在这一幕中亨伯特正是在试图要他负全部责任,亨伯特要奎尔蒂大声读的诗更加强调了他的图谋,同时又一次表明,纳博科夫的诙谐模仿如何突破风格模仿的“模糊乐趣”而与全书最严肃的部分相结合。这首诗以诙谐模仿艾略特的《圣灰星期三》(77)开始,但是以破坏“悔恨的”亨伯特一直在表示的全部忏悔告终:“因了你所做的一切/因了我没有做的一切/你非得死。”由于奎尔蒂被描写成是“美国的梅特林克”(78),不言而喻,随后发生的他死去的场面应该非常具有“象征性”。因为人是很难轻易摆脱“恶”的化身的,所以,像拉斯普京(79)一样不可一世的奎尔蒂几乎是不可能被杀死的;然而驱邪的概念因临死时的痛苦被滑稽地延长而变得荒唐。这是按照《夺发记》(80)第五章的精神,滑稽地模仿上自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下至最蹩脚的侦探小说的众多文学作品中描述死亡的场景里的血污和虚夸语言。奎尔蒂回到了犯罪的现场——一张床——而就是在这里亨伯特最后将他逼入死路。亨伯特近距离射出所剩几发子弹,奎尔蒂“向后倒了下去,嘴角旁出现一个具有幼稚涵义的大大的粉红色的气泡,变得像个玩具气球那么大,随后破灭”。这最后的细节描写强调了一种象征性的——但是滑稽地模仿象征手法的——与洛丽塔的联系;吞噬了洛丽塔、泡泡糖、童年等等一切的可怖的化身,已经“象征性地”死亡,然而,正如泡泡破了,哥特式酷似者这种类型小说的传统连同它的关于身份的“幼稚涵义”也都不见了,而我们很快便明白,亨伯特依然“浑身都沾满了奎尔蒂”。罪并不能如此轻易地可以驱除的——如果生造一个亨伯特惯用语来说,即麦克费特就是麦克费特——关于人的经验与个性特点的模糊性是不可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于“两重性特点”的。我们看到的并非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个性的成功结合,而是“隐蔽的克莱尔”与“包着的奎尔蒂”的拼接个性。奎尔蒂不肯死去,就像果戈理写酷似者的非凡故事《鼻子》(1836)里重新找回的鼻子起初不愿回到主人脸上一样。本来期待着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曼、或康拉德那一类描写酷似者的小说严肃伦理道德绝对准则的读者,此时相反倒发现自己漂流在荒诞滑稽、更接近于果戈理的体系里。我们希望亨伯特能制服他的“秘密分享者”,但后来我们倒发现,他追寻他的“抓不住的个性”,在比喻的意义上就像科沃寥夫少校在圣彼得堡幽灵般的大街上追寻他自己的鼻子,还发现亨伯特的“追寻”在一个最后的对抗中——这个对抗,好比《外套》(1842)的结尾,根本就不是一个对抗——有了它的虚假的“结局”。
纳博科夫有几次诙谐地提及罗·路·史蒂文森,这表明他心里想着亨利·杰基尔痛苦而认真地找到的“真理”,即“人不只是一个,而真的是两个。我说两个,因为我的认知状况不能超越那一点。在同样的思路上,别人将来会跟上来,别人将来会超过我”。《微暗的火》中的“系列个性”“超过”了史蒂文森和其他许多作家,而《洛丽塔》中在酷似者这方面的诙谐模仿非但没有减轻亨伯特的罪,这一手法反而将亨伯特锁进了一座镜子监狱,在这座监狱里“真正的个性”和它的伪装相互混合,从而使善与恶的折射线极其混乱。
亨伯特寻找特拉普侦探(奎尔蒂)的下落以及他的身份,引起读者的好奇,在纷繁的线索中探寻,以便解开谜团;这是一个既与坡的“推理故事”相似,又诙谐地模仿它的过程。亨伯特找到洛丽塔并逼她说出绑架她的人的名字,
她说这实在没什么用处,她决不会说的,不过另一方面,毕竟——“你真的想要知道他是谁吗?好吧,就是——”
她耸起两根细细的眉毛,噘起焦干的嘴唇,柔和地、机密地、带着几分嘲弄、多少有点难以取悦但仍不无温情地用一种低低的吹口哨的声音说出了机敏的读者早就猜到的那个名字。
防水的。为什么我的脑海中蓦地掠过沙漏湖上那一瞬间的情景?我,同样早就知道了这桩事,却始终没意识到。既不震惊,也不诧异。悄悄发生了交融汇合,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成为贯穿在整个这本回忆录中的枝条图案,我编织这幅图案的目的就是让成熟的果子在适当的时候坠落下来;是的,就是怀着这种特定的、有悖常情的目的:即使你获得——她仍在说着,而我却坐在那儿,消融在美好无比的宁静之中——通过合乎逻辑的认识所带来的满足(对我最有敌意的读者如今也应该体会到这一点)使你获得那种美好无比的绝对的宁静。
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亨伯特还是不肯说出奎尔蒂的身份,尽管“机敏的读者”可能已经认识到“防水的”是一个线索,它把我们带回先前湖边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里夏洛特说亨伯特的手表是防水的,而琼·法洛则提到奎尔蒂的艾弗舅舅(只说名,没说姓),后来还差一点指名道姓说出克莱尔·奎尔蒂:艾弗“对我说了他侄儿的一个完全猥亵的事情。看来——”但是她的话被打断,那一章就这样结束了。这种吊人胃口的推理手法——确实“宁静”!——是侦探圈套,是对读者的假设与期望的又一个嘲弄,仿佛最机敏的读者还是能够完全确定奎尔蒂或亨伯特或他自己的身份。
有了奎尔蒂的名字之后,亨伯特现在动身前往那座可以称之为“最后审判日的阿什尔庄园(81)”的帕沃尔府,那里有着对于坡的广泛而丰富多彩的诙谐模仿。小说全部的诙谐模仿主题都集中在这一章了。亨伯特的结论浓缩地道出了这一章的重要性:“我肚里暗自说道,这就是奎尔蒂为我上演的这出匠心独运的戏剧的结局。”在形式上,当然,这个高难度的华美片断不是一个戏;然而,作为对于主要情节的带滑稽模仿性质的总结性评价,它的确有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戏中戏的作用,而且,它的“上演”又一次强调了对于全书至关重要的游戏因素。
与这些游戏并行的有一个完全属于小说性质的展开过程,它显示了亨伯特所经历的远远超出了他和洛丽塔实际跋涉的两万七千英里。愚蠢的小约翰·雷把亨伯特的故事说成是“这个悲剧故事坚定不移的倾向不是别的,正是尊崇道德”,而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话居然是正确的。读者看到亨伯特从他的苦恋中解脱出来,做了一个并非完全直截了当的纯真爱情的表白,并最终认识到,遭受损失的不是他而是洛丽塔。这是在倒数第二页一段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的话里表达的;这一段话没有被诙谐模仿所破坏,也没有带上讽刺意味,这种情况在这部小说里是第一次。这段“最后一个奇怪的令人绝望的幻景”刚读到一半,读者又一次被呼唤,因为,亨伯特如此独特地易懂的道德最高境界,构成了这盘棋的残局和纳博科夫的最后一幅错视画。倘若读者早就断定小说中没有“道德现实”并且颇为老练地认可这一说法,那么,他就完全有可能忽略棋盘最远处的角落里这意想不到的一步棋,从而输了全局。这是作者最后一次直接对读者说话,因为小说要结束了,这盘棋也要结束了。
除了起到保持棋局要素这一作用之外,作者参与模式还提醒我们,《洛丽塔》只不过是排列在纳博科夫意识周围的那个小说世界的一部分,而纳博科夫不时地会跟亨伯特一样,悲叹文字其实很有其局限性,悲叹“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要想活在过去里,像亨伯特试图的那样,即是死亡。《说吧,记忆》的作者居然暗示了这一点,那就毫无疑问确定了洛丽塔的道德特性;同时,按照约翰·辉辛格所言“游戏是不受善恶限制的”(82)的观点来看,《洛丽塔》就是一个更加异乎寻常的成功了。
在《天赋》中关于费奥多尔的诗纳博科夫写道,“同时他得尽力保持自己对游戏的控制,或是观察玩物的角度”,纳博科夫这是在定义他写作小说时所面对的难题——充分理解这些小说的意义有赖于读者对该书所持有的立体看法。至此,诙谐模仿和作者参与模式是如何创造了看清“玩物”所必需的距离的,应该是显而易见了,而纳博科夫强化人们的“小说作为棋盘”意识,是通过确实在《洛丽塔》中安排了一盘进行中的棋局:亨伯特与加斯东·戈丹之间一场表面看来持续不断的对弈——一个处于前景位置、具有故事发生地点地方色彩的情节,而它反过来又浓缩了亨伯特—奎尔蒂“酷似者游戏”在“美国”这个棋盘上一来一去的过招,也浓缩了超然小说之外、具有压倒一切之重要性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竞赛。(83)
亨伯特与加斯东在亨伯特的书房“每个星期总下两三次国际象棋”,而纳博科夫好几次仔细地将洛丽塔与他们棋局中的后相联系。一天晚上他们在下棋时,洛丽塔的音乐老师打来电话对亨伯特说,洛丽塔又逃课了;这是亨伯特抓住的她的一次最明目张胆的撒谎,这暗示了他不久以后将失去她:
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的才智所受到的影响,又走到了一两步棋,轮到加斯东走的时候,我透过满心忧伤的轻烟薄雾发现他可以把我的王后吃掉;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认为这可能是他的狡猾的对手所设下的圈套,他迟疑了好半响,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摇了摇下巴,甚至偷偷地朝我瞅了几眼,把又短又粗、簇在一起的手指踌躇地微微向前伸了一伸——渴望吃掉那个甘甜肥美的王后,却又不敢下手——突然他朝它猛扑过去(谁知道这是否使他学会了往后的一些鲁莽行为?),于是我心情阴郁地花了一个小时才和他下成平局。
所有的参与者都想捉住“那个甘甜肥美的王后”,情况各不相同:可怜的同性恋者加斯东,完全是在下棋的意义上;色狼奎尔蒂只有一个目的;性变态者兼诗人亨伯特,以两种方式出于爱,首先是肉体上的,但然后又是艺术上的;而普通的读者,他会通过评判和谴责亨伯特来解救洛丽塔,或者会想象自己是洛丽塔参与故事从而站到了奎尔蒂一方——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仔细的读者迟早会同意亨伯特的观点:“在和加斯东下棋的时候,我把棋盘看作一个四四方方的清澈的池塘,在有着方格花纹的光滑的池底可以看见一些粉红色的、罕见的贝壳和珍宝。而这些在我那慌乱的对手眼中,都是淤泥和枪乌贼分泌的黑色液体。”
《洛丽塔》一开头,亨伯特说“这只是一场游戏”,当时他是过于谦虚了,因为,诚如纳博科夫在《防守》中对卢仁与图拉提之间的对垒所作的评价,这场游戏的棋盘上的一切都“透出生命”。当读者轮番地在面对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和面对一盘棋的一个个棋子这两者之间摇摆——仿佛望远镜在底座的轴上三百六十度旋转,让人们轮换着分别从两端观察——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就产生了急剧而令人头昏目眩的焦点的转移。《洛丽塔》的各不相同的“层面”毫无疑问不是新批评论(84)的“意义层面”,因为对于“所玩之物”的浓缩、全面的看法应该能使人即时地看清这些层面或方面——倘若自由地改写玛丽·麦卡锡用以描述《微暗的火》的一个比喻来加以形容,那就仿佛是从上面朝下观看两个象棋大师在置放在上下不同层面的几个玻璃棋盘上,同时进行三盘或三盘以上的对弈。(85)第一次读《洛丽塔》很难会给你这样清晰的、多种形式的审视,而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小说的表面主题在起初的时候那种吸引人注意力、让人觉得容易接受的特性会是最突出的。但是抛却先入为主的想法之后重读这部小说所得到的令人振奋的体验,产生于发现它是一本全新的书而非原先的书之后,产生于明白了该书的变形特性巧妙地描绘了人们自己的认识过程之后。博尔赫斯对于那部《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说的话显然也适用于《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通过一种新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86)。
小阿尔弗莱德·阿佩尔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加利福尼亚,帕罗阿尔托
(金绍禹 译)
(1) 纳博科夫这部用英语写的小说发表于1941年。它以文学传记的面貌出现,声称是一位已故作家塞巴斯蒂安·奈特的传记,是由这位了不起的作家的同父异母兄弟V所撰写,其实纯属虚构。
(2) spontaneous generation,一种认为动植物起源于无生命有机物的过时概念。这里显然是用作比喻。
(3) 约翰·厄普代克:《一代大师纳博科夫》,载《新共和》卷151(1964年9月26日)15期。收厄普代克《散文杂编》(纽约版,1965)中。——原注
(4) F.R.Leavis(1895—1978),英国文艺评论家,他最著名的著作《伟大的传统》(1948)追寻奥斯汀、乔治·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等作家现实主义传统。
(5) Law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小说家,他的《项狄传》写法怪诞,被认为是小说意识流手法的先驱。
(6) E.H.Gombrich(1909—2001),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艺术与错觉》(1956)论述艺术的性质与批评家的任务。
(7) 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1),法国诗人,象征派代表。
(8) John Barth(1930— ),美国作家,小说讽刺幽默,富有哲理。《迷失在开心馆中》包括十四篇故事,部分相连,涉及作者(人物之一)与读者间的互动。
(9) Raymond Queneau(1903—1976),法国作家,二十年代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作品有黑色幽默倾向。
(10) 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儿童文学作家。
(11) Samuel Beckett(1906—1989),爱尔兰戏剧家、小说家,荒诞派戏剧主要代表之一。
(12) 雷蒙·格诺:《障碍》,巴黎,1933年版,第294页。——原注
(13) Alain Robbe-Grillet(1922—2008),法国小说家。
(14) 雷蒙·格诺:《障碍》,巴黎,1933年版,第294页。——原注
(15)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纽约,1961年版),第567页。——原注
(16) 同上,第769页。——原注
(17) 同上,第513页。——原注
(18) 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
(19) 豪·路·博尔赫斯:《吉诃德的部分魔术》,收入《迷宫》(纽约,1964),第196页。——原注
(20) Proteus,希腊神话中的小海神,能预言,善变,好回避问题。
(21) Saul Steinberg(1914—1999),美国漫画家,在《纽约客》周刊连载漫画出名。他的画以几何图形、数字、符号、动物形象等表示幽默讽刺的意义。
(22) 参看纳博科夫的文章《〈洛丽塔〉与吉罗迪亚先生》,《常青评论》第11卷(1967年2月号),第37—41页。——原注
(23) Jean Genet(1910 —1986),法国小说家、诗人、荒诞派剧作家。作品有小说《鲜花圣母》(1944)、自传《小偷日记》(1949)等。
(24) 《包法利夫人》是法国十九世纪作家福楼拜的代表作,英译Madame Bovary,去掉字母B的ovary意为“卵巢”。
(25) Instant Pornography Test(快速色情读物测试法)的首字母缩写形式。
(26) Graham Greene(1904 —1991),英国小说家。
(27) Albion,古希腊罗马人对不列颠或英格兰的称呼。
(28) 纳博科夫在四年之后采用乔伊斯的类似方法,回敬了普雷斯科特,尽管没有点名,即让杀手格拉杜斯仔仔细细读《纽约时报》:“一个专门评论旅游新书的雇佣文人,在评论他本人挪威之行时说,挪威峡湾太出名了,根本用不着(他)再多费唇舌加以描述,还说斯堪的纳维亚人都爱花儿。”(《微暗的火》第275页)这是真的从这家报纸上选来的。——原注
(29) Herman Melville(1819 —1891),美国小说家,他多部小说以捕鲸船上的经历为题材,代表作为《白鲸》(1851)。
(30) 安德鲁·费尔德在《纳博科夫:他的艺术生涯》(波士顿,1967)第325页,以及卡尔·R.普罗菲在《洛丽塔解锁》(布鲁明顿,1968)第3页,都指出这一段。——原注
(31) 安德鲁·费尔德在《纳博科夫:他的艺术生涯》(波士顿,1967)第328—329页引用了。——原注
(32) 安德鲁·费尔德指出,人们应该记得这个故事原是要让俄国流亡者群阅读的。强烈的性爱(与色情相对立的)主题,俄国作家严肃地采用得相当频繁,远远超过他们的英国和美国同行。费尔德列举的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被禁的那一章),列斯科夫,索洛古勃,库兹明,罗扎诺夫,库普林,皮利尼亚克,巴别尔,以及蒲宁。费尔德还归纳了纳博科夫早年创作、没有翻译的写性主题的两个短篇《童话》(1926)和《敢闯的人》(1936年前后)的故事情节。——原注
(33) 具体地谈到《洛丽塔》的写作的时候,他说:“她就像创作一个绝妙的谜——谜的创作,同时又是谜的破解,因为一个与另一个是极相似的,依你所观察的方向而定。”——原注
(34) 潘尼罗普·吉列特:《纳博科夫》,《时尚》第2170期(1966年12月),第280页。——原注
(35) 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
(36) 潘尼罗普·吉列特:《纳博科夫》,《时尚》第2170期(1966年12月),第280页。——原注
(37) Anthony Burgess(1917—1993),英国小说家、批评家,代表作有《发条橙》(1962),对少年犯罪、暴力、高科技提出引起恐慌的、未来主义的观点。
(38) 安东尼·伯吉斯:《诗人与学究》,载1967年3月24日《旁观者》,第336页。《紧要印件》(纽约,1969)重印。——原注
(39) Lenny Bruce(1925—1966),美国喜剧演员,死于一次意外的用药过量。
(40) 这两幅画的照片载于1969年5月23日《时代》周刊第83页。——原注
(41) 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
(42) 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他的作品及简练奥秘的风格对象征主义运动产生很大影响。
(43) Alexandra Alexandrovich Blok(1880 —1921),俄国诗人,他的早期创作承袭象征主义,1905年革命后倾向现实主义。
(44) 红花侠是英国女作家奥切(Emmuska Orczy,1865—1947)的成名作长篇小说《红花侠》(1905)中的主人公的别名。
(45) 弗格系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 —1905)《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主人公。
(46) 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 —1936),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
(47) 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十四行诗组诗《一九一四年及其他诗篇》是他的代表作。
(48) Father Divine(1882—1965),非洲裔美国宗教领袖,1919年发起“和平使命”运动(the Peace Mission movement),有大量追随者,被许多教徒尊崇为心目中的救世主耶稣。
(49) Trieste,意大利东北港口城市。
(50) Robert Burton(1577—1640),英国圣公会牧师、学者、作家。他以《忧郁的剖析》(1621)一书闻名于世。虽非医学著作,作者也未能给忧郁症下明确定义,但为忧郁症开药方,其一云:“勿离群,勿懒散。”颇有意思。作者旁征博引,书中警句俯拾皆是。
(51) Samuel Johnson(1709 —1784),英国大文豪,第一部英语辞典(1755)的编纂者。辞典例句丰富多彩,释义有趣。
(52) 即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1494—1553)长篇讽刺小说,中译本作《巨人传》。高康大食量酒量大,脾气好,庞大固埃性格粗野,爱戏谑。
(53) Harold Lloyd(1893—1971),美国喜剧电影演员,演过无声电影《大学新生》《最后安全》等,获1953年奥斯卡荣誉奖。
(54) 虽然《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在1941年即纳博科夫来美国一年以后出版于纽约,但实际上是在1938年(用英语)创作于巴黎。编写年表的研究者也应注意,《洛丽塔》作于《普宁》(1957)之前。《洛丽塔》在美国的出版日期(1958)让人误解。
(55) 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流亡美国,主要作品有《西线无故事》(英译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等。
(56) 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1905—1984),苏联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英译All Quiet Flows the Don)。
(57) 抑扬格指的是英文诗歌一轻一重两个音节组成的音步,译文自然是另一种情形,故抄录英文原文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A curious sight - these bashful bears,
These timid warrior whalemen
And now the time of tide has come;
The ship casts off her cables
It is not shown on any map;
True places never are
This lovely light,it lights not me;
All loveliness is anguish—
(58)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流行于美国报纸上的连环漫画故事。迪克·特雷西即是故事主人公,一个有天分、有正义感的侦探。
(59) Terry Southern(1924—1995),美国作家,以写电影剧本为主。他的作品典型地反映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青年人的精神状态。
(60) “马·梯尔登”的原文是Ma Tilden,将字母顺序倒过来就成了所谓“回文词”Ned Litam,中译即“内德·里坦”。
(61) 这是把俄文单词пошлoсть(意为“庸俗”“低级趣味”“令人生厌”等)按发音用英文字母进行拼写。
(62) Tristram,英国亚瑟王传奇中著名的圆桌骑士之一,因误食爱情药与康沃尔国王马克之妻绮瑟相恋。
(63) 原文中,“报答”是repaid,而“尿布”是diaper,即把六个字母顺序颠倒排列。纳博科夫喜欢用这种“回文构词法”制造诙谐效果。
(64) Vladimir Fedorovsky Odoevsky(1803—1869),俄国公爵,作家、音乐评论家,著有短篇小说和哲学谈话集《俄罗斯之夜》(1844),以及浪漫主义和哲学幻想性质的中篇小说。
(65) Ducan Hines(1880 —1959),美国美食家和出版商,曾广泛游历全美各地,记录并点评沿途各家旅馆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出版旅游指南性质的书籍。
(66) 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散文家、批评家,美学运动的主要人物,但人们一般记得他著有长篇小说《朱莱卡·多勃生》。在小说《圣诞花环》(1912)一书中,作者技法娴熟地模仿亨利·詹姆斯、威尔斯、吉卜林以及其他当代重要作家的文学风格。
(67) 库克罗普斯(Cyclops)和瑙希凯厄(Nausicaa)均为《奥德赛》中人物。
(68) Marianne Moore(1887—1972),美国现代主义诗人,对动物尤感兴趣;诗行不以音韵衡量而以音节数计,一反传统。
(69) 录自注释者1953—1954年课堂笔记。——原注
(70) 弗拉基斯拉夫·霍达谢维奇:《谈谈西林》(1937),迈克尔·H.华克译,西门·卡林斯基和罗伯特·P.休斯编,《三季刊》,第17期(1970年冬)。——原注
(71) Claude Mauriac(1914—1996),法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先锋派新小说理论家。
(72) Federico Fellini(1920 —1993),意大利电影导演。
(73) 笔者曾另文讨论过这部小说,把它看作一部小说以及看作一种巧妙手法;参看拙作《〈洛丽塔〉:诙谐模仿的跳板》,见《威斯康星当代文学研究》卷Ⅷ(1967年春),第204—241页。重印于L.S.邓博编:《纳博科夫其人及其著作》(麦迪逊,1967),第106—143页,其中125—131页、139—141页尤为重要。——原注
(74)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主要作品有《恶之花》。
(75) 这些还不算亨伯特对陪审团的几次喊叫(第207页是个典型例子),对整个人类的呼叫(“人呀,请注意!”[第195页]),对他的车子的呼叫(“嗨,梅尔莫什,多谢了,老伙计”[第484页])。我在这儿尽说些统计数字,因为亨·亨对读者的直接招呼是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体现自相矛盾的新技巧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至于文学形式和手法方面,天底下没有什么新花样(借用一位诗人的说法);不断翻新的是环境和组合。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到了另一个时代就成了超现实主义。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或塞万提斯的读者来说,戏中戏、故事中的故事都是惯例;对于一个习惯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读者来说,戏中戏是荒诞的、莫名其妙的、装模作样的。关于重新启用“过时的”直接称呼,也是一样的道理。后詹姆斯时代的小说家通过完善比较新的“印象派”惯例(不露面的叙述者,“中央情报信息”,即使“靠不住”但始终如一的叙述人等等),似乎已经永久地排除了这样的自我意识的手法,在文学史的这样一个时刻,过时的直接称呼又复活并变了形。“这一新技巧是故意地不合时代的技巧,”豪·路·博尔赫斯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关键文本《〈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一文,(《迷宫》第44页)中写道:电影方面的相似作品可以在最近重又启用无声电影手法的导演的作品中信手找到(引人注意的导演有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和理查德·莱斯特)。——原注
(76) 沛奇·斯特格纳在《潜入美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艺术》一书(纽约,1966,第104页)中也指出了这一双关语。(译者按:克莱尔·奎尔蒂原文Clare Quilty是仿照clear guilty两个词,形声近似。)——原注
(77) 托·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6)1930年发表的诗《圣灰星期三》传达的是诗人对英国国教会的信仰以及他在《荒原》(1922)结尾处所呼吁的信念。诗得益于但丁的《神曲》,充满宗教寓意和象征主义色彩。
(78) 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法语诗人,象征派戏剧代表作家,获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
(79) Gregory Yefimovich Rasputin(1871—1916),俄国农民出身的修道士,因医治皇太子的病而颇受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的宠幸,并干预朝政,生活淫荡,不可一世,但终被保皇党骗至皇宫一地下室里杀死。
(80) The Rape of the Lock,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 —1744)所作,1712年发表时仅两章,1714年增至五章发表。诗采用仿英雄体,小题大做,写一对贵族男女因追逐游戏而交恶。这诚如英国大文豪约翰逊博士所言,诗作是“滑稽作品之最有趣者”,它把“新事物变熟悉了,熟悉的事物变新了”。
(81) 阿什尔庄园系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的哥特式小说《阿什尔庄园的倒塌》的叙述者儿时伙伴罗德里克·阿什尔家摇摇欲坠的庄园。叙述者前往拜访时,发现罗德里克与他的孪生妹妹梅德琳都处于精神与健康岌岌可危景况之中。梅德琳昏死过去就被埋葬,但又惊醒过来,在狂噪与死亡的痛苦中拖着罗德里克告别人间,同时庄园也倒塌在山间的湖水之中。
(82) 约翰·辉辛格:《人的游戏:文化游戏因素之研究》(波士顿,1955[1944年初版]第11页。文中虽未提及纳博科夫,但不失为阅读纳博科夫作品的绝好入门)。——原注
(83) 《洛丽塔》这一方面的意义,在特尼尔的风景棋盘(或棋盘风景)那幅画中形象地得到了表达;它是刘易斯·卡罗尔《镜中奇遇》第二章里的一幅插图。在那部小说里,一个棋局实实在在地与故事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原注
(84) New Criticism,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群文艺批评家,主要是美国文艺批评家的理论,对于诗歌与虚构散文从哲学与语言学角度来作分析的观点。托·斯·艾略特的批评文章对新批评论有极大的影响,然而这个理论的叫法是约·克·兰塞姆1941年出版的《新批评》一书中确定的。这个理论的着眼点是文本的模糊处,而不是作家生平的烙印。诚如这一运动的捍卫者大卫·戴奇斯所说:“新批评论教会了一代人如何阅读,这是不小的功绩。然而要读文学先要读生活。”(参看《朗文二十世纪文学指南》1981年莫里斯·霍塞修订版)
(85) 玛丽·麦卡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相遇》第ⅪⅩ卷(1962年10月号),第76页。[译者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国小说家,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心理,作品有长篇小说《她的伴侣》等。]——原注
(86) 博尔赫斯:《〈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相遇》第ⅪⅩ卷(1962年10月号),第44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