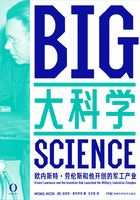
第一部分:机器
第1章 英雄时代
欧内斯特·卢瑟福是科学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是那种驾驭时代发展的巨人,而不是顺着别人的车辙亦步亦趋的盲从者。一位熟人曾对他说道:“你总是处在波峰上。”据说他是这样回答的:“是的,毕竟是我制造了波,不是吗?”他说话大声,笑声爽朗,对他那个时代里著名的“粗俗笑话”由衷地欣赏。C.P.斯诺(C.P.Snow)——卢瑟福的一个年轻的助手,曾以其小说被学术界和政府列于走廊橱窗而赢得文学名声——曾这样回忆起卢瑟福勋爵:“一个体格高大而笨拙的人,高大的凸窗下沿只到他半胸位置,他有大大的蓝眼睛和湿乎乎下垂的下唇。”
卢瑟福1871年出生于新西兰,父亲是一位能干的工匠,母亲是乡村教师。当时的新西兰还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遥远的海外殖民地。卢瑟福成年后成为他那个年代富于直觉的理论家和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没有人能质疑他在发掘实验结果的意义方面的天才能力,他的实验结果均产自他精心打造的手工设备。“卢瑟福是一个艺术家,”他以前的学生A.S.拉塞尔(A.S.Russell)这样评价道,“他的所有实验都带有他的独特风格。”
卢瑟福24岁时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当研究生。那是在1895年,一个偶然的时刻,当时物理学家们都在琢磨他们的设备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物理力。就在卢瑟福到来之前的一个月,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Wilhelm Roentgen)报告称,某种放电产生的辐射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它能将人的手骨成像在感光底版上。伦琴称他的这一发现叫X射线。
伦琴的报告促使巴黎的物理学家亨利·贝克勒耳(Henri Becquerel)寻找X射线的其他特征。他采用的方法是将多种化学物质放在阳光下暴晒。他用一张黑纸将感光底版包裹起来,再用涂有待检测化合物的纸盖在其上,然后将它们放置在太阳下,晒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将它们拿回房间查看密封底版上是否有阴影出现。1896年2月,巴黎连续几天是阴天,于是他将最新制备的材料——涂有铀盐的纸包裹着的底版——放在一个抽屉里,等待太阳再次露脸。当他给底版显影时,发现底版在黑暗的抽屉里竟然自发地被铀盐曝光了。
不久之后,玛丽·居里(Marie Curie)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在巴黎的他们的实验室确认,贝克勒耳射线是由某些元素自然产生的。这些元素里包括了他们所发现并命名的两种:钋(用以纪念玛丽·居里的故乡波兰)和镭。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放射性”。(贝克勒耳和居里夫妇因为在这一最初称为“贝克勒耳辐射”方面的工作而分享了1903年的诺贝尔奖。)
同一时期,其他科学家也在积极探索以解开隐藏在原子内部的奥秘。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J.J.汤姆孙(Joseph John Thomson)——欧内斯特·卢瑟福的导师,在1897年发现了电子,从而建立起原子可分割成更小的粒子——“微粒”(他这么称呼这种粒子)——的概念。汤姆孙提出了一种原子结构模型。在这种模型中,他的这种带负电荷的电子散布在未分割的正电荷体当中,犹如细碎的果粒散布在松软的蛋挞当中。这个模型一经出现便成为著名的“葡萄干布丁”模型。它风行了14年,直到卢瑟福将它请下台休息。
与此同时,卢瑟福也在忙着检查“铀辐射”,他的登台可说是由贝克勒耳的发现促成的。1899年,他确定放射性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他按放射性的穿透力将它们分为:α辐射——容易被铜、银、铂或玻璃吸收;β射线——贯穿力更强,能够像阳光穿过玻璃窗一样轻易穿过铜、铝等轻金属。此时卢瑟福已经搬到蒙特利尔,他获聘麦吉尔大学的教授职位,这所大学建有当时一流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由加拿大商人资助,是工业界资助科学研究的早期范例。卢瑟福有一位天资聪颖的助手,名叫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他提出了“同位素”的概念,用以命名同一种元素中那些结构不同但化学性质相同的元素成分。卢瑟福认定,像铀、钍和镭这些重元素的放射性是由衰变产生的。所谓衰变是指一种自然发生的转化过程。通过多步衰变——有些衰变仅持续几分钟,有些则历经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这些重元素最后变成放射性不活泼的铅。最终,卢瑟福确定,α射线实为失去电子的氦原子,即氦核;β射线是高能电子。这项工作使他荣获19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那时,他已经回到英国获聘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在曼彻斯特,他通过对原子结构这一核心问题的钻研,为科学树立了更大的里程碑。“我是在将原子看成是一个好看的硬家伙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根据个人趣味,你可以将它看成是红色的或灰色的。”多年后,他在谈到葡萄干布丁模型时这么说道。虽然他认为原子的空间基本上是空的,而不是点缀着带电什锦块的均匀质量体,但此时他还不认为这是一个替代模型。与曼彻斯特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助理汉斯·盖革(Hans Geiger)和欧内斯特·马斯登(Ernest Marsden)一起,他开始着手寻找这样一个替代模型,使用的工具就是α粒子。他知道,这些粒子都能被磁场偏转,但奇怪的是,它们在通过固体物质——如薄的云母片——时偏转得更厉害。这表明原子内部是一个电磁漩涡,而非平静的、坚实的布丁,这种漩涡使经过它的粒子被甩出去。
卢瑟福的实验是采用从纯净玻璃小瓶里的镭放射出的α粒子来轰击金箔。盖革和马斯登通过观察α粒子打在涂有硫化锌的玻璃板上所发出的闪光或闪烁来记录α粒子的散射。该装置显示出卢瑟福做事特有的简单性和风格,但执行起来任务极其繁重。观察者需要先坐在没有灯光的实验室里进行一个多小时的暗适应,然后一次只能持续观察一分钟,因为紧盯显微镜屏幕的紧张往往会产生虚幻的闪烁感,从而混淆了真实的闪烁。(盖革由此最终发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粒子计数器,从而解救了疲劳无助的实验者。)
实验表明,大多数α粒子穿过金属箔后仅有非常轻微的偏转或没有偏转。但有一小部分——大约是八千分之一——出现大角度反弹,有的甚至被直接回弹到放射源。
卢瑟福对这一结果感到震惊。“这几乎就像你向一张薄纸发射一枚38厘米的炮弹,结果它竟弹回来打在你身上一样难以置信,”几年后他这么说道,那时他已建立起核物理历史上最珍贵的图像。对他来说,理解这其中所发生的事情并不难,因为这一现象只能解释成原子内大部分空间是空的,几乎所有质量都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带电的内核上。只有当α粒子碰巧直接打在这个内核上或足够接近这个核才可能被它的电荷偏转。卢瑟福的结论是,这个内核就是原子核。
卢瑟福的发现在原子物理学家的模型概念上引起了一场革命,但这并不是他最终的成就。那是在1919年,他报告了一个比1911年观察到的薄纸反弹结果更令人吃惊的现象。
卢瑟福再次挪了位置,这次是去了剑桥,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一职。这间实验室是在1874年建立的,第一任主任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刚任命时麦克斯韦还不是那么出名,但在短短的几年内,他发表的关于电和磁的工作使他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所建立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也跟着成为欧洲领先的科学中心。麦克斯韦建立起来的电磁概念将电和磁看成是同一个电磁现象的两个方面,从而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经典物理学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世界之间建立起桥梁,他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成为英国物理学实验传统的充满生机的宝库。
在卢瑟福掌舵期间,卡文迪什实验室陶醉于其破旧但庄严的氛围中。在机构设置上它可谓小科学的缩影。建筑物的形状就像个L形围拢的小庭院:长边一侧三层,顶层的山墙上开着窗子,屋檐急剧向下倾斜。大楼里有一间大实验室和一间专供“教授”使用的小实验室,一间存放实验设备的房间和一个演讲大厅。卢瑟福每周过来三次,给大约四十名学生讲课,偶尔从上衣里面的兜里抽出几张备课卡片来提示一下。物理学家马克·奥利芬特(Mark Oliphant)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从澳大利亚来到卡文迪什。他是这样描述的:“地板上没铺地毯,油漆的松木大门显得昏暗,石灰墙面色彩驳杂,惨淡的光线透过脏兮兮的玻璃从天窗射下来。”对于实验室主任,他将卢瑟福描述为“一个高大、面色红润的男子,头发稀疏,胡子倒是一大把,让我不由得想起百货商店和邮局的看门人”。实验室严格遵守欧洲的“绅士传统”,晚上六点,不管实验是否还在进行,到点关门,一位年老的值班人员会来到实验台前不耐烦地瞪着还在工作的科学家,摇晃着手中的实验室大门钥匙提醒他时间。工作拖拉被认为是一种“坏的习惯,坏的形式,坏的科学”。
卡文迪什非常看重它昔日的光荣历史,当年它在十分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取得了伟大的进步。整个年度预算约为2000英镑,大约相当于21世纪里的80000美元。这点钱就是在旧时代按当时的工作强度来说也可谓捉襟见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诀窍全在于卢瑟福一帮助手的精明和手艺,他们能够从简洁优雅的实验装置中提取出最大的成果。1919年的实验就体现了卢瑟福团队的这一风格。
卢瑟福在带着詹姆斯·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一起工作时,后者的实验技能堪比卢瑟福本人,训练他如何让α粒子去打一系列气态靶:氧气、二氧化碳,甚至普通的空气。在用一个改进了的1911年的马斯登-盖革密闭盒进行实验时,他们发现,普通空气会产生特别频繁的闪烁,就是那种类似于氢原子核——质子——所产生的闪烁。卢瑟福正确地猜测到,这种现象与空气中所含的80%的氮有关。
“我们必然得出结论。”他写道,“氮原子……在与一个高速α粒子的近碰撞中被瓦解了。作为氮核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氢原子被释放出来。”这些绕口的话在科学界产生了地震,因为卢瑟福描述的这种现象是原子的第一次人工分裂。人们最终认识到,这个反应涉及氮原子核——由7个质子和7个中子组成——对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α粒子的吸收,然后放出1个质子,氮-14嬗变成同位素氧-17。但真正为科学世界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的是卢瑟福在文章结尾提出的观点。“总之这个结果表明,”他写道,“如果α粒子——或类似的弹丸——在实验中能获得更大的能量的话,我们就能够打破许多较轻原子核的结构。”
换句话说,由镭和钋自然产生的α粒子作为核探针已经物尽其用。它们已经显得不够强大。我们必须找出某种途径来使弹丸具有更大的能量:人的智慧加上大自然的馈赠就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核探针。卢瑟福为核物理学的未来制定了一个路线图。在遥远的地平线那端,现实将表明,完成获得必要能量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卢瑟福这一代人所熟知的优雅的基础科学的能力。
卢瑟福的发现在物理学领域催生了一批精英。后来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一个英雄的时代”,这不仅仅是因为知识资源被集中到应对卢瑟福提出的挑战,而且还在于这一工作发生在一种知识危机的背景下。物理学家们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惊人的难题,这些难题彻底撼动了他们关于自然世界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痛苦地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那个时代的杰出物理学家的话里总是充满了对知识的绝望。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新的量子力学理论的最早信徒,在1923年写道:“大量的矛盾可能仅仅意味着整个物理学概念系统必须从根本上推倒重建。”维也纳理论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一个集严谨的知识完整性与尖刻的批评于一身的人(他对一篇草率的文章的著名批判是称它“简直不叫错”[1]),在1925年感叹道,物理已变得“非常混乱”,“我希望我……从来没听说过它”。即使头脑冷静的詹姆斯·查德威克在回忆起卡文迪什的实验时也称它“如此绝望,简直到目前为止都属于炼金术时代的做法”。
尽管他们的任务异常复杂,但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的工作才吸引了公众的目光。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看来,物理学带有戏剧性的光环,甚至还有浪漫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始于亚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勋爵于1919年11月在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举行的会议上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做出的惊人确认。伦敦《泰晤士报》历史性地以三行标题“科学的革命/新的宇宙理论/牛顿的想法被推翻”宣布了这一结果。爱丁顿通过艰苦的宣传活动,使得相对论及其创建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成为国际生活中人尽皆知的热词。但这只是激发了公众对探索自然界基本真理的好奇心,同时让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现代物理学家都是无畏的人,为了收集数据敢于奔赴天涯海角,就像爱丁顿,为了见证相对论所预言的日食奇景,居然跑到遥远的非洲普林西比岛上去。
报纸编辑表现出对最新突破的极大兴趣。科学家成了名人。1921年,玛丽·居里带着她的两个女儿——艾娃(Eve)和伊莲娜(Irène)——做了一次6周的美国之旅,这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钦佩之情。这次访问是由玛丽·马丁莉·梅洛尼(Marie Mattingly Meloney)夫人发起的。她是纽约的一位社会名流,也是一家时尚杂志的老板。当她得知居里夫人的研究因缺钱买不起镭时感到非常震惊。梅洛尼出了个点子:筹集100000美元为居里购买1克这种宝贵的矿物质(这个量差不多就是能嵌在顶针里的那一点),并邀请居里坐船来美国接受这项礼物。“居里夫人正计划终结所有癌症”,《纽约时报》在她到来那天早上的头版上发布了这一消息(次日报纸又悄悄地将这条赤裸裸的断言收回了)。居里夫人此次访问的高潮是在白宫受到梅洛尼和包括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琅沃思(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在内的华盛顿社会名流的隆重接待。玛丽·居里直接从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Harding)的手上接下了载有镭的缎带瓶,之后她用她那“蹩脚的英语”(《纽约时报》用语)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可见即使在小科学时代也需要这样的融资。
公众开始相信,物理学掌握着自然世界所有现象的关键,包括化学和生物学。撰写卢瑟福传记的作者亚瑟·伊芙(Arthur S.Eve)写道:“物理学家们携最初的成功,正努力根据正电子、负电子和它们在以太中产生的效应来解释所有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如果他们是对的,他说:“像遗传、记忆和智力等现象,以及我们的道德和宗教思想……都可以根据正、负电子和以太来解释。”
并不是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如此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深入地探究原子结构的复杂性,但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却增长有限。他们的困惑源于两个相关且同样令人费解的现象。一个是自然在微尺度上表现出的所谓波粒二象性:实验结果显示,光和电子的行为有时候像粒子,有时候则像波。
爱因斯坦早期关于光电效应的开创性工作表明,光是由一股“光量子”或粒子构成的。但他承认,如衍射、干涉和散射等行为又都属于波的性质。他没有调和这些相互矛盾的观察结果,而是将这一问题提交到他的同事面前。“这是我的观点。”1909年,他在德国萨尔茨堡召开的一次科学会议上这么宣布:“理论物理学下一阶段的发展将带给我们一种光的理论,它可以解释为一种波与(粒子)理论相融合的理论。”
物理学家带着未解决的亚原子行为之谜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望不断积累的观察结果能将他们引向事实真相。但情况恰恰相反:他们获得的数据越多,似乎他们知道的就越少。“非常奇怪的情况是,越接近问题的解,”年轻有为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沃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这样认为,“矛盾却变得越来越严重。”唯一的答案似乎就像英国物理学家威廉·布拉格(William Bragg)勋爵当作玩笑提出的:“上帝在每周的一、三、五利用波动理论来解释电磁现象;魔鬼则在每周的二、四、六用量子理论来解释它。”
大概要算海森伯和他的导师,说话温柔但逻辑严谨的丹麦人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最后猜中了正解。海森伯将这个认识过程比作在浓雾中看一个浮现的对象。他们的结论是,对于发生在量子尺度上的事件,任何人能知道的仅限于他能够观察到的是什么——所获知识依赖于观察手段。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所用的仪器是设计用来检测作为粒子的电子的,那么这些电子就会表现为粒子;如果他所用的仪器是设计用来检测波的,那么这些电子就会以波的形式出现。电子作为粒子和电子作为波是同一事物的同样有效的两种表现,这里没有矛盾,有的只是——按玻尔的话——“互补性”。
理论认识上这可算是一种突破,但互补性并没有解决原子核所产生的反常结果。核结构成为20世纪物理学家的第二大神秘难题。
欧内斯特·卢瑟福将原子描述成一个微型太阳系:带负电荷的电子围绕着一个体积微小但质量巨大的带正电的核做轨道运动,这个核由质子和带负电荷的电子构成。这个模型的诱人的简单性使得它成为广为接受的真理,特别是在尼尔斯·玻尔于1913年证明了电子只能在与特定能级相关的、距核一定距离的轨道上运动之后,就更是如此。这似乎是调和了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关系:前者支配轨道运动,后者决定着能级,从而决定了电子可以占据的轨道“壳层”。原子在整体上呈现中性:轨道电子的负电荷平衡了原子核的正电荷,原子核之所以呈正电性是因为质子数大于电子数。因此,按卢瑟福的推算,氦原子有2个轨道电子和1个由4个质子和2个电子构成的核;镭有138个轨道电子和一个由226个质子和88个电子构成的核。
问题很快就变得明显,这个模型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而且越重的原子问题越大。到了1923年,也就是玻尔原子模型提出后的第10个年头,物理学家们仍在质疑其普适性。玻尔模型仅适用于最简单原子——氢——的实验观察,氢只有1个质子和1个电子。而对于下一个最重的原子——氦,这个模型便开始失效,所引起的反常几乎让马克斯·玻恩感到绝望。
麻烦制造者是那些核内电子。没人能解释这么多粒子是如何被约束在核内的;或者如果有东西切入,这些高能粒子是如何能够待得住的。玻尔本人被迫承认,他珍爱的量子力学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核,我们或许需要发展出更新颖也更让人不知所措的机制来解释日渐增多的实验反常。
现成的解决方案卢瑟福那里就有。这位卡文迪什的元老自这个十年开始就一直在思索这个谜团,当时他认为,核内电子在强相互作用力的作用下会产生“严重变形”,因而它们在性质上非常不同于轨道电子。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电子会与质子结合形成一个不带电的、迄今未被发现的复合粒子,他称之为中子。
卢瑟福让永远忠实的查德威克来探索这种难以捉摸的中子。“他向我详细地阐述了……问题的困难性,复合核如何能够建立起来,如果可用的基本粒子只有质子和电子的话,因此现在需要的就是借助于中子。”查德威克多年后叙述道:“他大方地承认这纯粹是猜测……除了私下讨论,他很少提及这些问题。”但“他完全改变了我。”
随着探索的进行,事情变得越发明显:要解开核结构的神秘性,所需的探针的高能量已超出大自然提供的范围。卢瑟福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一法则的潜在影响。镭发射的α粒子的能量接近7.6百万电子伏,β射线,即电子,则只有3百万电子伏。“我们所需要的,”卢瑟福宣称,“是这样一种设备,它能提供10百万伏特量级的电压,可以安全地置于一个相当大的房间内,由几个千瓦功率的电源驱动……我向懂技术的朋友们推荐这个有趣的问题。”
但产生卢瑟福所要求的电压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简单的部分,大自然就能满足这一要求,因为一个闪电的电压就有3~200百万伏特。这些巨大的、短暂的电压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景观,但能被利用的价值不大。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个力量,如何维持它,并操纵它对原子核实施攻击。通过电力行业常见的安排,如串联变压器,“能获得的电压似乎没有上限”,卢瑟福声称,再说发电厂就能够产生“一道几码长的火花,类似一个小尺度的快速连续的闪电”。但这项技术仍谈不上“接近,更不用说超越放射性元素在提供高速电子和高速原子方面的作用了”。
科学家在试图获得所需能量的过程中常常遭遇到设备被炸成碎片,实验室到处散落着玻璃碎片的令人沮丧的局面。有些人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大自然的愤怒:来自柏林大学的三名男子在阿尔卑斯山的两座山峰之间拉了一对700码(1码=0.9米)长的钢缆,等待测量雷电。当雷电到来时,他们测得的电位差高达15百万伏特——但狂怒的雷击将其中一人当场炸得粉身碎骨。
美国高校这时已开始分享与大企业合作的成果,并将这种协作关系正式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州理工学院接受了南加州爱迪生有限公司馈赠的礼物——一台1百万伏的变压器,这样加州理工大学就可以发展高电压技术,爱迪生当年曾梦想,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在三百英里外的科罗拉多河上建造一座大坝(即胡佛大坝)水电站,将产生的电力传输到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们用这台机器来产生X射线,但它远不及卢瑟福所要求的那般紧凑——不是放进“一个相当大的房间”,而是填满了一座面积达836平方米的三层大楼。整个楼坐落在地下很深的地基上。但就是这样也仍然无法产生可用的高能粒子束。最后,这台机器成为加州理工学院最著名的景观,每逢校庆“纪念日”,校友们便要到这里来观看它在雷鸣般的报告声中所发出的“长长的九曲回肠般的电弧”。
在探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物理学家默尔·图夫(Merle Tuve)。他决心在真空管里实现一次性加载1百万伏的高压,那么多的能量会把现有的真空管炸得粉碎。“我相信,我们所有人在年轻时都是极端分子。”他后来解释说:“我们总是想去达到温度的极限、压力的极限、电压的极限、真空的极限,或是其他什么的极限。”他选择的仪器是特斯拉线圈,一种由富于远见的物理学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在1890年发明的高压变压器。图夫的版本是由铜绕线包裹着的一个空心的三英尺长的玻璃管构成,整个装置浸在盛满油的加压缸里以抑制电火花。他和他的华盛顿卡耐基学院的同事们设法产生了1.5百万伏甚至更高的电压来显示β射线的产生和偶尔出现的加速质子,但这台设备显得粗糙、古怪,而且不可控。不久,图夫就抛弃了它,觉得它不适合做原子核研究,并诅咒它为“无法摆脱的麻烦”。
图夫转向求助于静电起电机。静电起电机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名叫罗伯特·范德格拉夫(Robert Van de Graaff)的工程师发明的。这个装置有一个位于绝缘柱顶部的大的空心金属球壳,球壳内有一套穿过绝缘柱自下而上连续传动的丝织带。在底部,直流电源通过金属尖针向丝织带放电,使丝织带带电并通过电机转动传送到顶部;在顶部,再通过一根与金属球壳相连的金属针将传送带上的电荷传送到球壳上,并在壳上积累,使之最终达到合适的电压。范德格拉夫起电机可以产生丰富的电压和火花,从而使它成为许多好莱坞影片中疯狂科学家必备的主要道具,但它还不足以成为卢瑟福所需的能提供“富足的”高能子弹的武器。为此图夫和范德格拉夫一起,想方设法利用真空管和其他设备来产生所需的经过聚焦的高能带电粒子束。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但就在他们艰辛跋涉的时候,范德格拉夫的技术已经被另一些全新的东西超越。
这种新技术的开发者就是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一个生长在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名叫坎顿(Canton)的小镇上,曾在童年与默尔·图夫——他的同学和街对面的小伙伴——一起分享他所迷恋的电动小玩意儿的人。在物理学撞上阻碍理解原子核的这面大墙之际,欧内斯特·劳伦斯如命中注定一般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道障碍令人恼怒,物理学家只能隔着这道墙远远盯着远处昏暗的景观,真相一直笼罩在薄雾中。劳伦斯像是在这堵墙上打开了一道缺口,薄雾瞬间被清除掉。同时,劳伦斯的发明还标志着科学研究从小科学形态过渡到大科学。他发明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人为地将亚原子粒子加速到足够的能量使之打入到核内,让物理学家看清楚核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在他们的同事看来,卢瑟福和劳伦斯都以“欧内斯特”著称,他们的工作都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历史上留下划时代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