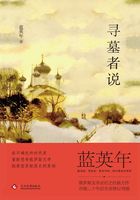
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
苏联作家卡普列尔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恐怕无人知晓,但他的作品又恐怕无人不知。他就是在中国放映过无数次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脚本作者。他不仅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还是70年代苏联人民最热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卡普列尔半生坎坷,几次大起大落,都是因为他太痴情、太真诚、太富于正义感的缘故。他妻子戏称他为“并非愁容的骑士”,除掉愁容外,他确实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一个普通的敖德萨青年,不到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剧本《三个同志》和《矿工们》,并被搬上银幕,几年之间便成为苏联知名的剧作家。1938年莫洛托夫亲自主持十月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卡普列尔应邀参加,并以剧本《起义》(即《列宁在十月》)一举夺魁。接着他又创作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在苏联电影、戏剧史上,卡普列尔是第一个把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写进剧本的。这两部由罗姆执导、舒金扮演列宁的影片一上映,列宁仿佛又回到人民之中,卡普列尔由此名扬天下。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有幸或者说不幸结识了女中学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且一见钟情。如果斯维特兰娜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真挚的爱情也许会绽开艳丽的花朵。然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千金,卡普列尔则是犹太血统的敖德萨人,因此悲剧就难以避免了。斯大林不准女儿同卡普列尔恋爱,除后者是犹太人外,还因为卡普列尔在《列宁在十月》中对斯大林颂扬得不多,对斯大林的政敌丑化得不够。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讯刚刚结束,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之外,统统被斯大林处死。斯大林想把自己说成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但卡普列尔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并未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影片已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最初,斯大林只想把他们拆散,两人不再来往就算了,所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斯大林卫队长克拉西夫将军派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列尔打电话,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南方去。卡普列尔被爱情冲昏头脑,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电话里叫他滚蛋。接着,好友作家西蒙诺夫再次劝他到南方去,卡普列尔依然不听。苏德战争爆发后,卡普列尔当了战地记者,1942年底,他飞往斯大林格勒采访。此时卡普列尔非但没冷静下来,在离别的煎熬中,爱情变得更加热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L中尉发自斯大林格勒的通讯》,竟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斯维特兰娜来。信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窗口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连斯维特兰娜的居住地点都点出来了,等于向全国公开他同斯大林女儿的爱情。深知父亲性格的斯维特兰娜读了这篇战地通讯后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天真的卡普列尔闯了大祸。这时斯大林突然从办公室赶回家。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写道:
“平时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儿?在哪儿?’接着又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儿?’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吻说出‘作家’这两个字。‘我全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拍拍他的衣袋。‘快,都拿出来!你的卡普列尔是英国间谍,已经被捕!’
‘可我爱他!’我说,我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你爱他!’父亲对这个‘爱’字充满仇恨,大喊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这糊涂虫!’说完他拿起所有信件、照片回餐厅去了。”
这次短暂的爱情,以卡普列尔被捕、斯维特兰娜同父亲关系破裂而告终。著名作家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从电影字幕和报刊上永远消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影片,1951年在我国首次放映时,字幕上当然不会再有作者的名字了。
1943~1953年,卡普列尔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但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未改变他的性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立即被释放,重返莫斯科。他依旧那样天真、真挚、充满正义感,以散文家,说得更确切些,以杂文家的姿态投入惩恶扬善的斗争。
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靴子踹胸口》便是他对索契民警局宣战的檄文。他揭露了索契民警局局长的恶棍行径:把女儿送进疯人院,仅仅因为她爱上普通司机;而把司机关进监狱也就因为他胆敢接受民警局局长千金的爱情。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民警局差点把卡普列尔投入监狱,幸亏赫鲁晓夫得知后发了脾气,卡普列尔才得以幸免。
为了恢复影片《女友们》的作者瓦西里耶娃的著作权,卡普列尔四处奔走,恳求知情者主持公道,还在《俄罗斯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呼吁文章。在卡普列尔的感召下,许多著名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剽窃女作家作品的导演发表声明,承认被无辜镇压的女作家的著作权。但影片导演仍不吭声,结果卡普列尔的满腔热情付诸东流。其实,卡普列尔同女作家瓦西里耶娃非亲非故,为恢复她的著作权而战斗,不过是想伸张正义,恢复人们对正义的信心罢了。
50年代中期,卡普列尔被选为国际电影编剧协会副理事长。换了别人,这个职务不过多增添了个荣誉头衔,多几次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但卡普列尔在这个岗位上却开始了新的战斗——为编剧的著作权而战斗。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影片的字幕上只印有导演和演员的名字,却不印编剧的名字。电影史介绍某部影片时也只提导演,不提编剧。卡普列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公道的,是对编剧劳动的蔑视。他在《打输了的一场战役》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是:创作一部影片谁更重要,爸爸还是妈妈。我认为创作影片既需要爸爸——编剧,也需要妈妈——导演。”他在各种场合呼吁社会对编剧给予应有的尊重。他的行动深得编剧们的赞赏,他们私下与他握手道谢,但没有一个编剧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他们不敢得罪导演,担心一旦得罪导演,导演便不会选用他们的脚本了。面对强大的导演营垒,卡普列尔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影片字幕仍不署编剧名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片上打出编剧名字的传统逐渐恢复,编剧的劳动终于得到承认。苏联影片字幕上打印编剧的名字是同卡普列尔的斗争分不开的。
1966年卡普列尔应苏联国家电视台邀请,担任电视节目“电影丛谈”主持人。“电影丛谈”包括新影片介绍;同国内外演员、导演、编剧交谈;介绍电影档案资料;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等。从此卡普列尔又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广大电视观众喜爱的明星。观众之所以喜欢他,因为他从不说空话、套话,只说真话。但观众喜爱并不等于领导满意,卡普列尔一到电视台便在节目播放的形式上同台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卡普列尔坚持有权参与编排节目、邀请嘉宾,谈论人们关心的问题。慑于卡普列尔的威望,电视台只好让步,这样苏联广大电视观众才能在银屏上看到鬓发苍白的心爱的剧作家,倾听他沁人肺腑的话语。
不久,电视台感到观众太爱收看他的节目,致使对其他节目失去兴趣,决定停止他的节目。卡普列尔便向苏联电视委员会主席拉平递交辞呈。他把辞呈往拉平桌上一放,掉头就走,并把门“砰”的一声带上。于是拉平解除他主持人的职务,并销毁他所主持的节目的全部录像。卡普列尔在观众的视野中从此消失了,直到他1978年去世,报刊、电视上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博览群书》1995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