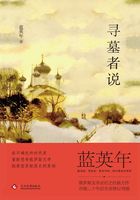
《喀秋莎》作者的桑榆暮景
伊萨科夫斯基是中国读者最熟悉、最喜爱的苏联诗人。以他的诗谱成的歌曲《喀秋莎》从苏联唱到中国,从30年代唱到今天,有谁没听过呢?他的自传和诗歌选集早已译成中文,不论翻译过来的还是我们自己编写的《苏联文学史》,都用整章或整节的篇幅介绍他的创作生平,稍涉猎苏联文学的人对他都略知一二。他是斯摩棱斯克州人,1900年生于农民家庭,少年开始写诗,后名气越来越大,1931年调莫斯科任《集体庄员》杂志编辑。1943年以《谁知道他》、《喀秋莎》、《在井旁》等诗获第一届斯大林奖,1947年以《诗与歌》再度获斯大林奖。自1947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年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是农民诗人或来自农村的诗人,绝大部分诗歌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然而自传(只写到1949年)和各种文学史给人的印象是:伊萨科夫斯基是集体农庄的新生活歌手,创作道路一帆风顺,深受人民的喜爱和当局的恩宠,在国内接连不断的清洗、镇压、迫害的惊涛骇浪中未损一根毫毛,是苏联作家当中少有的幸运儿。但在当权者的政策和人民的权益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又怎能做到让两头都满意呢?如果歌颂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势必歪曲现实,今天不会再有读者;如果真实地反映从根子上摧毁俄国农村经济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恐怕诗人的脑袋早就搬了家。伊萨科夫斯基有何奥秘呢?
去年秋天我在俄罗斯教汉语,同俄国朋友一起把当天聚会时仍唱的伊萨科夫斯基的诗歌集中起来,共得16首。统观这16首诗歌时,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竟没有一首歌颂农村“新面貌”的。诗人讴歌的是俄罗斯苍茫而绮丽的大自然、淳厚的民风和男女炽热的爱情,并往往带着淡淡的忧伤。卫国战争的诗歌则呼唤人民把敌人赶出自己的家园,誓死保卫母亲——俄罗斯。连集体农庄的影子也没有。我又翻阅1988年出版的《伊萨科夫斯基诗文集》(相当于全集),发现其中有“集体农庄”、“共青团员”等字眼,有对农村新变化的描绘,如农村有了电灯,但都不是直接歌颂集体农庄的。也找到几首描绘农庄庄员的,如《生活的地理学》,除该诗文集外,他生前所编的选集均未收入,想来诗人对这几首诗不满意,我读了也觉得矫情。我这种看法是否站得住脚,尚需有力的论据。这很快便在孔德拉托维奇的《〈新世界〉日志》(1991年出版)一书中找到。孔德拉托维奇是《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助手,《日志》记录了同该杂志有关的大事。1966年特瓦尔多夫斯基有意发表伊萨科夫斯基1946年写成的长诗《真理的童话》,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部招数,仍无法打通书报检查机构这一关。《日志》记录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谈论伊萨科夫斯基创作的一段话。两位诗人是多年好友,彼此了解,所以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伊萨科夫斯基创作的看法尽管同苏联文学史的定评大相径庭,但仍不失为真知灼见。
1967年6月15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对《新世界》的同事们说:“不管人们怎样谈论伊萨科夫斯基,他都是一位才华横溢、与众不同的诗人。可我重读他的诗时明白了一件可怕的事:他哪首诗也未歌颂集体农庄的新农村。那时他心里的什么东西被扯断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家索科洛夫—米季科夫干脆不再写斯摩棱斯克地区,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可伊萨科夫斯基还写。
但每当他要找到富有诗意的色彩时便转向旧农村。那时他便写得妙极了。他沉浸在往事中,描绘往昔的生活。如果硬塞给他一个题材让他写,他写得糟透了。以他那首《生活的地理学》为例,写的是看守集体农庄麦田的庄员。夜里他看见自家农舍着火了,怎么办?去救火,抢救财产?不行,他是哨兵,得坚守岗位。结果家舍化为灰烬。想想太可怕、太荒唐了。他看守麦田是怕女人和孩子们掐麦穗煮麦粥喝。如果不是饿得要命谁会干这种事!而这一切多么不人道啊。涅克拉索夫写过一首描写流浪汉的诗。流浪汉因偷面包被人当贼打。我们读的时候却站在流浪汉一边。不能不如此。列斯科夫写过一个在冬宫站岗的哨兵,他听见有人掉进涅瓦河,擅自离岗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可又不能不离开。哨兵跑去搭救落水者,后来长官因他擅自离岗惩罚他,但惩罚得不重,也不可能重。俄国古典文学便是这样处理这类题材的。可伊萨科夫斯基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诚心实意地描写集体农庄的新生活,可每次都不由自主地写成《生活的地理学》那样。他写得多,因为报社老催他。催他写他就写,写了很多坏诗,专供报刊用的诗。后来他病了才摆脱他们的纠缠。然而一回到过去他就写得好极了。后来他创作的高潮是歌词,但请你们大家注意,所有歌词写的都不是集体农庄的农村。‘喀秋莎走在峻峭的河岸上’,她是从哪儿走出来的,农场宿舍还是自家农舍?这你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歌词,战争期间他的诗歌响彻祖国大地。这是他第二个创作高潮,因为已无须歌颂集体农庄了。难道战争期间提出过‘捍卫亲爱的集体农庄’的口号?提出过捍卫祖国,捍卫‘一切神圣的东西’,甚至有过‘为被凌辱的神圣的东西而复仇’的口号。可没人保卫集体农庄,也没人号召大家去捍卫。那时伊萨科夫斯基的歌词写得格外好。这是他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创作高潮。”
我引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话绝非挟大诗人的威望以壮自己的声势,也无以“英雄所见略同”来抬高自己之意,而只想说伊萨科夫斯基的创作特点非常显眼,不抱成见的读者都能感觉到。苏联文学史不提,另有原因,因为它们连伊萨科夫斯基屡遭打击也只字不提。这就使我们无从了解为什么1949年以后,诗人尚不满半百的时候便沉默了,或再没写出流传后世的好诗了。而实际上,在作家惨遭迫害的年代,伊萨科夫斯基不可能成为例外,他同他们一样同样遭受过打击和不公正的对待。战后他对自己一生经历、不正常的社会生活进行过深刻的反思。长诗《真理的童话》便是反思的结果,但完成后无处发表,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沉默的原因。
1945年伊萨科夫斯基发表了《敌人烧毁了他家园的村屋……》:
敌人烧毁了他家园的村屋,
把他全家的人杀个精光。
士兵他如今该投奔何处,
向谁去诉说心中的悲伤?
士兵他怀着深深的悲痛,
在两条路的交叉口停留。
士兵在那宽阔的田野中,
找到长满青草的坟丘。
士兵伫立着——像有个硬块
把他喉咙紧紧掐住。
士兵说:“普拉斯科维娅,赶快
迎接英雄——自己的丈夫。
快为客人准备好美食,
摆出宴席把他款待,
我回到你身边来庆祝节日,
和你同庆我的归来……”
没有任何人对士兵搭理,
没有任何人把士兵欢迎,
只有温煦的夏风缕缕
把她坟头上的小草拂动。
士兵叹口气,紧了紧皮带,
打开自己的行军背包,
把一瓶苦酒掏了出来,
在墓前的灰石板上摆好。
普拉斯科维娅,别把我怪罪,
我回到你身边是这种心意:
我本想为你的健康干杯,
如今该举杯祝你灵魂安息。
(顾蕴璞译)
这首诗发表后立即受到报刊的严厉批评,打头阵的是《共青真理报》评论家谢苗·特列古布。他质问伊萨科夫斯基,在胜利凯旋之日,万民同庆之时,为什么不同全国人民一起欢庆胜利,却唱起悲伤的歌:“伊萨科夫斯基竟然写道:‘士兵他如今该投奔何处,向谁去诉说心中的悲伤?’难道在我们苏维埃国家里无处可去?我们有可去的地方,我们这里总能找到出路。比如他可以上村苏维埃嘛,他们会听他倾诉,给他帮助……”用这首诗谱成的歌曲,也禁止演唱。然而伊萨科夫斯基对这种愚蠢的批评却不能公开反驳,只能在信里向朋友们发泄自己的愤慨。早在1942年他在致自己的老搭档、著名作曲家扎哈罗夫的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坚信战争将以希特勒彻底崩溃而告终,我国不仅应唱胜利的歌曲,还应在歌曲中为那些为祖国捐躯的人哭泣。”(《伊萨科夫斯基文学书简》,1990年,以下引文均出自该书)但他刚一为他们哭泣,棍子便向他当头打来。他在致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老实说,只有伪君子和白痴才会这样批评这首诗呢。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简直像笑话。但它却表明我们的评论界愚蠢到何等地步。我认为这是我最优秀的诗歌之一。”
这次批评促使伊萨科夫斯基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走过的荆棘塞途的一生。一幕幕惨剧重又浮现在他眼前。他来自农村,根子在农村,对集体化的恶果有切肤之痛。他曾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现已变成镜花水月。1945年他开始写长诗《真理的童话》。长诗采用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体裁。老汉萨韦利·库兹米奇受众乡亲之托出外寻求真理。老汉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穿过密林和沙漠,从乡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乡村,最后在破旧不堪、杂草丛生的农舍里找到真理。真理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不是貌似天仙的少女,而是躬腰驼背的老妪。1966年他在致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信中写道:“我在《真理报》编辑部朗读了长诗,三个人就长诗发言,……我记得他们的态度是否定的。他们没太骂我,也没夸我。后来我把《真理的童话》交给波利卡尔波夫(他当时任作协书记)。他读过后只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说我国人民已找到真理,因此未必需要对此再发议论!简单说,他话里的意思是不需要这首长诗。他的话令我万分惊讶,但我毫未反驳。反驳是徒劳的。可我并未投降。为了挽救长诗,我又写了第二部。我想向你解释为什么要写第二部。《童话》以萨韦利同真理对话结束。老汉对真理说:现在叫他怎么办?人们认为真理是美丽的、强健的、无所不能的,可以征服一切。可真理原来是这般模样,他怎么对推举他出来的乡亲们说呢?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会把他打死。这时真理给萨韦利出了个主意:‘你啊——鼓起勇气……就对他们撒个谎吧。’我的《童话》就此结束。我动手写第二部的时候首先要解释真理为什么教萨韦利撒谎。
“第二部里我采用了著名的母亲撒谎的传说。她向被押上断头台的儿子挥动白手绢。白手绢表示母亲已经向沙皇为他求得赦免。但实际上并未求得。她欺骗儿子为的是儿子在断头台上不泄气,英勇就义,不玷污他为之献身的理想。但我在第二部里所说的还不止这些。我写儿子知道母亲欺骗他,但却装出相信的样子,免得母亲伤心,因为她望着他就义表现得沉稳而无畏。换句话,我想说明在某些情况下谎言也可以是神圣的。”
伊萨科夫斯基想对诗友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明什么呢?世上没有“真理”,所以人们不得不说谎。谎言不是可以慰抚以至鼓舞人们吗?他一生中也说过谎,但那决不是想欺骗人民,而是给他们打气。如在《致俄罗斯妇女》那首诗中,他写后方妇女过得极为艰苦,但给前方战士们的信中却说她们过得很好,然而“前沿上的战士们,读着你们的信,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你们那神圣的谎言”。谎言当然不都是神圣的,所以诗人为自己所说过的非神圣的谎言深感内疚。
伊萨科夫斯基在信中继续写道,他把《童话》交给意识形态负责人列休切夫斯基,后者答应把《童话》转交给广播电台。但伊萨科夫斯基必须用诗的形式写个如下内容的后记:多少年过去了,萨韦利早已去世,坟头已成平地,新的时代开始了。人民过上新生活,他们不必再寻求真理,因为真理到处同人民在一起,并已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地位。但他没写后记,也没把《童话》交给广播电台,原封不动放在书柜里。他最后决定,如果《童话》有朝一日能发表,那只发表第一部,删除第二部,因为感到“神圣的谎言”的提法不真诚,太做作。长诗结尾处他还谈到一种艰难的真理,并非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追求这种艰难的真理,因为它很危险。所以长诗不得不这样结尾:“你啊,就对乡亲们撒个谎吧。”这样“真理”便成为粉饰现实和欺骗人民的手段了。
伊萨科夫斯基不愿再写“神圣的谎言”,又无力追求艰难的“真理”。这不仅由于他胆量不够,生理上也难做到。他先天高度近视,晚年完全失明,妻子去世后生活不能自理。他的诗名虽如日中天,但当局对他已失去兴趣,除他70寿辰时给他戴顶高帽子——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外,平时对他毫不关心。他不再写诗,而以翻译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白俄罗斯诗人库帕拉的作品度日。诗友特瓦尔多夫斯基虽对他十分关心,想帮他一把,但力不从心,竟无法在自己主编的《新世界》上发表《真理的童话》。这首长诗41年后,1987年才在《旗》杂志上发表,这时伊萨科夫斯基已去世14年了。如解冻时期长诗得以发表,其影响定会大大超过爱伦堡的《解冻》,也许伊萨科夫斯基还会写出流芳后世的诗篇,不会在创作最成熟的阶段缄默了吧。
《博览群书》199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