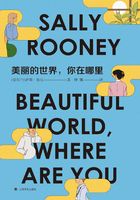
第8章
亲爱的艾丽丝。你说马上要去罗马,你是去工作吗?我无意干涉你的生活,可我以为你要休息一阵的。当然,我希望你一路顺风,不过我不知道你该不该这么快就开始参加公开活动。之前你给我发了那么夸张的信息,抱怨出版界,说里面你认识的每个人都那么嗜血,想杀了你或者把你操死为止,你要是觉得这样做能发泄情绪,那请尽管继续。毫无疑问,你在工作中会遇到恶人,但我觉得你也遇到了很多无聊但具备一般道德水准的人。当然了,我不是说你不痛苦——我知道你很痛苦,所以我很惊讶你又准备让自己经历这一切。你是从都柏林起飞吗?如果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在你起飞前见一面……
我本来不觉得我坐下来回信时心情不佳,但或许的确如此。我不想让你觉得你可怕的生活其实是一种特权,但无论从哪种合理的定义看来,它都是。好比说,我一年挣两万欧元,三分之二都拿去交房租,和讨厌我的人合租一间小公寓,而你一年赚二十万欧(?),独居在乡下一栋巨大宅邸里,但哪怕如此,我不觉得如果换做是我,我会比你更享受你的生活。如你所说,任何一个能享受这种生活的人肯定有什么问题。可反正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不是吗?我今天上网上太久了,开始感到压抑。最糟的是,我真心觉得网上大部分人都是出于好意,但是自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的政治话语已经发生如此迅速而严重的退化,大多数试图理解当下历史瞬间的努力最后基本上都毫无意义。人人都依附于各自的意识形态,这情有可原,但他们又大多不愿说明这些意识形态由什么构成,如何形成,有什么目的。唯一明确的架构是,对于每个受害群体(出身贫寒的人、女性、有色族裔)来说,都存在一个压迫群体(出身富裕的人、男性、白人)。但在这种框架下,受害者和压迫者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历史性的,不如说是理论性的,受害者都纯良至极,压迫者则人人邪恶。因此,身为特定身份群体的成员就拥有了无法超越的道德意义,我们的大量话语都致力于将个体划分到合适的群体中,也就是说,赋予他们匹配的道德判断。
即使严肃的政治行动仍可能发生——我觉得这个问题尚可讨论,它跟我们这类人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认为它基本上与我们无关。老实说,如果为了人类福祉我们不得不去死,我会毫无怨言地接受,因为我不配拥有我的生命,甚至并不享受它。但我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对这份事业作出贡献,无论是什么贡献,无论它有多渺小,我都不介意,因为我反正也是为了自己好才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折磨的其实是我们自己,虽然是以另一种方式。没人希望这样活着。至少我不希望。我想要另一种生活,或者我死了能让别人将来过上这种生活,我也愿意。但我在网上没有看到什么值得为之赴死的思想。网上唯一的思想似乎是我们应当注视无穷的人类苦难在我们面前展开,等待最贫困、最受压迫的人转过身来,告诉我们怎么停下来。我们似乎认为——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尚未得到解释——剥削自身会生成解决剥削的途径,而提出异议就是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类似男性的说教。可要是剥削不会产生解决方案呢?如果我们只是在白白等待,而这些没有工具来终结痛苦的人则继续受着苦?我们这些有工具的人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采取行动的人会招致批评。哦,说得好听,可我又采取过什么行动呢?其实我的问题在于,我因为别人没有答案而光火,哪怕我自己也同样没有答案。我算老几,有资格要求别人谦逊宽容?我向世界索取了这么多,自己对它做过什么贡献?我哪怕降解成一捧尘土也没人在乎,这也是理所当然。
另外,我有了一个新理论。想听吗?如果不想你可以跳过这段。我的理论是,一九七六年,当塑料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材料时,人类就失去了对美的直觉。如果你去对比一九七六年之前和之后的街头摄影作品,就可以看到切实变化。我知道我们应该对怀旧审美抱有警惕,但事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人们穿耐用的羊毛和棉布做的衣服,用玻璃瓶储存饮料,用纸包裹食物,屋里用的是结实的木质家具。现在我们的视觉环境中,绝大多数物件都由塑料构成,这是地球上最丑陋的物质,塑料上的颜色不是涂在表面的,而是从里到外渗出的,看起来丑得独树一帜。我允许政府做的事不多,其一就是禁止生产塑料,除非它对于维系人类生活迫切相关。你怎么想?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这个叫费利克斯的人遮遮掩掩。他是谁?你在和他上床吗?要是不想说也不用告诉我。西蒙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讲了。据说他和一个二十三岁的女人约会两个月了,我却从没见过她。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一想到西蒙——我十五岁时他就已经二十多岁了——现在在和一个小我六岁的女人定期做爱,我就想径直爬进我的坟墓。而且他身边的女人从来不是那种鼠棕色头发、对皮埃尔·布尔迪厄[5]有有趣见解的书呆子,她们从来都是那种有一万七千个粉丝的Instagram模特,从护肤品牌那里拿免费小样。艾丽丝,我不想假装认为年轻美女的虚荣既不无聊,也不令人尴尬。我比谁都虚荣。我不是在夸张,要是西蒙把这个女孩搞怀孕了,我会从窗口跳下去的。想想看,我后半辈子要对某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和善,就因为她是他孩子的母亲。我跟你说过他二月有天约我出去吗?他不是真的想跟我约会,我觉得他只是想让我自信一点。不过我们昨晚的确打了一通很有趣的电话……不说了,费利克斯多大?是那种会跟你写诗、讨论宇宙的神秘老男人,还是十九岁、牙齿洁白的乡村游泳冠军?
婚礼后的那周我可以过来看你——大概六月第一个周一到。你觉得如何?如果我会开车的话会容易得多,但好像坐火车然后打车就可以了。你想象不出没有你我一个人在都柏林晃荡有多无聊。真心希望能再在你身边。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