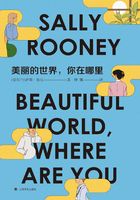
第10章
关于我之前邮件里提到的那个陌生人:费利克斯跟我们同岁,今年二十九。如果你好奇我和他睡过没有,答案是没有,不过我觉得这个事实无助于阐明我和他的关系。我们的确约会过一次,我当时也跟你说了,很失败,而自那以后我们之间没有进展。我猜你真正想问的不是我们有没有发生性行为,而是我和他的关系是否和性有关。我觉得有。但话说回来,我认为每段关系都是如此。我希望能读到优秀的性爱理论。现有的理论似乎大多和性别相关——可性本身呢?我是说,性究竟是什么?对我来说,以性的方式对待遇到的人是很正常的,我都不用实际和他们做爱——更准确地说,甚至不需要想象和他们做爱,甚至不需要去想象这种想象。这说明性爱有“他者”性,而这其实和性无关。或许我们绝大部分性爱经验都属于这种“他者”。那么他者究竟是什么?我是说,我对费利克斯的什么感受——顺便一提,他甚至都没碰过我——让我认为我们之间是性关系?
我对性思考得越多,困惑就越多,它在我眼中就越丰富,我们谈论性的方式也就越琐碎。如何与自身的性“和解”:它似乎意味着,弄明白你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对我来说,意识到我既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或许只是整个过程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到百分之一。我知道我是双性恋者,但我不觉得它是我的身份——我是说,我不认为我和其他双性恋者有什么特别相同的部分。至于我对自己性向认同的其他问题,它们似乎都更复杂,并且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许就算找到了答案,我也没有语言能表达它们。我们该如何确定自己享受哪种性,为什么?性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要获得多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自己的性爱人格能了解到自己的什么特质?这些东西对应的术语是什么?在我看来,我们随时都感受着这些强烈到不可思议的冲动和欲望,强烈到不惜毁掉自己的人生、婚姻和事业,可没人真的试图解释这些欲望是什么,来自哪里。和我们生活中令人精疲力竭、身心俱疲的性相比,我们思考和谈论性的方式,是如此局限。不过打完上述这段话后,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听起来有点疯癫,或许你的性欲远没有我强烈——或许没人有我这么强烈,我也不知道。没人会聊这些。
有时我认为人类的关系是柔软的,像沙或水,而我们将它们倒入某个特定容器,从而赋予了它们形状。因此,一个母亲和她女儿的关系被倒入一个名叫“母女”的容器中,这种关系便拥有了盛装它的容器的轮廓,被装在里面,无论是好是坏。或许有人做朋友不开心,但做姐妹的话就非常融洽,或者有的夫妻做父母和子女反而更好,谁知道呢。但去缔结一段没有事先规定形状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呢?就是把水倒出来,任它坠落。我想它不会有任何形状,而是四处流淌。我觉得这有点像我和费利克斯。我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路径通向任何可以前进的关系。我不觉得他会拿我当朋友,因为他有朋友,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与我之间的关系不同。比起和他们,他和我距离更远,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更接近,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受任何边界或习俗的制约。它如此非同寻常,原因不在他或我,也并非我们拥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特质,甚至无关我们独特的个性组合,而是我们发生关系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缺乏发生关系的方式。也许最终我们会退出彼此的生活,或者变成朋友,还是别的什么。但无论发生什么,至少是这场实验的结果,有时我觉得这个实验太糟糕了,有时又觉得我只想拥有这种关系。
赶紧补充一句,我们之间的友谊除外。不过我认为你对美的直觉的观点是错的。你说当柏林墙倒掉时,人类失去了对美的直觉。我就不跟你再讨论苏联问题了,苏联死去时,历史也死了。我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很长的问题,而最后我们给出了错误答案。我们在世界结束时出生,这是不是很不幸?自那以后,地球就没有了希望,我们也没有了希望。或许这只是一个文明的终结,我们这个文明的终结,在未来某个时刻,又会有别的文明出现。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就是站在最后一个亮灯的房间里,在黑暗降临前见证着某种东西。
我来提供另一种假设:对美的直觉依然存在,至少在罗马。你当然可以去梵蒂冈博物馆看拉奥孔的雕像,或者去那座小教堂,在小槽里投一枚硬币去看卡拉瓦乔[8]——博尔盖塞美术馆里甚至还有贝尼尼[9]的《被掳掠的普洛塞庇娜》[10]。费利克斯这位天生的感官主义者,宣称他特别喜欢这个雕塑。意大利还有芬芳扑鼻的深色橙树,小而白的咖啡杯,蓝色的午后,金色的黄昏……
我跟你说过我再也读不进去当代小说了吗?我想是因为我认识太多写当代小说的人了。他们在文学节上随处可见,喝着红酒,聊着纽约的哪家出版社在出谁的书。抱怨一些世上最无聊的事——宣传不够多,有负面评论,谁挣的钱更多。谁想听这些?然后他们跑去写那些多愁善感的关于“真实生活”的小说。事实是他们对真实生活一无所知。他们大多数人有几十年没有抬头看看真实的世界了。这些人自一九八三年起便坐在铺着白色棉麻桌布的桌子后面,抱怨负面书评。我真不在乎他们对普通生活或普通人有什么想法。就我个人而言,他们说话的立场是虚假的。他们为什么不去写他们真正的生活,那些真的让他们着迷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假装着迷于死亡、悲伤、法西斯主义——其实他们一门心思只顾着新书能不能被《纽约时报》点评。哦,顺带一提,他们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出身平凡。他们并不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儿女。问题是,他们脱离了平凡生活——或许他们出第一本书时还没有,是在他们出第三或第四本的时候,但无论如何,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当他们回过头去,试图回忆起普通生活是什么样的,却已经走远到只能眯起眼看了。如果小说家如实描写自己的生活,就没人会读小说了——而且也理应如此!或许那时我们终于能承认,当下的文学生产是错的,从哲学意义上大错特错——它把作家从平凡生活中带走,在身后关上门,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他们有多么特别,他们的观点是多么重要。然后他们在柏林接受了四场报纸采访,三场照片拍摄,两场票卖光了的活动,三场优哉游哉的晚宴,席间人人都在抱怨负面评论,周末结束后回到家中,然后打开旧MacBook,写一本充满对“真实人生”洞察的小说。我认真地说一句:这让我恶心。
当下欧美小说的问题在于,它凭借自身的整体稳固性来压迫地球上大多数人类的生活现实。要是把数百万不得不生活在贫穷困苦中的人,把他们的贫穷和困苦与小说“主人公”的生活并列在一起,小说就显得要么没有品位,要么是失败的艺术。简而言之,当周遭大多数人类正在面临不断加剧、愈发残忍的剥削时,谁还在乎小说主人公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分手了还是继续在一起?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还重要吗?所以小说通过抑制世界的真相而成立——它把真相紧紧地压在文字的光鲜表面之下。于是我们重新开始在乎,就像我们在真实生活中那样,在乎人们分手与否——但前提是并仅仅是,我们成功忘掉生活中比它更重要的事,也就是,一切。
毋庸赘言,我自己的作品是罪魁祸首。就凭这个我再也不会写小说了。
你在上一封邮件里心情很差,还说了些很病态的话,什么想为革命而死。我希望当你收到这封回信时,你想着的是为革命而活,以及这种人生是怎样的。你说没几个人关心你遭遇了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知道我们中有人非常、非常在乎——比如我、西蒙、你母亲。我还确定,被人深爱(你正被人深爱)好过被很多人喜欢(大概也有很多人喜欢你!不过我就不劳神论证了)。很抱歉跟你抱怨了这么多新书宣传的事,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想听这些——也很抱歉之前跟你说我会休息,结果又飞去罗马宣传新书,因为我很胆小,不想令人失望(抱歉我们没能在航班起飞前见面,不过那其实不是我的错——出版社为我订了去机场的车)。你说得没错,我赚了太多钱,生活得很不负责。我知道我肯定让你感到无聊了,但我对自己也一样感到无聊——我很爱你,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话说回来,婚礼结束后请一定过来看我。要不要也请西蒙过来?我们两个一起肯定可以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和比我们年轻的美女约会是错的。我也不完全确定这为什么是错的,但见面之前我一定能想出一些观点的。爱你,艾丽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