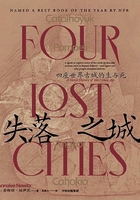
第一章
定居生活的冲击
我在土耳其中部有200万人口的繁忙都会科尼亚登上一辆空调大巴车,来到恰塔霍裕克这座世界古城。那天上午万里无云、十分炎热,大巴车就这样出了城,途经商店无数,从卖新鲜鸡蛋的到卖苹果电脑的一应俱全。当亮丽的公寓楼宇逐渐为旷野所取代时,我们并未远离文明。蜿蜒的路旁仍可见整齐的贝都因人营帐,而途经的小镇中几乎每条街上都有新房正在建造。约45分钟后,大巴车在一个碎石铺就的停车场停了下来。一幢幢长形矮建筑和小木屋围出了一处赏心悦目的院落,中间摆放着许多带遮阳伞的野餐桌。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休闲中心或小规模的学校。
其实这里是通往遥远过去的一扇门户。野餐桌数百米开外就是建于所有城市之先的城市——恰塔霍裕克城。这座城市大部分被掩埋在早已被风吹平的低矮高原——东山丘——之下。从空中鸟瞰,面积有13公顷的东山丘呈泪珠状,它就像一张土制的大毯子盖在了这座已有9 000年历史的城市遗址上,城市的居民长期以来在房子上面盖房子,泥砖建筑层层堆积,形成了一座城丘。东山丘的外面还有较新的西山丘,它规模略小,大约形成于8 500年前。建城之初城丘两侧均有河水流淌,附近的科尼亚平原上散布着许多农场。今天,这片土地已经干涸,只有一片片干黄的草散布其上。我吸进了一口带着尘土的暖空气。这里是所有城市的起点。我所认识的世界——公寓、工厂式农场、电脑遍布,而且(街道上)成千上万人摩肩接踵的城市——亦由是而生。
有的考古学家称恰塔霍裕克是由小居民点融合而成的“大型场址”或巨大聚落。这座城市似乎是在没有任何中央规划或指导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而成的。恰塔霍裕克的建筑和在该地区之后出现的各种建筑截然不同。每一家住房像蜂窝一样紧密相连,几乎没有街道分隔。城市网格起码比地面高一层楼,人行道沿屋顶排布,而各家的大门也开设在屋顶。居民们花在屋顶上的时间肯定少不了,他们在房顶上做饭、制作工具,还经常借助简易遮蔽物在户外睡觉。他们进城回家都靠简单的木梯上下。
最早的建筑工程开始时,许多来到恰塔霍裕克居住的人才刚刚脱离游牧生活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当时来说,在一个地方定居的想法极具革命性。虽然在恰塔霍裕克之前也出现过小村落,但绝大多数人还在延续他们旧石器时代祖先数十万年来一贯的小股流动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原来在自然世界与你共处的只有少量的人和动物,如今你却要同数百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定居,这该如何适应。只熟悉老旧游牧生活的父辈祖辈不可能教导你如何适应这奇怪复杂的城市生活。难怪恰塔霍裕克人一直想方设法寻找最好的群居方式——但在这过程中也犯了不少致命的错误。
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你的老家在哪儿”跟“你的祖上都是谁”这个问题一样重要。对一个总在流动的游牧民族来说,“你的老家在哪儿”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重要的是“你的祖上都是谁”,你是哪一族人。因此,很多西方的古籍,包括《圣经》,在介绍英雄人物时不免拉拉杂杂列出名单冗长的祖祖辈辈。你的列祖就是你最好的写照,但如果你在某个城市度过一生,那么那个地方可能比你的家族渊源更让你有认同感。
当人们来往于恰塔霍裕克成千上万个屋顶上的通道时,也就意味着他们走进了人类社会的新阶段。恰塔霍裕克人开启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一个身份与人的固定居住地绑定的未来;这块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成了土地的一部分。这就像经历一个慢动作的冲击波,震撼了好几代人。人类能否持续生存下去如今取决于气候是否宜于耕作,而死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因旱涝而到来。我们可以从这座古城的历史中看到,定居生活实属不易,人们险些就决定永远放弃城市生活。但我们的祖先最终没有这么做,而这是几千年以后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想弄清楚我们的祖先为何如此抉择。
与印第安纳·琼斯截然相反
我将注意力转回大巴车放我下来的地方,即恰塔霍裕克发掘所。25年来有数百位考古学家以此地为家,孜孜不倦地努力揭开这座古城的奥秘。我正赶上十几位考古学家开展的关于恰塔霍裕克的历史和宗教的研讨会。
我们一行人登上了东山丘的顶部,考古学家已经移除了山丘的北面表层,将城市网络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不同寻常的发掘面,亦即被人们简称为“4040”的地方,约有现代城市一个街区的大小。4040上方有一个用木头和不透明白色塑料搭建的像飞机库那样的拱形遮阳棚,遮盖住了整个东山丘。人一旦步入棚内,炙热的阳光即刻变得柔和,空气也变得凉爽了不少。我眼前是一片黄褐色泥砖砌成的相互连接的好几百个房间。
起码有十几位考古学家正在这里面工作,有的蹲在墙边在本子上记笔记,有的用相机记录着上午的发现。为支撑断壁残垣,到处都堆放着沙袋。我们这群人站在房屋地面上方约1米处,向下望是9 000年前某一人家的起居室。我可以看到厚厚的泥墙中显露出的一团团灰泥,这让我想到在自己家百年老宅的木门框上刮下6层不同颜色的油漆的景象。有一些地方,居民用赭色土绘制的图案仍然清晰可见,在光洁的灰泥上呈之字形。一个是钻石形螺纹的重复图案,另一个是波动在曲线之间的一些小长方形图案,似乎是想表达河流的形象。所有的图案都是精巧的抽象图案,传达出一种动感,绘画者们似乎是想让这个缺乏变化的居住区获得生命力。
在发掘区我们看到了地面上有许多椭圆形小坑:这是坟墓内的骨头被移除的明显迹象。恰塔霍裕克人将逝者埋在泥塑的床台下面,就在自己身边。人体在下葬时呈胎儿蜷缩状,其棺木形状像一个圆形的容器,有异于西方人所熟悉的长形棺木。有的床台下面有多个古墓,最多的竟有6个之多。后来我们听说,有一座墓有多个颅骨却只有一副身体骨架。
团队的领队是斯坦福大学考古学家伊恩·霍德,这位谈吐温文尔雅的伦敦人自1993年就开始指导恰塔霍裕克发掘工作。此人的形象基本上与好莱坞影片中的探险家印第安纳·琼斯截然相反。他因开启了颇具影响力的脉络考古学派 先河而闻名,该学派认为古文物应该被视为了解古老文化的钥匙,而不是战利品。如果《夺宝奇兵》系列影片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是脉络考古学家,那么他就会把金色神像留在神殿里,并设法了解金色神像与这座设有各种奇妙机关的神庙的建造者们的信仰有无关联。当霍德在恰塔霍裕克发现无价之宝时——他知道不少这类发现——他总想探知该文物能告诉我们关于这座古城社会关系的哪些信息。
先河而闻名,该学派认为古文物应该被视为了解古老文化的钥匙,而不是战利品。如果《夺宝奇兵》系列影片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是脉络考古学家,那么他就会把金色神像留在神殿里,并设法了解金色神像与这座设有各种奇妙机关的神庙的建造者们的信仰有无关联。当霍德在恰塔霍裕克发现无价之宝时——他知道不少这类发现——他总想探知该文物能告诉我们关于这座古城社会关系的哪些信息。
霍德摘下他的帆布软帽,爬进了一个切入房子地面的方形深坑。坑的一边是考古学家所称的剖面,展露出恰塔霍裕克人在几个世纪间在这里的房子上盖房子后留下的多重土层。最底层是年代最久远的地面,随后每上一层年代就离我们更近,所以才有人不清楚考古学家谈到“更上面”时,其实讲的是“年代更近”的意思。另外一个描述这一分析方法的名词是“地层学”,亦即借助历史背景来研究土层。霍德指着夹在浅褐色黏土层中的缓波形走向的黑色物质,黑色物质上又覆盖着一层似乎掺和着碎骨的东西。它就像一块讲究的维也纳千层糕,只是这块土制蛋糕有3米高。霍德说,我们眼前所见正是这座城市数百年间房屋的情况。之所以有褐色黏土层,是因为恰塔霍裕克人勤于维护住房地面,经常给它们涂灰泥。黑色层则是住房被弃置后留下的灰烬。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通过焚烧屋内物件的仪式将被废置的房屋“封存”起来,所以才会留下容易分辨的炭化物质。有时候,房子就此变成了垃圾坑,邻居们会将自家火炉中的灰烬和其他废弃物也倾倒在这里。
最终又会有另外一家人在此重建住房,他们会在留有灰烬的地面上再涂上厚厚的一层黏土和灰泥,并按旧建筑的原布局重建。霍德用“依样画葫芦”一词来形容恰塔霍裕克人的造房法——居民们并不觉得有改变建筑风格的必要。有一次,霍德和他的同事挖掘到一所重建了4次的房子,房中储存锅具和埋葬死者的地方从来没有变过。
在他向我们展示的房子的上层土层里,霍德认出了夹杂在灰烬中的3段黏土层,这3段黏土层清楚地反映了房屋被弃置而后重建的不同阶段。下面的土层相对模糊些,但是我们还是辨认出了至少8层黏土和填充土。霍德猜想它们或许代表更早期的许多住房,或者是数目较少但在使用期间曾被人花大功夫修整过地面的住房。无论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今城市中依然存在的一种现象的古老版本。恰塔霍裕克人在旧房子上建造新房,我不也在我那间百年老宅上重修墙面、重建墙体、重涂油漆吗。
离开4040工棚后,霍德带领着我们经由山丘顶部往西南方向走去,前往一个年代更为久远的被称为“南发掘处”的地方。沿路我们看到了好几个支撑在几个小发掘点上方的帆布帐篷,我想象着当年恰塔霍裕克居民沿着一样的路线,从屋顶穿过城市的景象。目前发掘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只占古城面积的5%。在我们脚下的是1 000多年来层层叠叠、数以千计的住房,这些宝藏仍有待与世人相见。
“南发掘处”令人叹为观止。在用钢材和玻璃纤维搭建的穹盖下,我们看到考古学家已经往下挖了起码10米,发现了更久远的城市网格。我站在一个木制的观景台上凝视着令人咂舌的层层堆叠的土层。位居最下的也就是人们开始决定不再四处游牧、全年定居于此的最早期的城市。当时这里是一片草木繁茂的湿地。定居的人在开始建设这里之前并没有“城市”的概念。他们不断地在湿地上面按需求加建,直到黏土堆变成土房,土房变成上层屋顶的土路、街区和艺术品。似乎我们一眼即可将1 500多年的城市历史尽收眼底。
霍德指着坑中最深处挂着旗子的一根钢筋,带着些许神秘的微笑说:“那是乳制品作坊所在之处。”就是在这一层,科学家发现了恰塔霍裕克人烹调乳制品的第一个证据。陶罐中的残渣表明人们已经开始在汤里放羊奶,可能还放了奶酪。研究新石器时代牧羊情况的玛丽亚·萨尼亚、卡洛斯·托内罗和米格尔·莫里斯发现了多代人养殖少量羊群的证据 ,羊可以为人们提供羊奶和羊肉。这条乳制品线不仅让人们的饮食变得更丰富,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牲畜的生活方式以及定居点四周的土地。从“乳制品作坊”中,我们能看到人们已经停止在大自然中寻找栖息地,并开始改变自然使其为己所用的蛛丝马迹。
,羊可以为人们提供羊奶和羊肉。这条乳制品线不仅让人们的饮食变得更丰富,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牲畜的生活方式以及定居点四周的土地。从“乳制品作坊”中,我们能看到人们已经停止在大自然中寻找栖息地,并开始改变自然使其为己所用的蛛丝马迹。
人类如何自我驯化
1923年,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的《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问世,他在书中首次谈到城市生活的演化进程。柴尔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革命改变人类文明思想的影响,创造出“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词,用于描述在恰塔霍裕克有人居住期间逐渐呈现出的一系列发展。他说,就像工业革命的远古版,所有社会在采用农耕方式、产生符号交流、进行长途贸易和建造高密度居住点时必定会经历一段深刻、迅速的变革。他解释说,这一套新石器时代的做法迅速席卷了中东,接着延伸至世界各地,城市化应运而生。
数十年来,人类学的学生大都熟读“新石器时代革命”说,相信游牧民族变成交税的城市居民必然经历了极为突然的文化断裂。虽然过去有不少学者相信这种论点,但今天的考古学家从他们在恰塔霍裕克等新石器时代社会搜集到的新证据中发现,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我们已经了解到,从游牧生活到大型城市社会的过渡是一个渐进过程,数千年来不断走走停停。另外,它也不是从中东开始向外延伸的,被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是在多地——从东南亚到美洲——同时独立出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和居住安排无疑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走向。过渡有时确实突兀,特别是对那些刚刚离开旧的生活方式的人来说。不过,工业革命并不是对我们在恰塔霍裕克所窥见的社会变革的最佳比喻。20世纪初,一代人见证了电力、电话和汽车的普遍使用。但在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花了几十代人的时间来发展农业,又花了几十代人的时间才发展出乳制品作坊。虽然步调十分缓慢,但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还是设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周围的世界,就像他们遥远的后代适应了化石燃料和有碳排放的引擎那样。
到恰塔霍裕克这座城市建立起来的时候,人类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印记,人们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畜养山羊、绵羊、狗等牲畜,栽培果树,种植多个品种的小麦、大麦以及其他作物。 与此同时,我们也引来了意想不到的老鼠、乌鸦和象鼻虫等有害生物,外加在居住密集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人传人、动物传人并会带来疫病的微生物。人类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的食物、排泄物、身体和住房招来了各式各样的有益生物和有害生物。
与此同时,我们也引来了意想不到的老鼠、乌鸦和象鼻虫等有害生物,外加在居住密集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人传人、动物传人并会带来疫病的微生物。人类的生态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我们的食物、排泄物、身体和住房招来了各式各样的有益生物和有害生物。
人类改变了进入我们定居点生态系统中的每一种生物。我们栽培能更快食用、养活更多人的植物,这才有了长出更大麦粒儿的小麦和果肉更饱满的水果。像狗、绵羊、山羊和猪等家养动物经过几千年的驯化也改变了习性。或许,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让它们越来越像幼崽,也就是“幼态持续”现象。家养动物往往体型较小,外貌特征也比较柔和,诸如耷拉的耳朵、短鼻等。还有些更突出的变化,如家养的猪多出一对肋骨。人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也驯化了自己。
多代的定居生活、摄入各种各样的软性熟食,也在我们人类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记。“幼态持续”让人的面容更加精致,体毛也变少了。我们的下巴变得更短、更圆,或许因此让新的声音得以进入我们的语言系统。 更具体地说,我们只有移动上下颌骨、上齿轻触下唇才能发出“v”音和“f”音。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有了农业以后人们开始食用新鲜谷物糊和炖煮菜肴。
更具体地说,我们只有移动上下颌骨、上齿轻触下唇才能发出“v”音和“f”音。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因为有了农业以后人们开始食用新鲜谷物糊和炖煮菜肴。
新的食物种类使得大量人口在基因层面出现了“幼态持续”现象。所有孩子与生俱来就有消化乳糖——生奶中的一种糖——的能力。在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变得乳糖不耐受,喝了奶或吃了奶酪后胃就极度不适。然而,一旦乳制品在西方成为人类膳食的一部分,成人耐受乳糖的基因突变很快就在人口中蔓延开来。这一基因改变发生得非常突然,覆盖面也广,完全是由我们向定居生活转变导致的。在城市这种人为生态系统中,没有一成不变的生命体,智人也不例外。
深知野生动物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区别的恰塔霍裕克人一定也能看到这种转变。土耳其科奇大学研究城市食物的考古学家拉娜·奥斯瓦尔告诉我,恰塔霍裕克人喜欢用自家种植的植物、自家圈养的可食用的动物制作的饭菜。根据她对储物罐、烹调锅具和垃圾坑内残留物的化学分析结果,我们得知当时人们的食物包括奶、谷物和羊肉等。只有在特殊场合,如举办大型宴会时,人们才会吃野牛之类的野生动物。驯化似乎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人们喜爱摄入用被驯化了的动植物制作的食物,我们的身体因此发生了转变,渐渐地,我们的身体也更适合摄入这种食物,我们也就更愿意种植植物、圈养动物了。
驯化改变的还不只是人的生理,它与新的符号结构的出现也有关联。霍德说他们在恰塔霍裕克许多房子的泥墙上发现了人们刻意镶嵌于其中的鼬鼠和狐狸的牙齿、熊的爪子和野猪的下颌。他们还常常在野牛头骨上抹一层厚厚的灰泥——将牛角裸露在外——并将它们悬挂在门边。很多人在家中还把这些头骨叠加在柱子上,使其看上去就像是用牛角构成的脊肋。野生动物在绘画中也充当要角,我们发现了花豹、野牛和鸟类的图像。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林恩·梅斯克尔指出,恰塔霍裕克最常见的泥塑形象不是人类而是动物 ;恰塔霍裕克出土的数百件泥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人或人体部位的形象。
;恰塔霍裕克出土的数百件泥塑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人或人体部位的形象。
为什么那时的居民在一个如此喜欢驯化的社会中却对他们拼命想摆脱的野蛮世界如此情有独钟呢?虽然城市中的人已经被驯化,但他们距离被动物围绕的游牧生活——那种随时狩猎动物或者成为其猎物的生活——也仅有几步之遥。霍德推测当时城市居民对野生动物仍然心存敬畏,所以他们才会用动物形象来彰显权力。 霍德特别喜欢的一幅壁画里展现的是两只对立的花豹,它们没有对望,而是目露凶光、无情地凝视着观画的人。还有一幅壁画画的是一只似乎擒着人头的巨大秃鹫振翅飞翔。在恰塔霍裕克人绘制的狩猎场景中,公牛和野猪被放大,线条化的人益发显得渺小。在恰塔霍裕克人的心目中,野生动物的形象是挥之不去的,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确实如此。
霍德特别喜欢的一幅壁画里展现的是两只对立的花豹,它们没有对望,而是目露凶光、无情地凝视着观画的人。还有一幅壁画画的是一只似乎擒着人头的巨大秃鹫振翅飞翔。在恰塔霍裕克人绘制的狩猎场景中,公牛和野猪被放大,线条化的人益发显得渺小。在恰塔霍裕克人的心目中,野生动物的形象是挥之不去的,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确实如此。
不过,绘画中的人物也并不总是与野生动物对立。恰塔霍裕克的艺术家们最喜欢的绘画主题是“兽人”,即兽与人的混合体。有一幅画里面的秃鹫就长着一双人腿。许多狩猎或挑衅公牛的人身上都有花豹的豹斑。考古学家还发现鼬鼠及其他捕食动物的粪便被故意放置在人的坟墓中,似乎是当时的人们有意把危险动物的“秽物”与坟墓里的土混在一起。或许这是人类宣称自身有象征性权力的一个方式,表明他们像花豹一样迅猛,像秃鹫一样凶残,像鼬鼠一样嗜血。霍德说,人们或许把野生动物当作自己过去孔武有力的远祖,与它们有这层关系就能赋予他们相对于后来人来说的权威。换言之,兽人可能是政治姿态的早期表现,自己就因为比人多出那么一点点就有权驾驭他人。
又或许,当时的人们画野生动物壁画是为了提醒当时的城市居民不要忘记他们的先祖曾经住在简易蜗居或帐篷里,对来袭的野牛全无反击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野生动物图样要反映的就是人类的弱点。过去不堪一击的墙体如今已异常坚固,足以抵御捕食者。旷野离他们并不远,那些野生动物还在等待机会伸出爪子扑来。(荷兰)RAAP考古顾问公司的马克·费尔赫芬把恰塔霍裕克的墙体解释为“躲藏和显露”的地方——它们把未驯化的世界请了进来,却又用灰泥将这个世界遮盖起来。说到底,居家生活并不意味着将自然拒之于门外。其实居家生活更像是一种过滤,允许某些生物进来,对其他生物则敬而远之。被驯化后的动植物可以与人类一起居住在屋内,旷野则以墙为限。恰塔霍裕克的城市设计反映了一个对驯化后的生活并不太适应的社会。老百姓仍未完全放弃野性的过去,因为那给了他们力量,但又想对这段过去加以限制,与之保持距离。
这座老城的居民还想与另一样东西保持距离:他们的邻居。在这方面,住在伊斯坦布尔闪亮的高楼中的人倒是与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先人想到一块儿去了。由于要长期与他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朝夕相处,恰塔霍裕克人想方设法在与邻居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仅隔60厘米泥砖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私密性。人类学家彼得·J.威尔逊在《人类的驯化》一书中写道:像恰塔霍裕克这样的城市的出现正值私密性概念的萌芽时期。 游牧时代的人没有多少独处时间。空间大家共有,房舍可以折叠带走,与他人之间仅有帘幕遮挡并没有真正隔断。当然,愿意离群索居的人的绝对私密性是有保障的。如果两伙人冲突严重、水火不容,那么他们不需要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各过各的。
游牧时代的人没有多少独处时间。空间大家共有,房舍可以折叠带走,与他人之间仅有帘幕遮挡并没有真正隔断。当然,愿意离群索居的人的绝对私密性是有保障的。如果两伙人冲突严重、水火不容,那么他们不需要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各过各的。
恰塔霍裕克把这一套社会模式来了个大颠倒。人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埋头过自己的日子,他做什么邻居完全看不到。不过,有了永久住所后人们开始累积大量属于自己的东西,再离开群体就变得极度困难了。其结果是进入各自住房的门口就变成了充满社会和神秘力量的界限。威尔逊写道:别人要进屋,得先请主人家“对邻居展示某件自己私人所有的物件”。 城市社会到处可见紧闭的房门和隐藏的房间,使得人们在彼此交往时仍然不会将自己完全暴露。直到发明了城市,人们才想到远离他人的独处需要,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事。换一种说法就是,私密性概念出现时公有概念才相伴而生。
城市社会到处可见紧闭的房门和隐藏的房间,使得人们在彼此交往时仍然不会将自己完全暴露。直到发明了城市,人们才想到远离他人的独处需要,这也是颇耐人寻味的事。换一种说法就是,私密性概念出现时公有概念才相伴而生。
回到恰塔霍裕克“南发掘处”的大棚下,我望着下面层层深入的城市:墙上筑墙,地面上铺地面,顺着这巨型的阶梯越往下,我们回到的时光就越久远。我意识到这座城不只是一个物理建筑。居民在建造房屋的同时也给自己添加了一层新身份。自己在家里做的事别人完全不知道。当然,隔墙有耳,流言蜚语也有传播网络,但这里的人却有一种新奇的感受,那就是虽然别人就在周围,他们却仍然可以我行我素。打开大门走出去等于是换了一副对外面孔,在行为举止方面对自我的要求自然与在家里的大不相同。公共区域在上方,在房顶的过道上,私人世界则在下面的夯土面上。而在所有这些之下的则是被埋葬的祖先和祭祀物件,那里既非私人空间亦非公共空间。总之,我们可以通过人们的住房来思考社会关系。
人们在一块土地上居住的时间越久,这块土地就越会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或许可以说,“我是纽约人”“我来自大草原”之类的说法的最早情感起源即来自这里。这些话只有在你把自我与这块土地捆绑在一起时才有意义。霍德和其他考古学家把这种思想方式称为“物质纠缠”,即意味着我们的身份已经与我们四周的实体物件密不可分了。这些物件可以是祭祀用的兵器,也可以是我们亲爱的人赠予我们的礼物,或我们出生的山丘等。在恰塔霍裕克,出于精神方面的和实用的理由,最显而易见的“物质纠缠”的场所就是住房:房屋的墙壁上展现着富有野性的魔力,地面下隐藏着震撼人心的历史,不需要任何人走出畜群和这块安全、被驯化的农场,储物间里就有足够供家人享用的粮食。
远在我们开始全天住进房屋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构建住房的能力,所以并不是因为有了技术突破才使得我们有了新的思考方式。实际情况或许正与此相反。随着社会日趋复杂,我们需要用更持久的东西来思考自己。
声明自己拥有土地
柏林自由大学考古学家玛丽昂·本茨在她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她对我说,定居生活带来的文化冲击即便是在人类文明的今天依然未曾停歇。为了应对或表达这种冲击,人们修建了有纪念意义的建筑,在普普通通的土地上打造出一片奇幻景观。石碑、金字塔、庙塔,甚至连今天的超级摩天大楼,表达的都是将人与某一具体、特殊地点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的冲动。
本茨还说,每当我们改变社区建筑的模式时,亦即在进入新的人类文明转折点时,往往能看到纪念碑型建筑的爆发式出现。在恰塔霍裕克成为城市之前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可以从那时的建筑中看到这种现象。大概在1.2万年前,半游牧民族就在一座高原的顶部建造了一处了不起的建筑,亦即今人熟知的哥贝克力巨石阵。该遗址位于恰塔霍裕克以东约600千米处,由200多根T形石柱组成,有的石柱高达5.5米。这个巨石阵与史前时期的巨石阵有几分类似,不过要讲究得多。石柱上满是危险或有毒的野生动物的浮雕。
从宴饮和扎营残留的废弃物来看,这里曾经有人居住,它可能是西方首批人类居住区之一。但这里并不像恰塔霍裕克那样常年有人居住。到访者必须走过一道狭长山径才能抵达此处,他们可能会在石柱旁边扎营。从附近采石区开采而来的这些石柱矗立在一系列层层围起的圆形围墙内,沿着墙体有一条蜿蜒小道,一直延伸到有许多石凳和两根最高石柱的中心区。这处建筑或许原来有屋顶,营造出一座黑暗的迷宫,火把照在石柱的浮雕上时,动物形象在变化的光影下更显得栩栩如生。考古学家在该地还发现了经过雕刻绘制的人的头盖骨,上面还钻有许多小孔,经皮绳穿串即可悬挂在石柱上。
雄伟壮观的哥贝克力巨石阵数千年来不断吸引着人们前来,为其添砖加瓦并在此举行祭祀仪式和宴饮。21世纪领导该地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认为,巨石阵是敬拜逝者的庙宇原型。 然而,对本茨来说,建造哥贝克力巨石阵的具体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在自己开始定居生活的时候就修筑了这座具有持久性的雄伟建筑。本茨认为,这就是人类声明自己拥有这块土地的方式,将人类社区与地方挂钩,而不是与人群挂钩。
然而,对本茨来说,建造哥贝克力巨石阵的具体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在自己开始定居生活的时候就修筑了这座具有持久性的雄伟建筑。本茨认为,这就是人类声明自己拥有这块土地的方式,将人类社区与地方挂钩,而不是与人群挂钩。
不过,这也是当时的人们应对社会危机的一种处理方式。在人们离开游牧群体形成农耕社会时,人口随之激增。突然间,周围的人就不仅仅是你熟悉的大家庭成员的面孔了。在一个200人的村落里,或者一个几千人居住的城市里,你可能连邻居都不认识。人们仅靠与其他人的关系是无法建立归属感的。“(他们)需要巨型的不朽艺术品来凝聚人心,并不断提醒人们他们的集体认同感。”本茨对我这么说。或许可以说从前人们认同的是彼此,如今却是认同一个特定、共有的地点。不论是从实际上还是从感情上来说,原来游牧部落所起的作用都已被象征性建筑所取代。
哥贝克力巨石阵建成后2 000年,人们开始在恰塔霍裕克定居,此时人们对自己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在此前的2 000年中,中东各地已经出现了定居点,农耕生活所带来的冲击已逐渐淡化。通过这段时间动物在艺术中的表达方式,本茨追踪了这种变化。哥贝克力巨石阵和同期的雕塑中有人物,但这些人物“往往被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围在中间”。艺术家勾勒的世界既有人也有野生动物,两者对等。在哥贝克力,动物甚至偶尔有凌驾于人物之上的趋势。有的T字形石柱有手臂,下身还雕刻有缠腰布,它们没有脸,上身满是动物和抽象的图案。可是在恰塔霍裕克被发现的壁画中,动物四周却是手持武器的人物。“我们看到一群狩猎者……一起成功猎杀了一头野生动物。”她解释道。从这一转变中本茨观察到“大幅度的观念改变”。哥贝克力时代的人们还在试图巩固旷野中的新社会,而恰塔霍裕克人却已是有数千人之众的“基础牢固、充满自信的社区”的一部分了。
哥贝克力巨石阵中那些不朽的野生动物浮雕和绘制的头盖骨在恰塔霍裕克人的住房里也有展示,只是规模小些。在城里,它们就变成了与火炉和住家有关的私人、家用物件。这个迹象或许能够说明恰塔霍裕克人已经没有了对某单一地点建立认同感的迫切需要。城市里的居民与他们物质环境之间的纠缠,已经深到这样的地步:走过几个街区,脚下的一切无一不出于人类之手。恰塔霍裕克人对人可以改变环境这一点已经没有质疑,并且能够在远胜于游牧时代所见过的建筑内蓬勃发展。本茨猜想,也许这就是恰塔霍裕克的建筑如此“平庸无奇”的原因。我们看不见别致出众的住房或高耸的石碑。只有城市本身一望无际,数以千计的住房紧密相连,四周是随着代代相传不断扩大的精耕细作的农田。恰塔霍裕克就是一个过渡,是步入城市未来的门户,也是纪念野性、游牧的过去的一座丰碑。
走向抽象
随着恰塔霍裕克的逐渐成熟,居民们在城内信得过的人——与他们信念相同或掌握同样手艺的人——之间建立社交关系,以适应这个超大型社会。因为恰塔霍裕克的人口数以千计,城市又大,城市网络中不免有陌生人,所以人们需要用快捷、便利的办法表明身份,彰显归属。因此,恰塔霍裕克和附近居住点的居民常常携带被考古学家称为图章的泥质标志物。图章的大小通常与名片相当,其中一面刻有图像。有证据表明,有人将图章随身佩戴,也有人拿它与人交换。除此之外,有人还真的发挥了图章的作用,将其沾上漆后盖在纺织物上或在软泥上打上印记。
早期的图章上布满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石器时代的图像:秃鹫、花豹、野牛和蛇等野生动物。还有一些图章展现的是住房图像,有时是三角顶的双层住房等图案。中东技术大学考古学家西格登·阿塔库曼在中东各地研究图章,他认为这些图章就像房屋的便携版本,是把人与地方或群体联系在一起的象征物。某一户人家或某一个村落的人可能都带有同样的图章。新成年的人在成年礼上可能也会被授予表明其新身份的特殊图章。图章也可以用来表明你是哪里的农民,是不是萨满教巫师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图章的用途我们并不是全都知道,但我们在附近的所有居民点都曾发现过图章,有的甚至出现在制作地点几百千米开外。它们把定居生活的象征符号又带回到了路上。
历经数百年,图章设计益发抽象。阿塔库曼特别谈到了阳具图案的演变。在恰塔霍裕克、哥贝克力巨石阵和其他无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野生动物画像里,经常出现勃起的阳具。恰塔霍裕克人狩猎动物的壁画里,公牛和野猪的阳具也经常呈勃起状。哥贝克力巨石阵的石柱上还刻有没有附着躯干或者与模糊的人身相连的勃起的阳具。恰塔霍裕克遗址出土的一些小雕像似乎也是没有躯干的阳具,图章上也一样。这种现象引起了考古学家的热烈辩论。它们代表的是男性权力?是生育?是激情和暴力?在探讨其他城市的阳具图案时我们会发现,阳具并不一定只是阴茎,它是不一定与性和性别有关的许多东西的象征符号。图章上阳具图案的变迁讲述的正是一个进入新阶段社会的人类的故事。
阿塔库曼解释说,图章上的阳具最后变得越来越抽象:早期图章清楚显示的是两个睾丸上的直立阳具,几十年以后图章上的图形就变成了圆圈上一个凸起的球状物,再过几百年又变成一个简单的三角形。这一度代表阳具的三角形后来又出现在对住房的抽象表现中。人类学家珍妮特·卡斯顿曾表示,早先的城市居民在人体和房屋之间看到一种精神联系 ,人体某一部分最终体现在住房上从象征角度来看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创造出的象征符号越来越抽象。
,人体某一部分最终体现在住房上从象征角度来看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创造出的象征符号越来越抽象。 阿塔库曼认为,这表示人们因频繁使用符号表意,于是发展出了简略版。人们可以从与它此前代表的东西完全不相像的图案中辨别出它的意思。
阿塔库曼认为,这表示人们因频繁使用符号表意,于是发展出了简略版。人们可以从与它此前代表的东西完全不相像的图案中辨别出它的意思。
没有证据显示恰塔霍裕克人发明了文字,但从他们的图章来看,文字已呼之欲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字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新石器时代阳具图章抽象化过程的延续。人们通过一层层的抽象图案来表明自己的身份。用三角形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个图形最先来自阳具。它只不过是象征与某一地点相关的屋顶形状。或者,它被刻在一个更大的独特符号当中,借以表明图章持有人的身份,有时也透露出他的老家、他的行业的有关信息,或者表明他已经成年。
在恰塔霍裕克的人口从几百人增至几千人时,人们要习惯的就不只是驯化这一件事了。他们生活在某种特定的人类文化环境中,大家的血缘关系、技能和信仰都极为复杂多样。在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的身份可能由居住在某地的家族来界定。但恰塔霍裕克人可能都是显赫的共同先祖之后,其祖先用某种动物表示;同屋居住的人不一定都有血缘关系;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大部分时间在打造石具,其他人则从田地里拿食材回来烹调。身份既可以被替代,又可能会出现交叉情况。也难怪城市居民要佩戴图章表明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恰塔霍裕克又出现了更复杂的符号图案。我在发掘工作现场时,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人类学家彼得·毕尔曾表示,对房子一再重建或许是迈向有历史概念的第一步。他猜想,恰塔霍裕克人可能是古老文明中最先超越记忆开始有历史思考的人。他说,历史是超越一个人有生之年的“记忆的外化”。或许对土地有强烈归属感的人最可能会产生这种认知框架。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奥弗·巴尔-约瑟夫表示,毕尔的观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宇宙学的诞生,在他看来,这门学问是从还要早几千年、充满象征符号的远古旧石器穴居时代开始逐渐出现的。恰塔霍裕克人之所以把他们的城市与骨头串联在一起,或许就是想标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神灵居所。巴尔-约瑟夫还认为,我们或许无法分清新石器时代中历史与宇宙学之间的关系。两者都是在更大范畴内解释人类关系的抽象概念。我们必须设想新石器时代的城市文化并未对过去与神灵世界之间、奇幻与科学之间进行清楚的区分。
霍德认为,城市的开始与终结都伴随着许多人赋予自己的住房“越来越多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这些微不足道的行为。恰塔霍裕克的城市化并非出自任何王公贵族的宏伟蓝图,它其实是住房不断向外延伸的结果,人们在这里发展了工艺、工具和符号体系,这一切使得城市尽管有许多缺点,仍然相当有吸引力。霍德写道:“是散布于日常生活中的微不足道的行为产生了了不起的结果。” 他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震撼人心的城市乃起源于稀松平常的居家生活。城市的社会关系,以及关于社区、历史、我们与野性的过去的精神联系等新概念亦由居家生活而生。
他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震撼人心的城市乃起源于稀松平常的居家生活。城市的社会关系,以及关于社区、历史、我们与野性的过去的精神联系等新概念亦由居家生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