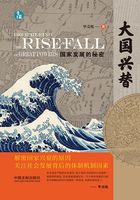
为什么能源革命发生在英国?
17世纪50年代起,煤炭开始成为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第一大能源,到18世纪初,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已经接近一半。煤炭作为化石能源,属于一种现代能源,区别于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传统能源(有机能源)。煤炭较传统能源的功效更高,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因而由使用传统能源到使用现代能源,这场能源结构上的转变影响深远,触发了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也在这个基础上得以运转。这场变革率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值得探究。
一、能源禀赋
彭慕兰的《大分流》[1]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源于两个“偶然”事件,一是煤炭在英国的广泛分布和利用,二是英国大量的殖民地。彭慕兰所列的第一个原因即能源禀赋,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第三大煤炭资源国,历史上很早就开始使用煤炭。河南郑州古荥镇冶铁遗址的挖掘发现,当地从西汉中叶至东汉前期就开始以煤为动力冶铁。南北朝时,我国北方家庭已经广泛使用煤取暖、烧饭;唐朝时,我国南方也开始广泛使用煤;宋朝时,煤炭在京都汴梁已是家用燃料。但是这些并没有引发中国的能源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也有限。世界上其他的能源储量大国,比如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国家等,也都没有率先发生能源革命。
尽管李伯重认为,虽然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但是中国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煤炭资源稀少。[2]但莱特的研究表明,中国江南地区并不缺少煤炭资源。[3]至少在当时的能源需求水平下,中国江南的煤炭资源并不稀缺,而地处江南的安徽省至今仍是中国的煤炭主产地之一。
中英之间在煤炭资源禀赋上的差别不是关键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煤炭资源比英国更丰富。没有一定的煤炭储量,在17世纪的情况下,英国是不可能发生能源革命的。但是能源禀赋是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能源禀赋状况并非影响现代能源革命的关键性因素。
二、能源需求——人口增长
能源需求无疑会倒逼能源结构转型,而在能源需求中,人口的大量增长是一个主要因素。[4]但是对比英国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情况,会发现人口增长也并非中英发展异途的原因。
由于逃避税赋、服役等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官方人口统计存在较大的误差,目前修正后的研究基本认为,中国自宋代开始人口数量迈入“亿”的门槛,但是人口增长一直处于平稳状态,自清中期才超过2亿人。[5]与中国的情况类似,英国人口增长率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也没有较大变动。
表1 中国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变动

续表


图1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表2 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变动

续表


图2 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史上的人口年均增长率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并非英国能源革命的推动因素,因为英国在能源革命发生前并没有人口的爆发式增长。相反,能源革命与工业革命一起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从18世纪后期起,英国人口出现了较快增长的趋势。中国由于在同期没有发生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人口增长一直不明显。可见,人口增长是结果,而非原因。
三、能源需求——人口结构
人口增长情况未能说明英国能源革命的原因,并非可以完全否定人口因素对于能源结构的影响。在早期现代,人口结构因素对于能源结构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农业社会,一个人吃、穿、住、行所需的能源并不多。但是城市化后,需要建更多的房屋、更多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对能源需求的拉动巨大,这些都制造了大量的能源需求。在人口结构的演变上,恰好可以看出中英发展的差异。
城市化率是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反映城市发展程度、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关于中国古代人口的数据,不同研究的差别较大,本文采用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的数据。中国在北宋时就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汴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万人左右。[6]但实际上有宋一代的总体城市化率并不高,在10%左右,就全南宋地域而言,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12%。[7]宋之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没有发展,反而不断下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7270万左右的人口中,大约有6650万民籍人口,620万军卫人口(包括军人及其家属),大约有633万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占民籍人口总数的9.7%。由于都城北迁,明代之后的城市化水平很难超过明代初年。[8]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中国城市人口总数为2273.4万,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3%。虽然城市人口大大增加,但是城市化率却较明代下降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率不仅没有明显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图3 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率
数据来源: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部出齐。
相比而言,英国在能源革命发生前,城市化率处于持续增长中。从1520年开始,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在上升。1520年时,英格兰的城市化率仅为5.25%,到了1800年,城市化率增长到27.75%,如图4所示。

图4 英国人口结构,1520-1800年
数据来源:E.A.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61, Tab 3.2.
城市化的发展,意味着要用更少的农民去养活更多的人。在传统能源模式下,农业不仅提供人们基本的衣食,还提供基本的能源——生物质能。在城市化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农业还要承担基本能源提供者的角色,土地和农业从业者必定不堪重负,尤其是英国本来就面临着耕地的劳动力相对短缺。根据赵冈的研究,古代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小于英国,反过来也可以说,英国的亩均劳动力远远小于中国。英国的庄园制度时期,农奴从领主手中得到的分地,普通是30英亩大小,多者能达到80英亩。在中国,以汉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与耕地总数来说,每人平均只有1.6英亩,平均五口之家的农户只有8英亩耕地。中国自从有信史以来,每户的平均耕地始终在30英亩以下,而且总的趋势是平均耕地愈来愈小。[9]
英国的城市化倒逼了能源结构转型。从17世纪50年代起,煤炭在英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图5)。对比表4,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比重的增长因应英国城市化率的增长,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初,城市化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煤炭的消费比重就会平均增长2.8个百分点。
表3 英国能源结构(英格兰和威尔士),1560s-1850s(单位:千万亿焦耳)


图5 英国能源结构(英格兰和威尔士),1560s-1850s(单位:千万亿焦耳)
表4 1600年以来英国煤炭消费对城市化率的弹性

从表4可以直观地看出,英国煤炭消费增长与城市化程度增长之间具有极强的一致性,城市化对于能源结构转型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的煤炭工业发展缓慢,到了18世纪,中国的人均煤炭使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10]英国虽然在1600-1800年间,农业人口占比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却满足了总人口增长情况下的农业需求。现代能源替代了农业作为基本能源提供者的角色,满足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求,反过来又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对此可以称为“现代能源红利”。
四、能源需求——产业结构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于能源的需求影响不同,重工业要比轻工业和农业对能源的需求更多。
15世纪以来,英国出现了重工业增长迅速的局面。金属工业中心伯明翰的人口在1675-1769年就增长了4.5倍。以煤铁工业为主的矿冶业在16-18世纪英国重工业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早在1551-1569年,英国9个主要煤田的年产量已达21万吨。到1681-1690年,这些煤田的年产量增加了13倍,达到298万吨。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750年(通说),又增加到473万吨。[11]而煤炭的重要用途之一就是重工业,如制造业、造船业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英国远远把中国甩在后面,以致后来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相比之下,中国工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发展缓慢。因此对于现代能源的需求有限,“现代能源红利”的作用也有限。明清时期的江南几乎没有煤铁工业,因此也很难出现工业的规模经济。据研究,明代江南吴江等5县的五金匠总数不过878户。[12]不仅如此,在明清几百年中,虽然轻工业在迅速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13]
明清江南的能源使用量较低,从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工业部门来看,江南五金加工业所用能源,仅为木炭1万吨(明代后期)和4.5万吨(清代中期)。而17世纪末英国金属工业除了使用大量木炭之外,还要烧煤20万吨以上。[14]
轻工业对旧有产业结构的冲击不大,可以类似于农业生产的作坊模式进行,有些轻工业(如纺织业等)本身就是农业的延伸。而重工业需要集中生产和规模经济,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转型。重工业的发展制造了巨大的能源需求,而能源转型又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升级。
五、能源成本——科技进步的作用
能源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就能源而言,其外部成本主要是对于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这在今天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早期现代阶段,虽然对于煤炭污染的批评很多,但是发展相比生态环境得到了更多的强调。而能源的内部成本则对于这种能源的推广普及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此,不可忽视科技进步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开发成本的影响。
蒸汽机的发明在英国煤炭能源的开发推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英国的煤田煤层厚,基本都在海平面以下,因而矿山积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煤挖掘出来,需要先把积水抽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萨弗里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提水机,在1698年取得标名为“矿工之友”的英国专利。但是萨弗里提水机的特点是靠真空的吸力汲水,汲水深度有限,最多不能超过六米,这还是很难面对英国的大量厚煤层。因为要想从几十米深的矿井汲水,必须将提水机装在矿井深处,用较高的蒸汽压力将水压到地面,这无疑是困难而又危险的。为此,英国工程师纽科门及其助手卡利于1712年首次制成可供实用的大气式蒸汽机,用以驱动独立的提水泵。这是第一个实用的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的前身,为后来蒸汽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这种蒸汽机先在英国,后来在欧洲大陆得到迅速推广,被广泛应用了60多年,在瓦特完善蒸汽机的发明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在使用。最后不得不说的是詹姆斯·瓦特,瓦特制造出的蒸汽机被称为“万能的原动机”,在工业上得到广泛应用,开辟了人类利用能源的新时代。蒸汽机应用到矿山开采业,降低了人们的劳动强度,机器相比于人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连续开采,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在科技进步的作用下,到1800年左右,英国的煤和铁的产量比世界上其他地区产量的总和还要多。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令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但是在应用技术方面却始终未有重大突破,这也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六、英国结构转型的深层原因
中西比较应该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下,比较不同地区历史演变的关键因素。能源革命在英国的发生绝非偶然事件,是城市化、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城市化是一个关键的结构转型。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中英在历史上体现出了不同的“推力与拉力”。
根据赵冈的研究,古代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要远远小于英国。也就是说,在同样的耕地上,中国的劳动力要远远多于英国。这意味着,中国应该比英国有着更多的劳动力富余,更容易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伊懋可[15]、赵冈均认为,中国过多的人口形成了劳动密集型农业,从而抑制了城市及工商业的发展。但是,土地的粮食亩产主要受制于地力和农业科技,而不是同一块土地上耕种的人越多,产出就越多,“人多地少”会激发人们寻找新的出路。一定还有其他原因阻碍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密集型农业是“果”而非“因”。
中英城市体制的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是由封建社会分化出来的,独立于封建领主直接控制之外,成为独立的经济单元。因为城市功能的单纯性,只要经济不断发展,城市一般都很稳定,逐渐扩展,很少有强烈的兴衰起伏。前文所述的英国城市化率不断增长就是一例。
西方中古城市自由市民的身份对于农业劳动力极具吸引力。比如1227年,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就给克劳彻斯特城颁发了特许证,其中明文规定,农奴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便成为自由人,可以受到城市法律的保护。14世纪,受黑死病影响,劳动力短缺,农奴可以逃离庄园,到报酬较高的地方工作,农奴制在事实上解体,农民取得了自由选择工作地点的权利。因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以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为主要居民,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同时,长子继承制促进了阶级流动,使得富裕家庭的次子、幼子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成为优质商人,提高了商业质量。
到了工业革命之时,当英国的“一个工业中心突然迫切需要劳动力时,附近农村就会成为劳动力来源,形成四周向中心流动的向心型转移;而周围农村因流动而形成的劳动力短缺又由更远的地区来填补”。在这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机制至关重要。这种人口流动模式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促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且有助于消弭地区发展差异。[16]
在政治制度上,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教授对欧洲各城邦的规模增长率与政权持续时间、议会活动指数的关系,做了大样本量化回归分析,发现议会活动指数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发展速度、货币汇率稳定性越高,这些国家在18世纪、19世纪的经济增长越高,并且也是工业革命的主要倡导者。[17]英国是世界上议会制度的发源地,政治制度较为成熟,或许这也是英国首先发生结构转型、能源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作为政治中心出现的,不是由工商业者组织而成的。在城市里,府衙是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也常因政治与军事功能的变动而兴衰变化,不会有持续的城市化发展。中国自宋朝之后城市化率的下降印证了这一点。
相比西方的自由民身份,古代中国有着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另一条途径——科举。面对人多地少的约束,科举成了众多底层劳动人民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比如,福建山多田少,生计艰难,走读书当官之路的人特别多。据载,建宁府(今建瓯县)“土狭人贫。读且耕者,十家而五六”[18]。由于读书风气兴盛,在宋代的科举考试中,福建人异军突起,到北宋后期,福建的秀才数量已居全国前列。南宋末宰相、诗人吴潜总结全国的科举考试情况时便认为:“士之精于时文者,闽为最……”宋代似乎存在人均耕地越少,“家贫子读书”风气越盛的特点。[19]这一趋势在后来历朝历代中也很明显。但科举制度的存在以及与科举制度相关的意识形态,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得优秀的人才不会流向工商业,同时科举制度对于教育制度的塑造也抑制了独立的科学研究的发展。
能源革命推动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也开启了人类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的历史。然而,历史似乎有着一种微妙的轮回。由使用可再生的传统能源到使用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而使用化石能源给人类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今天全球正在准备一场杰里米·里夫金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含义,是指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人类将迅速过渡到一个全新的能源体制和工业模式,步入一个“后碳”时代,这个时代以绿色能源和能源互联网的普及使用为主要特征。简单来说就是要由使用化石能源回归使用可再生能源,但是要以一种现代化的、高效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能源。新的能源革命不是简单地设定能源消费指标就能实现的,需要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需要城乡结构、产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当然还需要科技创新。
[1] 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 参见Wright, Coal Mining in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1895-193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然而,并非所有学者都支持人口大量增长是现代转型的一个主要推力,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大量人口会阻碍现代转型进程。如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过去的模式》一书中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说”,认为:中国没能成功地进行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必须发展农业技术。参见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5] 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六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全部出齐。
[6]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4页。
[7] 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9页。
[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 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369页。
[9] 参见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0] 对于中国当时的能源结构,缺乏准确的数字,此处的说法来自多位此领域研究者的估计。参见[荷]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苗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99页。
[11]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页。
[1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页。
[13]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页。
[14]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
[15] 参见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6] 参见钱乘旦:《寻找他山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7] 参见Jan Luiten van Zande,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1800,Boston:Brill, 2009。
[18] 《永乐大典·胡寅斐然集》。
[19] 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0-641页。
[20] 参见[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