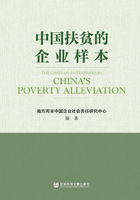
聚焦每一类困难群体
扶贫车间里的女人们[1]
有一次,朱爱青送女儿上学。女儿非要拉着她进教室,一个个同学介绍过去,“这是我妈妈。”她顿时觉得“心酸”。
“老百姓没经历过价格大幅波动这种事。去年同期收购价是23~25元,如果今年一下子掉到17元,他们接受不了,可能就把桑树给挖了,不养蚕了。”
“做生意来讲,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更有商机。”
外出打工的朱爱青回来了。
2019年,她还在广西南宁一家耳机厂做车间主管,每月能赚八千多元,回到百色市隆林县,这个数字降至三千多元。
隆林在滇黔桂交界,居住着苗族、彝族、仡佬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是集“老少边山穷库”于一身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全国52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截至2019年底,全县尚有10个村2219户7829人未脱贫出列。
朱爱青回乡是为了女儿。
去年,女儿三岁,上了幼儿园。有一次,朱爱青碰巧回了家,便送女儿上学。女儿非要拉着她进教室,一个个同学介绍过去,“这是我妈妈。”
她顿时觉得“心酸”,决定回来。
女人们回乡就业的理由大抵相似,“能有一份工作,能待在家里陪小孩、陪老人,已经很满足了”。2020年5月14日,朱爱青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她的新工作还是车间主管,地点是隆林扶贫车间,设在城西的轻工业区。扶贫车间的建立目标是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隆林县人社局就业服务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扶贫车间带动就业人数984人,其中贫困劳动力209人,易地搬迁劳动力55人。留守妇女是扶贫车间的就业主力,占就业总人数的74%。
一块显眼的红色横幅挂在朱爱青所在的工厂外墙,“就业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返乡的年轻人
朱爱青所在的达江电子专做马达与小风扇,前者发向广东,后者销往东南亚。
厂门口贴着一张4月28日的招工启事,产线普工底薪2000元,加班费每小时12元。算下来,工人们一周六天班,每月平均挣三千多元。
这家工厂有近二十个贫困户。招工时,别的正式工要在“38岁以下”,贫困户则放宽到55岁。
春末开始,风扇热销,流水线常常热火朝天工作到晚上8点。5月14日17:40,有工人来请求提前下班,“我要去买冰箱,今天这个时间可以(走了)吗?”
朱爱青嘴上怪他没“提前说”,但还是把人放走了。“人家来这里上班,选择一份收入没那么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家里。人家家里有事,你就得批。”她解释。
这也是她自己回乡的原因,将心比心,便多了一份理解。
过去在南宁工作时,每个月回家,单程要五个多小时,即便搭大巴,路费也超过190元。在隆林当小学老师的丈夫经常开车去接她。
隆林县民风传统,回乡的人常常奔走于家庭事务,逢家族中生老病死、婚嫁节日,都要请假回家料理。“这里请假特别多,比如家里有人过世,最少得请一个星期,多的话是半个月,不可能不批,”朱爱青说,“每天都有十几二十个人请假,所以我用90个工人,必须备到120个。”
工人总数在增多。朱爱青2019年12月入职时,厂里只有七八十人,现在已经超过120人。其中有一些,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外地无处可去的人。
年轻姑娘何雨就是其中一个。她原本在广东一家制鞋厂打工,今年,她从主管和老板处得知,订单大减,过去也没活干,只得在家门口找了新工作——在扶贫车间的昌隆服装公司做制衣。
40岁的朱开艳刚来没几天。她是个新手,南方周末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将小学校服前襟的两张布片车为整体。“质量很好的,做工也很细致的。”她边车边说,动作不快,“做不好要返工,一定要到位的”。
朱开艳在云南、四川、广东、福建都打过工,还在桥梁工地做过“苦工”,搬搬抬抬,多的时候能挣七八千元,“能挣钱的我都做”。尝试了几天新工作,她尚算满意,“也可以,熟手的话,一个月挣三四千元”。
针对这批新进工人,隆林县政府给出了“以工代训”技能培训补贴。2020年2月起新进的生产一线工人,可以得到每人每月500元补贴,以推动员工通过在岗实践提升技能。
信息栏上张贴的四张招工告示中,达江电子与昌隆服装两家公司都写明,招聘对象为“贫困户”,且强调“免费培训,简单易做”。
扶贫车间的工作大多如此,没有技术含量,主要以勤致富。
四十多岁的女工王婷麻利地将校服裤子套在缝纫机上,为裤腰车边,头也不抬,几秒钟便车好一条,丢在面前的“裤山”上。
4月,她仅凭服装计件就挣到3855元,空闲时间还去口罩厂帮工,也有576元收入,再加上133元加班费和300元满勤奖,月工资总数接近五千元。
不过她是特例,服装厂一百二十多名员工中,工资超过四千元的只有三人。
隆林县人社局就业服务所负责人廖碧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全县有9家扶贫车间,大多是厂房式,其中两家是2020年4月刚刚认定的。根据规定,带动贫困劳动力5人以上,支付年劳动报酬6000元以上,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即可认定为扶贫车间。
今年,这些簇新的厂房附带一项“福利”,连续3年免租。
疫情期间,当地还给出了六项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其中,在2020年3月31日前复工复产,并于6月30日前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扶贫车间,能得到2000元/人的带动就业补贴,这比以往翻了一番。而在2~6月赴区外务工,或在扶贫车间、企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能得到每月300元稳岗补贴。
“开工了,不可能让工人停下”
扶贫车间的主要受益人是留守妇女。
根据隆林县人社局就业服务所2020年3月的数据,留守妇女是扶贫车间的就业主力,占就业总人数的74%。其中,高凤服饰所有员工都是农村留守妇女,厂房设在新州镇含山村大树脚屯,专门生产少数民族传统服饰。
村里的男人几乎都前往广东、浙江等外省务工,妇女主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大树脚屯有一百多户人家,现有54人在高凤服饰工作。
这是一家前身为小家庭作坊的企业,1992年就已经开在含山村里。同村妇女不断加入,作坊规模扩大,后来到县城开了店面,在县城陪读的母亲们会去领手工,以补贴家用。
如今,这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已经在广西拥有三间店面、贵州有六间,面向的是少数民族对传统服饰需求的小众市场。
“最少是人手一套,有些人一年可能要好几套,出席不同的场合要新的款式。”该公司负责人杨倩霏说。
这是南方周末记者接触到的扶贫车间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一家。疫情期间,所有节庆、嫁娶活动停止,需求骤减,货量积压,尽管公司在3月16日已复工,但收入比往年少了一半。
为了自救,不得不全体减薪。管理层每人减半,降了3000元;在车间坐班的缝纫工,工资由2800元降到2000元;做手工的员工不再坐班,由专人配送至村民家中完成绣、染、钉等步骤,按加工量支付酬劳。节省出来的坐班费用,是每人每月500元。
减薪或裁员,都为了减小疫情影响。嘉利茧丝绸的老板杨旭栋将135名员工裁至126名。他采取的方式是持续生产,积压货品,实际订单销量只占产量的1/4。
“我这种情况,支撑到9月左右应该没问题,但再往后可能就有点吃力了。”他坦率地说道。
杨旭栋的家族在浙江做绸布生意,他的蚕丝公司入驻隆林后,开始育桑苗、饲养小蚕、收购蚕茧、生产蚕丝,成为家族企业的上游供货商,向浙江运输丝线,成品销往意大利和法国。
一开始复工时,他“信心满满”,那时国外疫情并不严重,2月19日至3月5日仍有订单。后来,意大利封国,“开始没有销路了,但已经开工了,不可能让工人停下”。
对杨旭栋来说,在隆林办厂,最有吸引力的是当地政策。自2013年他的蚕丝企业入驻,隆林县开始发力种桑养蚕,投钱扩大种植面积,向种植户提供优惠政策,帮助修建厂房。种桑养蚕受到鼓励,农户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他的公司也有了货源。
杨旭栋小心翼翼维护着这种积极性。今年隆林县新种的桑树有28000亩,受到疫情影响,外地蚕茧收购价降到了16~17元,而他仍将收购价维持在最高的20.5元。
“在隆林,这个产业是新的,老百姓没经历过价格大幅波动这种事。去年同期收购价是23~25元,如果今年一下子掉到17元,他们接受不了,可能就把桑树给挖了,不养蚕了。”杨旭栋说,这是他选择保底价收购的原因。
在贫困县里,一个成熟的扶贫车间,不仅仅是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
改做口罩的服装厂
你能轻易辨认出扶贫车间——“精准施策易地搬迁安置奔康结硕果”一行大字刷在厂房楼顶。从隆林最大的易地搬迁安置点鹤城新区步行十分钟能到达这里的各个工厂。
鹤城新区如今住了三千多户,一万多人。他们从全县16个乡镇易地搬迁而来,也是扶贫车间主要的目标对象。
根据要求,扶贫车间优先安排易地搬迁安置点的贫困户,或全县其他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对具体数据有所要求——贫困户须占用工总数的10%以上。
“我们鼓励他们去扶贫车间就业,都是做电子零件、服装这些的,只要勤快,新手都能胜任。”廖碧珍说。
介廷乡那桑村的郑文武一家搬进了鹤城新区的三室一厅。他说,新区自来水供应还不稳定,老人住不惯,就跑到县城的妹妹家里。自己也经常在厂里洗澡,尽量回家就不用水了。
但总体而言,“在县城还是比农村好”。在村里时,他种稻谷跟玉米,仅够糊口,离婚后要照料老人孩子,更无暇外出打工,现在“打一个月的工,(赚的钱)够我在家种田吃一年”。
郑文武如今在昌隆服装当司机,一个月保底工资三千多元。
福建人黄东海的这家公司,是一众复产受阻的扶贫车间中少有逆势而上的。他开拓了新业务——生产口罩。
厂子2月便复了工。2月10日,他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疫指挥部消息,公司被要求协助相关部门生产医用头罩和鞋套。在县政府支持下,他紧急召集工人,帮忙代工,并投入资金,将服装厂一楼改造为无尘净化车间,采购了6条口罩生产线和60套口罩耳带机,3月初开始生产非医用口罩。
以此为契机,他的公司正式分为口罩与服装两厂。
5月16日,他接受完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就动身去南宁寻找客户,打算开拓渠道,将口罩销往国外。
昌隆服装原先主做校服,黄东海早在2009年就来隆林扎了根。他考察过,隆林那时还没有校服厂,在这里办厂用工、用地成本低,当地政府也支持。
几年时间里,他的工厂几乎“承包”了隆林县95%的中、小学校校服,“做生意来讲,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更有商机”。
只是,今年2~3月,校服制作遭遇了瓶颈,布料、原材料、辅料和配件不能及时到位,“拖了差不多一个月”,产量大受影响。
黄东海说,布料大多订自广东、福建,受全球疫情影响,很多外贸企业特别是布料厂停减产,国内订单也就跟不上了。
做风扇的朱爱青也遭遇过类似的材料供应状况,两条流水线因此暂时放了假。
也曾因疫情影响,在3~4月遭遇销售淡季,工厂在4月进行了调休,因此流失了一部分员工。
不过,旺季来了,订单不愁,原材料一到,又整日忙着赶工。“每天客户都是直接在微信群下单,这一单没做完,又猛地下单,做都做不过来。”单量小而急,有时客户上午下了单,下午物流车就开到了厂门口,几百上千个小风扇装好拉走。
她根据自己接到的订单情况对南方周末记者推测说,东南亚疫情形势大约是有所好转了。
过去半年里,朱爱青瘦了十几斤,现在只有85斤了。以往在南宁做主管,她只负责生产安排,眼里是“目标”“数量”“品质”“出货”,但现在,要操心的事情多了不少,工作更忙了。
相比而言,这里的组织结构还不成熟,后勤、人事、考勤、仓库物料等没有细分,都是她在负责。她迟迟找不到有管理经验者,只得选了几个工人加以培训,以期早日有人分担工作。
工厂每天7:50上班,幼儿园也是同一时间开门。回到了隆林,朱爱青依旧没时间送女儿上学。但至少,她每晚能在家陪女儿两个小时,女儿说,已经很高兴了。
(应受访者要求,何雨、王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