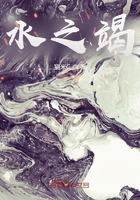
第7章 吴芮(6)
早上起来的阳光格外喜人,身旁的床褥已经叠放整齐。苹儿每天都会比我起得更早,然后去院中照顾她那些宝贝鸽子。我慵懒地伸了伸四肢,单手支在窗边听屋外的鸽子叫成一团。昨晚又梦到以前的事了,父亲、徐福、吴筵,这些人总会在我刚要把他们忘掉时突然在我梦中出现。我苦笑,看来是一辈子也摆脱不了了。
自徐福带着筵从鄱阳离开,一转眼又是八年过去了。据说之后他真的从始皇帝那里骗到了船也出了海,但自那以后就完全失去了音讯。父亲口上不说,心中还是惦念着的。看着他日益憔悴,白发都快掉光,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一直派人在东海沿岸打听着,让他们得到任何消息都要火速通知我。
后来始皇帝突然不信方士了,甚至坑杀了一批方士儒生。我得知后,特意叫人远赴咸阳打听消息,担心万一徐福他们回来了却被官兵抓住无法脱身。再后来始皇帝驾崩了,秦二世胡亥继位,暴政日益严重,那一阵各地都苦不堪言。鄱阳由于位置偏远,朝廷向来不愿意管,较之其他地方还好上不少,故而来了不少从中原逃亡过来的流民。再加上上缴税务的增多,害得我这个做县令的整宿整宿睡不好觉。考虑筵的时间也变少了。
由于酷政激起的民愤太深,结果还没让二世闹腾够一年,各地的反秦大军就纷纷露出了獠牙。我一直以来都勤于养兵,不光是为朝廷养,也有很大一批只吃我粮饷的私人兵。劝说我起兵响应的人不少,但介于时势未明,我决定先摆出起兵的架势,实际持观望态度。直到第一个举起反秦大旗的张楚王陈胜被秦国大将章邯消灭,而从江东打过来的项梁却借着陈王的名头讨伐了私立楚王的秦嘉,又拥立楚国后人芈心,从此迅速崛起时,我才稍稍看出点眉目来。于是命我的女婿英布率一部分的兵投奔项梁,派之前收复的番将梅鋗去战争沿线打游击,寻找有实力却隐忍不发的队伍向其靠拢,我自己则带领剩余的大队人马以我的名义自成一派。他日汇聚中原,不管谁掌天下,都好站稳脚跟。次日我与二人歃血作誓,三军一切听令于我,百越人众永不相弃。
如今反秦战争已经结束,项梁死后,英布追随了项梁的侄子项羽——便是当今天下人人畏惧的西楚霸王,梅鋗暗中交好了汉中王刘邦,而我又回到南方做了个谁也管不着的衡山王。一切正如我最初所料。
父亲在这期间还一直待在他的鄱阳老家。我曾想过要接他来邾县和我一起住,但他总认为筵有一天会自己回到家里,对于我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他似乎从没抱有希望。我只好不去管他,叫我的长子和筵的妻儿留在老家好生照顾他,并要被封到九江的英布不时派人问候……
当我意识到对往事的追忆会影响到我原本良好的心情时,赶忙将目光从窗外收回,赤着脚走到洗漱架前洗脸漱口,彻底清醒后再慢悠悠地坐回床上。
苹儿早已为我准备好早膳,放在桌子上,看着还不坏。昨天我失踪一事弄得她不快,我还以为她肯定会在里面放些毛虫什么的。毕竟这种事她在年少时干过不少。
一股暖意浮上心头,相伴的这许多年中,那丫头的确为我改变了很多。
苹儿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这一点从我捡到她的那一刻便知道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小女孩,抱着弟弟的尸体昏倒在路边。不知道她从哪里来,走过多远,又要到何方去。她的记忆就如同被那场大雨洗刷过一样干净。虽然我一直怀疑她失忆的可信度,但不管是怎样的过去,能够让一个孩子宁愿选择忘却,都绝对不会是温暖幸福的经历。所以我只是叫家医检查了一下她头部有没有受伤,剩下的就随她去了。
苹儿醒来之后的某一天,负责服侍她的侍女突然来报,说是从早上起就没见过她,府中都找遍了。“也许是跑出府了。”侍女偷瞄着我的脸色说话。没有看好要照顾的人,的确是她的失职。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责问了两句就没再追究。这个莫名出现的女孩从骨子里就透着古怪,自己走掉倒是给我省下一桩麻烦。因此我也没有派人去找。
第一次偶然相遇是巧合,第二次就是命中注定。当我第二次将苹儿从街角一群混混群中拖出时,她终于肯直视我的眼睛,问我道:“我命中欠你的吗?”
我苦笑,到底是谁欠谁的?
现在看来,果然还是她欠我的。要知道,照顾我可不知一件容易的事。服侍丫鬟被我换了无数,最后还是得让苹儿兼职夫人和侍女的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一向爱提意见的她对此倒是没有丝毫怨言,除了分娩前后,一直都将我的生活起居料理得一丝不苟。战乱时期,甚至跟随我到了前线。
说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对爱情更像是报恩。她惦念我两次救她,说会用一生来奉还,我也感激她的不舍不弃,因此从未考虑过再娶继室。
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大概是听到我醒来的动静,苹儿走进屋开始整理房间。倒掉洗漱用过的水,叠好被子,然后叉腰转向我,用眼神询问我为何一直盯着她看。
“你刚刚叠被子时往上面揍了两拳,我看到了。”我用筷子指了指床的方向。
“你说你昨天和朋友去洞庭湖边喝酒了?”
又回到昨天的问题上了吗……我随意地嗯了一声。
“你那个叫张良的朋友我没听你提过,哪天请到家里来让我见见吧?”
请他到家里来?我莫名觉得这句话很好笑,当然没敢真笑出来。我对她说:“好。”
见我一副敷衍的样子,苹儿撅起了嘴,毫不掩饰她的气恼:“还要扯谎吗?我看你根本请不来那个人!家医说你不是醉酒,是中了煞气。”
我背过身去,专心吃我的早膳。说是专心,其实是在专心注意饭里是否有针一类的东西。见我不理睬她,苹儿自然更加动怒。她的动怒法便是摔门而去,这点很好对付,事后哄哄也就过去了。
昨天的事,现在想来仍然很奇特。并非是故意向苹儿隐瞒,而是连我自己也没有理清头绪。
对于那个人,或者说是那只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