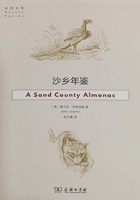
五月
从阿根廷归来
当蒲公英给威斯康星的牧场打上五月的标记时,就已经到了听取春天最后一个证据的时候了。在草丛上坐下来,把耳朵对着天空,排除掉草地鹨和红翅黑鹂的喧闹声,于是,你很快就可能听到它:高原鹬的飞行之歌,它刚从阿根廷回来。
如果你的视觉很好,你就能在空中寻找到它。它抖动着翅膀,在绒毛般的云层中盘旋着。如果你的耳朵不大灵敏,就不要去听它,只要盯着栅栏的柱子。马上,一道银色的闪光会告诉你:在那个柱子上,高原鹬已经落了下来,并且收起了它长长的翅膀。不管发明“文雅”这个词的人是谁,他肯定曾经看见过高原鹬合翅的动作。
它停在那儿,它的整个存在都在说,你的下一步行动是从它的领地上退出去。地方档案可能说明了你拥有这片牧场的理由,但高原鹬却轻松愉快地排除了这种世俗的合法性。它刚刚飞行了四千英里,就是为了再次宣称,它早已从印第安人那儿获得了权利,而且直到幼鹬能够飞翔
之前,这片牧场就是它的,没有它的声明,谁也不能非法侵入。

在附近的什么地方,鹬正在孵着四只很大的尖头蛋,这些蛋不久就会孵出四只早产的小鸟。从它们的羽毛刚干的那一刻起,它们就像田鼠一样趾高气扬地在草地上乱蹦起来,而且能巧妙地躲过你笨手笨脚地要捉住它的企图。在三十天时,幼雏就全面发育起来,其成熟的速度是其他鸟类所未有的。到了八月,它们就从飞行学习中毕业了。在八月的寒冷的夜晚,你可以听到它们所发出的就要飞向南美大草原的信号,它们要再次证实两个美洲的久远的整体性。半球上的休戚与共,在政治家中间还是件新鲜事,但在这些带着羽毛的空中舰队中间可并非如此。
高原鹬很容易适应农村。它尾随着黑色和白色的“野牛”,那些现在就放养在它的草原上的牛群,发现这是一些可以接受的、能够代替棕色的野牛的动物。13它在干草地里做窝,就和在牧场上一样,但和笨拙的野鸡不一样,它不会在割草机里被捉住。在干草准备收割之前,幼鸟已经羽毛丰满并飞走了。在农业地区,鹬只有两个真正的敌人:集水沟和排水渠。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的敌人。
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时期,威斯康星的农场几乎失去了他们的时间概念:五月的牧场是在宁静中变绿的,六月的夜晚也没有带来那婉转啼叫着秋天就要到来的预告。万能的黑火药,加上维多利亚时代之后宴席上的烤鹬肉的魅力,曾经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姗姗而来的联邦候鸟法案的保护来得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