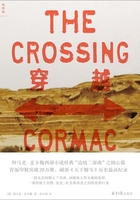
“这事恐怕不容易。这只狼到这一带来的时间还不长,你还找不到它什么规律。”桑德斯先生补充道。
“埃科尔斯说现在已经没有一只狼是有规律的。”
“他可能明白些,他自己就跟半只狼差不多。”
孩子们的父亲点点头。他坐在鞍上微微转身,朝开阔的平原看去,又转过身来看着桑德斯老爹。“你闻过埃科尔斯以前装饵用过的东西吗?”
“是的,我闻过。”
孩子们的父亲又点点头。他举起一只手招了招,然后掉转马头和孩子们一起上路了。
晚饭之后,父子们把一个镀锌的大洗濯盆架在炉子上,提了几桶水倒在里面,加了一勺子碱液,把捕兽夹全放进去煮。他们生着大火,一直往炉子里添着木头,一直烧到上床时分。睡觉之前,他们给盆里换了水,新加上了洋苏木屑,往炉膛里塞满了大块木头,继续让沸水清洗这些兽夹,然后都去睡觉。博伊德在夜里醒过一次。他躺在床上听着房子里、黑暗中的寂静,听着炉子里柴火的噼啪声和房子在风中的吱吱响声。当他朝比利的床看去时,床是空的。于是躺了一小会儿,他就起身走到厨房里。比利正坐在靠窗的一张厨房椅子上。他双手交叉压在脑后,椅子朝后仰着,正在观赏干河上空的月亮、河边的树林和南方的山峦。他转过头来看着立在门口的博伊德。
“你在干什么?”博伊德问他。
“我起来添火。”
“你在看什么?”弟弟又问。
“没看什么,这儿没有什么好看的。”
“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比利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回床上睡觉去吧,我马上也过去。”
博伊德闻声反而走进了厨房。他站在餐桌旁边。比利转过身来看着他。
“什么把你给吵醒了?”
“你呗!”
“我可没出声啊。”
“我知道。”
第二天早晨比利起来时,他的父亲正坐在厨房桌子旁,腿上搭着一个皮围裙。他戴着一副鹿皮手套,正在往一个兽夹里擦蜂蜡,其他兽夹都摊在地上的一张小牛皮上。兽夹经煮洗之后,都呈现出深蓝色。他看到了比利,便摘下手套把它们和围裙上的兽夹放在一起,然后包起围裙,放在地面的小牛皮上。
“先帮我把这个大盆搬下来,然后你可以接着打蜡。”
比利照着父亲的吩咐做了。他仔细地给兽夹上蜡。他先给饵盘子上蜡,特别没忘记为盘子上的字母打蜡,再给铰接颌状夹具的槽口打蜡,五尺长的铁链的每一个环扣都不错过。最后,连链头上的两爪倒钩都上了蜡。全妥了之后,父亲把所有的兽夹都挂在屋外的冷风中,免得屋子里的气味传染了它们。[6]次日早晨,当父亲进他房间叫他时,天还未亮。
“比利。”
“是的,爸爸。”
“早饭五分钟就好。我们早吃早走。”
“好的,爸爸。”
当他们走出家边的这片地时,天已经破晓。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所有的兽夹都装在一个柳条背篓里,由父亲背着骑在马上,但是背带被放松着,这样骑马时篓底就会落在他身后马鞍的后鞒上,免得人受累。他们朝正南骑行。在他们头顶,冠了新雪的布莱克峰已经在初阳下闪烁着银光,而与此同时,山底的谷地还笼罩在黎明前的暗影之中。当他们越过通向菲茨帕特里克泉的那条老路时,太阳已经四处可见。他们沐浴着朝阳,穿行到了牧场的高头。从这里,就要爬山进入佩伦西洛山脉。
半晌午时分,他们到了这丘陵中的一块低地,这正是小牛犊丧命的地方。在他们刚刚穿林而过的地方,已经有雪盖住了父亲骑的马三天前踩出的足迹。在死牛犊躺卧的树荫处,还有残雪未融,但这些雪已经被血染红,被践踏过,被小土狼的爪印反反复复地折腾过。小牛犊已经惨遭分尸,皮、肉和内脏的碎片零零落落地撒在血染的雪地上,有一些还被拉扯到更远的地面上。父亲摘下手套,卷了一根烟,坐在马上抽着,另一只手握着两只手套搭在马鞍的前鞒上。
“别下马,”父亲说,“看看能不能找到它的脚印。”
他们骑着马穿过这片地。马儿们看到地上的雪,显得有点局促不安。骑手们便以一种嘲弄的方式来宽慰它们,仿佛要羞辱它们的胆怯似的。
比利一直没能找到狼的踪迹。他父亲一踩脚镫下了马。
“到这儿来。”他对比利说。
“您想在这儿埋一副夹子吗?”比利问父亲。
“不,你下来看看。”
比利下了马。父亲已经滑下了背篓的带子,把背篓放在雪地上。他单腿跪立,用嘴吹去面前的一小片新雪,露出了这狼五天前留下的晶莹明晰的脚印。
“这是它吧?”比利问父亲。
“这就是它。”父亲断定。
“这是它的前爪。”比利也判断着。
“是的。”父亲又肯定着。
“它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吧?”
“不,它不会再回这儿了。”
比利站起身来。他朝前面的草地看去。有两只大乌鸦正栖息在一株光秃秃的树上。它们一定是在骑手们骑近时才飞到那树上去的。除此之外,什么景致都没有。
“您觉得其他的牛都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父亲思索着。
“如果牧场上有一头牛死了,其他牛会待在那儿吗?”
“那就看它是怎么死的了。反正它们不会愿意和一只狼待在一起!”
“您觉得它现在会不会又吃了一头牛?”
父亲从他跪立的地方站起来,拎起了背篓。
“这可能性很大,”他说,“咱们走。”
“是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