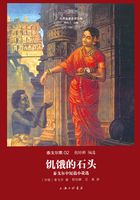
第8章 骷髅
倪培耕 译
我们三个童年时代的小伙伴,都歇息在一个卧室里,在它隔壁房间的墙上,悬挂着一具人的骷髅。夜间,风吹得那些骨头嘎吱嘎吱直响。白天,我们又不得不拨弄那些骷髅。我们那时正向家庭教师学习《云吼陈亡记》[9]等诗篇,以及向一个康勃尔医学院学生学习骨骼学。长辈们殷切期望我们迅速成为掌握一切科学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意愿究竟实现了多少,晓得我们情况的人,无须我们去告诉,不了解我们情况的人,我们索性藏拙不说。
光阴荏苒,转瞬许多年晃过去了。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无从探知,那具骷髅究竟从那屋里跑到哪儿去了,骨骼学知识也不知从我们脑里飞向何方,什么影踪都没有留下。
有一天晚上,我们的房子被客人住着。我没有找寻到栖身之所,只好在那放过骷髅的房间安歇。换了陌生的地方,不会一下就睡着的。在床上辗转反侧,倾听着近处教堂时钟敲响的全部夜点钟声。这期间,墙角的一盏油灯仍旧点燃着,它每隔五分钟暗淡一下,最后终于熄灭了。前些日子,我家死了人。当这盏灯刚熄灭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死亡”的事,仿佛觉得,在深更半夜,偌大的大自然舞台上,犹如这灯火的光亮消失在永恒的黑暗里一样,人类无数小小生命的光亮,时而在白昼,时而在黑夜,倏然熄灭了,并从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掉。
我蓦然想起那具骷髅。当我想象她生前的肉身模样,忽然觉得,仿佛一具有意识的活动东西,在黑咕隆咚的屋里,沿着墙壁摸索,绕着我的床四周回转。我清晰地听到她短促的呼吸声,仿佛觉得,她在寻找失落的东西。她一步紧似一步,满屋旋转。
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我彻夜未寐、头脑发热的幻觉,那些疾步的响声委实是我太阳穴上血管的跳动声。然而,我依旧恐惧得毛骨悚然,出于驱散那种恐惧的念头,我壮着胆,大声叱喝:“那边是谁?”
脚步声倏然在床边停止,听到了一个回答:“是我,我那个骷髅到哪儿去了?我是来寻找骷髅的。”
我心想,在自己想象的创造物面前,断乎不能流露胆怯情绪,否则会贻笑大方。我紧紧抓住枕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妙哉,深更半夜,出来干那美差使!你与那骷髅究竟有什么关系?”
她的回答好像在黑暗的蚊帐里发出:“问得奇怪!朋友,包藏我心的骨头就在那具骷髅里!我二十六个年华的青春在它四周发展!我难道不能有看它一回的愿望?”
我回答:“当然,这是一个蛮有理的回答。你就去寻觅吧!我还想安静地睡一会。”
她说:“你是孤零零一个人?我稍许坐一会儿,与你随便叙叙家常。离今天三十五年前,我也与一个男人,促膝交谈。但以后,我只在火葬场畔的阴风里悲鸣,不觉度过了三十五年韶华。今天坐在你身旁,我能否像人一样,同你叙谈叙谈?”
我觉得,她仿佛已坐在帐幔边沿。找不到其他法子,我鼓足了勇气说:“好吧,请谈你所喜欢的话题吧!”
她说:“倘若你想听最有趣的故事,莫过于我自己的生活故事。请仔细听着!”
教堂的时钟当、当敲了两下。
她娓娓细叙:“当我在人世年轻时,我像怕阎王一样怕一个人。那个人便是我丈夫。我整日提心吊胆,像上了钩似的。那时,我仿佛觉得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使我上钩,把我从自己洋溢着爱意和恬静的水池里拽出来,怎么也挣脱不了。两个月后,我的丈夫死了。诸亲好友和家里老少都为我悲伤和哀怜。我的公公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仔细端详我的脸庞,对婆婆说:‘你看见了吗,她有双邪恶的眼睛!’这句话至今仍萦回在我耳畔——你专心听着吗?你对这则故事感兴趣吗?”
“好极了!”我夸奖说,“故事的开端是引人入胜的。”
“我继续讲下去。我快活地回到了娘家。我的年龄渐渐地大了。人们总对我保守秘密,但我十分清楚,像我这样的窈窕淑女,不是俯拾即是的。你的看法呢?”
“可能的。但你要记住,我可从来没有见到过你。”
一听我这个回答,她忍俊不禁地捧腹大笑,然后又往下说:“没有看见过我?你不是见过我那具骷髅吗?哈!哈!哈!不要介意,我只是同你开开玩笑。我怎能使你相信呢!在我那深陷的眼眶骨的窟洞里,不是容纳着像大黑蜂那样的又黑又大的忧伤眼睛吗?在那阴森森的牙齿可怕相上,不是能想象出我当年恰似红宝石般的鲜红嘴唇上所荡漾的甜蜜笑意吗?我又如何使你深信,在一些干枯的骨头上有着我艳丽秀美的魅力,有着我青春成熟时期的柔和而坚实的靥窝的曲线,它们犹如天天盛开的鲜花,既能使我嗔怪,又能使我巧笑。你们竟用我身体的骷髅来学习骨骼知识,那种事在我那个时代,连最负盛名的大夫也不敢设想的。我记得,一个大夫向自己的挚友说,我是朵‘金色的旃簸迦花’,他的意思是,世上所有的人能够作为人体骨骼学的学习材料,而我似乎只是朵馨香美丽的花。难道在金色的旃簸迦花里能包含任何骷髅吗?
“当我碎步行走时,我感到仿佛摇晃着一颗晶莹宝石,向四周射出炫目的宝光。我稍许挪动轻盈的身躯,那波动的优美线条,仿佛像无数美丽的涟漪漫布在四周。我经常端详自己那双如花似玉的纤手,觉得那双手能够在世上所有轻荡男子嘴里,套上嚼口!随意地驾驭他们!当苏帕德拉带着阿周那,威风凛凛地乘坐凯旋之车,穿过惊呆的人群,风驰电掣地奔跑,那时人们可以观赏她那纤细的双臂,玫瑰色的手掌和犹如柔滑发辫的手指!
“但是,天哪,我那厚颜无耻、毫无遮掩、不加修饰的衰老骷髅,给你们提供了丑陋的假证据!那时我孤立无援,没有发言权。我把世上最大的愤怒,发泄在你们身上。我曾琢磨,用自己二十六个年华的勃勃朝气和青春火焰灼热的玫瑰红容貌,设法显露在你们面前,打消你们的睡意,横扫充塞在你们脑子里的骨骼学知识!”
我说:“倘若你有身影,我抚触到你的身躯,那我可以发誓,我就不让脑子里存在那种学识的影儿,脑子里只有人世间令人销魂的青春容貌,它在深夜漆黑的帷幕上闪烁出灿烂的光芒。行啦,我眼下不说更多的东西啦。”
她又讲下去:“我没有任何女伴,哥哥立下终身不娶的誓言。内室只有我一人。我常常坐在花园里的树荫下,梦想整个宇宙爱着我,整个天空星辰凝视着我,为我的绝色倾倒;清风一次次借着理由,叹着嘘气,从我腋下擦过;我脚下的青草,倘若有生命的意识,也因我的美色陶醉得无意识了。我知道,普天下的青年,成群结队,组成一束束青草,心甘情愿地伏在我脚底。不知什么原因,那时心灵觉得一阵悲凉。我兄长的朋友什西锡卡尔,通过了医学院毕业考试,成为我家的医生。我开始躲在帘子后面,偷偷看他。兄长是个奇怪的人,仿佛他不能睁眼看世界,世界对于他仿佛不是敞开的;他感觉一切都是空虚的。所以他愿意离开喧闹而光怪陆离的世界,退隐到僻静的黑暗角落里。
“他的朋友只有什西锡卡尔,所以在外界青年中,我只能看到什西锡卡尔一个人。黄昏,当我在花树底下铺上像帝王一样的坐毡,心情舒畅地坐着时,仿佛感到世间所有男子都化为什西锡卡尔的形象,站到我脚边,渴求得到庇护。——你听仔细了吗?故事怎么样?”
我叹了一口长气说:“我觉得,倘若我能以什西锡卡尔身份下凡,那该多好。”
她继续讲:“你听完吧。有一天,乌云密布,我发了烧。医生进屋,看望我。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脸对着窗户,以便落日的红霞照在我脸上,润色我苍白的脸儿。大夫一进屋,就朝我脸上看。我也暗自想象自己站在他的地位,注视着自己的脸蛋;在黄昏的绛红夕阳里,瞧着那漫不经心地搁在温热枕头畔的娇嫩而青白的脸蛋,仿佛像一朵凋谢的温柔花儿;蓬松而鬈曲的散发拂在前额上,羞涩而低垂的大眼睛的眼皮,在面颊上投上一层忧伤的阴影。
“大夫用温存的口吻对我兄长说:‘我可以诊一下令妹的脉吗?’我从被底下伸出自己慵困而圆满的手腕。我心想:‘倘若戴上青玉手镯,那会更好看。’他握着病人的手,诊脉。我从来没有看到大夫那样局促不安,他似乎害怕接触,手指颤抖得厉害。他已知道我烧的热度,我也计算着他心跳的次数,相互获悉了心心相印的暗示。——你相信吗?”
我说:“尽管没有发现怀疑的任何理由,但人的脉搏,每时每刻都不是一个样的。”
她说:“哦?我病了好,好了病,反反复复。有一天我蓦然觉得,我想象中的男子数目渐渐地减少,最后只留下他‘一个’。我的世界几乎成为无人居住地,在我这小小世界里,只剩下一个大夫和一个病人。
“一到黄昏,我无声无息地起身,穿上春天色彩的纱丽,细心地梳结好发髻,插上一个茉莉花环。然后携带一面小镜子,走到花园树荫下,像往常一样坐着。
“你以为我如此欣赏自己的美貌,会生厌?不会的。因为我不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那时虽然我独自一人坐着,但我那时看自己,仿如大夫大饱眼福,欣赏着自己的美姿。看了后,神魂颠倒,发痴地爱着、亲着。但不管对我发生多么浓厚的爱,我心灵深处仍发出深深的叹息,犹如黄昏的和风发出沙沙的哀鸣声。
“不过从那时起,我不是单独一个人。当我走动时,我细心地垂下眼,观赏自己踩地的娇小脚趾,心想我们新近医科学院毕业的大夫见了,将做何感想呢?窗外,正午炎热的阳光灼人,静谧笼罩着大地,哪儿都屏息静气,不透出一丝声息。远方天空,孤独的鹞鹰不时发出悠扬的鸣啭声,飞翔而过。我们花园围墙外,小贩用拖长的音乐似的叫声,喊着:‘卖洋娃娃啦,卖手镯戒指啦。’那时,我用手铺床,在草地上铺开洗濯得洁白的细床单,躺在上面。我轻佻地袒露着一只光胳膊,一只手枕在头下,恍惚觉得,有人正在欣赏我那种奇异的姿势,仿佛有人捧起我的手,在他的玫瑰红的手掌上亲了个吻,然后他慢慢地离开——你听着,倘若故事在这儿戛然而止,你觉得如何?”
我沉吟着说:“这倒是并不坏的结尾,但不完整。若能有头有尾讲完,我就能愉快地度过余下的晚间辰光。”
她说:“好!”但下面的故事内容兴许太严重了。它的笑容不知藏匿到了何处?那具带着阴森森牙齿的骷髅又不知在何处显露?
“再听下去吧。大夫有了些实习经验之后,就在我们楼下,开了一个诊疗室。那时,我常去找他,在谈笑中问及各种药,问他吃多少剂量的毒药,能置人于死地,人为什么那么轻易死去,无头无脑的问话连绵不断。一接触这些医疗话题,大夫总是口若悬河,娓娓细叙。我听着听着,就像对待家里人一样熟悉了死亡。所以我的小世界只有两件东西:爱和死亡——你听着,我的故事现在快结束了,余下不多了。”
我温存地说:“夜间的辰光也快完了。”
她又说:“几天以来,我发现,大夫的神情十分忧郁,神志恍惚,局促不安。有一天我看到他穿着十分讲究的华丽衣饰,向我兄长借马车用一夜。不知去何方。我坐立不安,好奇心驱使我到兄长那儿。起先说些无关紧要的题外话,然后问道:‘哥哥,大夫今晚借用马车,要到哪儿去?’
“兄长简略地说:‘去死。’
“我着急地追问:‘哥哥,你不能明白地告诉我?’
“他略微坦率地说:‘去娶亲。’
“我说:‘是真的?’说完,我狂笑不已。
“我渐渐地探听到:大夫在这场婚姻中将获得一万二千卢比的遗产继承权。但他瞒着我,不是侮辱我吗?我难道伏地向他请求,你这样干,我将悲恸欲绝地死去?天下的男子真是不可信。我在世上只认识一个男子。不消一会儿工夫,就发现了他的本性。
“当大夫看完病人回家时,我放声大哭,说:‘大夫,我听说,今晚是你大喜之日?’
“望着我那种狂笑模样,大夫不仅难为情,脸色顿时煞白。
“我问:‘不请乐班来吹吹打打?’
“他听了叹口长气,说:‘结婚难道是那么快乐的事?’
“我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话我闻所未闻。我说:‘不行,不行,应该请乐班吹吹打打,张灯结彩,装饰装饰。’
“我絮聒得兄长心烦意乱,他无可奈何,同意隆重地准备迎亲队。
“我反反复复打听新娘的模样长得如何?她来时,我该做些什么?我问大夫:‘大夫,那时你还这样诊女人的脉吗?’哈!哈!哈!虽然我不能窥透别人肚子里的事,尤其男子的心,然而我能发誓,我的话犹如针刺,戳进了大夫的胸膛。
“盼等着夜晚到来。黄昏时分,大夫与我兄长一块坐在屋顶阳台上,对杯痛饮。这已成为惯例。月亮在天空渐渐升起。我脸上堆着笑容走上去,说:‘大夫,难道你忘了?快到婚礼的时候了!’
“对了。我有一件事忘了交代。我偷偷地到药房,取来一些白色药末。到了屋顶阳台,乘人不备,把它撒在大夫的杯子里。饮了白粉酒,人要死的,这是从大夫那儿学来的。
“大夫举杯,一口饮光,忧伤的目光瞥视着我的脸。他用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说:‘好,现在我走!’
“喜庆喇叭吹奏起来。我走到楼下,穿起新娘嫁衣——巴拿勒斯的纱丽;把放在箱子里的所有首饰珠宝,统统拿出来佩戴上。头发分缝里满处都染上了朱砂。然后在花园的常青树下铺了床,躺着。
“那是个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夜晚!皎洁的月光倾泻着。驱散沉睡世界的疲困的南风吹拂着,整个花园里的常青树和茉莉花芳香四溢。
“乐队渐渐远去。月光开始朦胧,变得惨冷。我的常青树、果树、顶上的天空以及关联我一生的亲密世界,也像幻影似的,从我的思维中淡薄下去。那时,我合上眼睛,发出一阵痛楚的苦笑。
“我希望,当人们来看望我时,我那笑容像玫瑰酒痕一样,依旧停在自己的嘴唇上;希望自己从这里带上使我脸上生辉的笑容,步入花烛洞房时,笑容原封不动地永存着。
“但我的花烛洞房在哪儿?我那色彩缤纷的迷人嫁衣在哪儿?我蓦地听到从自己内心里发出一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而被惊醒,看到三个顽童把我的骷髅当作学习骨骼学的材料!在那胸膛藏着的悲怨欣喜,在青春花蕾初绽的地方,教师正叫着根根骨名,教授知识!
“你听着,我所袒露的自己的完美心灵,在自己的嘴唇上所流露的最后笑容,你看到了它们的印记吗?
“故事怎么样?”
我说:“令人感动!”
这时,乌鸦发出了第一声啼叫。
我问:“你现在情况如何?”
没有任何反应。
晨光渐渐射入我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