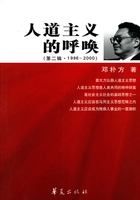
追求社会和谐与文化进步[1]
(一九九七年五月)
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者,能够参加“杰出亚裔人士论坛”,我感到十分荣幸,也非常高兴。
在座的各位,都是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等知名人士,卓有成就。我也曾有过当一名物理学家、造福人类和平事业的美好愿望。但是,正当我在北京大学专心攻读原子物理时,“文化大革命”那场大动乱一夜之间改变了我的命运,将我推入残疾人的行列。当然,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不只是我个人遭到不幸,亿万中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动乱结束后,我有机会到加拿大就医。在那里,我感受到现代康复医学对改善残疾人功能的巨大作用,体验到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文明。当友人们劝我留下来接受长期治疗时,我想到我的祖国还没有康复医学,千千万万跟我一样的残疾兄弟姐妹在迫切地等待康复,就毅然告别加拿大,回到自己的祖国,着手建立我国第一座康复机构,并由此走上了为残疾人工作的岗位。
中国有六千多万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由于自身残疾和外界障碍,他们是一个脆弱而易受侵害的群体。特别是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人的尊严和价值丧失殆尽,扩大化的阶级斗争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无情,残疾人备受歧视和冷遇。
面对如此艰难困境,首要的任务是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找回“文革”中失落了的社会亲和力,再造一个友爱和谐的社会。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我们的事业是人道主义的事业》的报告。我认为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不应当再摈弃这一人类文明的成果,应使它成为人际关系的准则,成为维系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做残疾人工作,帮助最困难的群体,就是最现实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残疾人事业的一面旗帜,必须高高举起。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那思想尚未解放的年代,有人视人道主义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有人则誉之为理论禁区的突破,拍手欢迎。我不是理论家,不去与他们争论。我只是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做。久而久之,坚冰终于融化,人道主义思想恢复了它的光彩。从政府官员到广大百姓,都逐渐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为它所感召、吸引,开始认识到残疾人同样是人,有其尊严和价值,应当享有做人的权利。如今,人道主义已经作为社会的基础思想之一写进了政府的文献;“不人道”成为对一个人最严厉的谴责。
一项事业的发展,如同一个国家一样,只靠道义的维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伴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我和我的同事们着手起草、制订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草案。前后历时七年,聚集了上百名法律工作者、残疾人代表和残疾人工作者,查阅了上百万字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同时也借鉴了十多个国家的经验,几易其稿,终于在一九九〇年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草案提交给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作。为使法律顺利通过,我和同事们逐个拜访各位委员,讲残疾人的苦难,呈送联合国制定的《残疾人世界行动纲领》,介绍国际社会的文明进步潮流,反映广大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强烈愿望。艰苦的工作换来意外的欣喜: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七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委会上,这部法律一次性全票通过!许多残疾人和他们的亲友都哭了,我也哭了。我和众多残疾人深切地感到:我们的人民真好!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们真好!
我由此悟出一个道理:绝大多数人的心都是善良的。不是不人道,而是不知道。只要工作做到,总会感动上帝的。历史的积垢,世俗的偏见,利己的私欲,往往给一颗颗善良的心包上一层坚硬的外壳。只要打破这层外壳,让心与心赤诚相见,人类终究是能够沟通的!于是,在我们主办的残疾人刊物《三月风》上,最早喊出了“理解万岁”!很快,它为全社会所接受。如今,已完善成“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公民行为准则。
为了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这一法则贯彻到实际社会生活中去,几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跑遍了全国的两千多个县。有些偏远地区,建国以后从没有中央政府的人去过,第一次见到北京来的人,当地干部、群众激动不已。所到之处,我们宣讲《残疾人保障法》,拜托政府官员关心残疾人的疾苦,登门入户访贫问苦,力所能及地帮助残疾人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内地一名残疾考生,连续三年参加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就是不被录取。我得知后,四处游说,直至拜访了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一位副总理,终于帮助这位考生进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进而,我们又与教育主管部门共同修订了残疾人入学标准,制定了《残疾人教育条例》,使残疾儿童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由十年前的不足百分之六提高到现在的百分之六十;数千名残疾考生进入了高等院校。
西藏地处高原,紫外线强烈,白内障发病率高,许多失明者只有三十多岁。了解到这一情况,我们先后组派了几批医疗队,入藏做白内障复明手术。一位喇嘛患白内障失明多年,一直认为是神明对自己的惩罚。手术复明后重见天日,他欢喜得载歌载舞给医疗队献上哈达,称赞医生才是真正的神明。这些年来,我们共为一百七十五万白内障患者做了复明手术,为五十多万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做了矫治手术,对七万多名聋童进行了语言训练。当在黑暗中生活多年的盲人重见光明,流下热泪时;当在地上爬行十多年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站了起来,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高时;当聋孩子们能够开口说话,父母亲第一次听到他们叫“爸爸、妈妈”时,我真比自己能够站起来恢复行走都高兴!因为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人们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社会的温馨和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日为“全国助残日”。我们把这作为宣传、动员社会的极好机会。每逢这一天,全国各级政府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总计数百万人,纷纷走上街头,走进残疾人家庭,嘘寒问暖,促膝交谈,倾听残疾人的呼声,帮助残疾人解决实际困难。这是残疾人的盛大节日,也是一次政府官员与平民百姓、健全人与残疾人、社会方方面面的情感大交融,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唤起人们扶弱助残的社会责任感,净化了每个人的心灵,促成一种和谐友爱的社会风尚。其影响超出了帮助残疾人,是广泛而深远的。
由点到面,残疾人工作的范围不断扩展。我们已经制定、执行了两个五年工作计划,目前正在执行第三个五年工作计划。从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到福利保障、文化生活,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残疾人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已不再是梦想。当然,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比起需要做的工作来,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始终坚持一点:积极吸取国外好的经验,立足中国具体国情。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起点低、起步晚。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残疾人事业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积累了许多好的、成功的经验。对这些经验,一是要学,二不照搬。例如许多发达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残疾人从出生到死亡,全部由国家包起来。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有条件这样做也未必好。因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劳动是人的基本权利,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在座的各位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只有当他能够造福社会、给别人带来幸福时,他才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所以,我们中国推行“劳动福利型”的政策: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要为残疾人提供一定的扶助和救济,以保障其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我坚信: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残疾人同样能够成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些年来,我们兴办了大量的福利工厂,集中安排残疾人劳动就业。同时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个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按照职工总数的一定比例,吸收残疾人就业。目前,全国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率已达百分之七十。就业不仅改善了残疾人的经济状况,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一位弱智青年,以往在家里看电视,总要服从其他家庭成员的意愿——别人要看什么,他只能随着看,没有选择节目的权利。我们通过兴办工疗站,安排智力残疾人边学习生活自理、边参加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这位残疾青年有了工资收入,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台电视,看什么节目,就由他说了算了。
我由此想到:任何成功、有益的经验,只有结合具体的环境、条件加以实施,才能得到预想的结果。植物界里可以搞“嫁接”,也可以搞“移植”。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嫁接”的效果多半要比“移植”好。拒绝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必然导致固步自封、退化萎缩;脱离实际生搬硬套,也难以成活。只有发挥“母本”优势,“嫁接”外来良种,才能提高品质,富有生命力。
从事残疾人工作多年来,我深刻地体会到:残疾人是一个最困难的群体,他们特别渴求社会的和谐与文明进步。“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的每一点进步,人们的每一点善意关怀,他们都能体察入微地感受到;相反,哪怕是微小的社会动荡、道德沦丧,都会给他们带来切肤之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残疾人的感受,反映着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做残疾人工作,也就是在从事一项文明进步事业。这项事业不仅为残疾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在促进着社会的和谐,推动着文明进步,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提升到新的高度。
值得欣慰的是:我虽然没能成为物理学家,但在为残疾人工作的岗位上,我同样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1] 这是邓朴方同志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杰出亚裔人士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