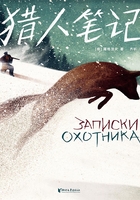
独院地主奥夫西亚尼科夫
亲爱的各位读者们,请想象一下这么个人,胖乎乎,高个子,七十来岁,脸长得有点像克雷洛夫,浓密的眉毛下,目光明亮聪慧,仪态庄重,言语从容,步履缓慢。奥夫西亚尼科夫便是这么个人。他穿着袖子老长的蓝色长褂,扣子一直系到脖子,围着一条淡紫色的丝巾,带流苏的皮靴擦得闪亮。外表来看,他像个家底殷实的商人。他的双手细白漂亮,聊天当中时不时抓一下扣子。奥夫西亚尼科夫的庄重与迟缓、明理与慵懒、直白与执拗让我想起彼得一世改革以前俄罗斯那些大贵族……要是可以的话,我简直想给他穿上费尔亚济衫注15。他是仅存的几位旧式人物之一。
邻居们对他都极为尊敬,把与他交往看作是荣幸。跟他同样的独院地主们恨不得要替他祷告,离着他老远便要脱帽致敬。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其实,在我们这儿,一般很难把独院地主和农民区分开来。他们的家业简直比农民还不如:小牛犊只吃得上荞麦,马儿半死不活,马车也破破烂烂。
奥夫西亚尼科夫过得不至于此,但也并没有多富贵。他跟自己的妻子住在一座舒适的小宅院内,用人并不多。他都让他们穿上了俄式衣着,并叫他们“伙计”。用人们顺带也种地。他从来不佯装贵族地主,不忘乎所以。做客时,总要客套一番才肯入座,而当有新客来访,他必然第一个起身问候。不过,他的自尊仪态必然使来客对他深深鞠躬。
奥夫西亚尼科夫守古风并非因为迷信(他在信仰上是十分自由的),而是出于习惯。比如,他并不喜欢带弹簧座的马车,因为觉得并不舒坦;要不就是坐赛马马车,要不就是垫好垫子,自己驾一辆漂亮的、由枣红色走马拉着的小马车(他家里养的全是枣红色的马匹)。他家车夫是个年轻的、脸颊红扑扑的小伙子,鬓角剃得光光的,身着泛蓝的粗毛料外套,戴着山羊皮帽,系着腰带,总是恭敬地坐在一旁。奥夫西亚尼科夫每日饭后必睡个午觉,每星期六洗澡,只读宗教方面的书籍(朗读时必郑重地戴上宽大的银边眼镜),早睡早起。胡子他倒是剃去的,发型也留着德国式的。
招待客人时,他热心而诚恳,不过不会对客人深鞠躬,不会忙来忙去,不会一个劲儿劝人吃些干果或者腌菜。“老婆子,”他并不起身,只是微侧过去对妻子缓缓说道,“给客人们上点好吃的吧。”他认为粮食是上帝的赐予,买卖粮食是罪过的。因此,年灾荒和物价飞涨那会儿,他把自己所有的储备都免费分给了周围的地主和农民们。第二年,大家都用收成抵还给了他。
邻居们常常跑来向他征求意见或者请他解决纠纷,大家往往都听他的,老老实实按他说的去做。因为他的干预,有几家子彻底划清了地界……不过,跟几位女地主打交道发生不愉快后,他宣布,不再过问她们之间的事。
如今,他完全没法忍受各类匆忙草率的行事作风,以及女人间的叨叨咕咕和纠缠。有次,他家不知怎么失火了。有个仆人心急火燎地冲进屋,对他喊道:“火,起火啦!”“你叫什么叫呢?”奥夫西亚尼科夫平静地说道,“把帽子和手杖递给我……”
他喜欢自己调教马匹。有一次,一匹比秋格马疯一般地驮着他冲下山坡,直往深沟边上去。“行啦,行啦,你这小家伙,会把自己摔死的。”奥夫西亚尼科夫宽厚地安抚着它。一瞬间,马儿驮着他,拉着马车和坐在后面的车夫,一股脑儿跌进了沟子。所幸的是,沟底堆着厚厚的沙层,没人受伤,只是那比秋格马把一只腿摔脱臼了。“你看看,”奥夫西亚尼科夫爬起来,平静地对它继续道,“早就跟你说了吧。”
妻子他也是自己挑的。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奥夫西亚尼科娃是个高个子女人,不苟言笑,话不多,总是戴着咖啡色的丝质头巾。她让人觉得有点发冷,不过,其实并没人抱怨过她的严苛,正相反,很多可怜人都说她是个善心的好夫人。她有一张轮廓标致的脸,大大的深色眼睛,薄嘴唇。直到今日,在她身上还能看到那曾远近闻名的美貌的痕迹。夫妇俩并没有孩子。
读者们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认识奥夫西亚尼科夫的。两天后,我便去拜访他。他刚好在家,坐在宽大的皮椅里面读着《每日圣徒言行录》。一只灰猫蹲在他肩上,舒服地呼噜着。他以自己惯有的热情而不失自尊的方式接待了我。我们聊了起来。
“路加·彼德罗维奇,您说实话,”我问道,“从前,您的那个时代是不是更好?”
“跟您说吧,那时候当然不错啦,”奥夫西亚尼科夫道,“我们那时候过得很平静,特别舒坦……不过,还是现在更好。上帝保佑,到您孩子那一代,会更好。”
“我还以为,路加·彼德罗维奇,您会跟我夸赞旧时光呢。”
“不,旧时代没什么好夸的。就比如吧,跟您已故的祖父一样,您现在仍是地主,不过,您可没他那个权力咯!您也不是那类人。我们现在被别的阶级挤对,这是没办法的。就把原先那些都打破吧,兴许会更好呢。不过,年轻时候经历的那些,我是再也见不到啦。”
“比如?”
“比如说吧,我还是以您的祖父举例。那可是个威严的人!他对我们这些独院地主可是不客气的。您应该是知道的,自己的领地您不会不熟悉,从查普雷金到马里宁的那块楔形地?现在您那儿种的是燕麦的那块……以前其实是我们的,整块都是我们的。您祖父夺了去。他骑马过来,用手一指,说道:‘这是我的领地。’就这么强占了。我那已故的老爹(愿他在天之灵安息!)是个特别正义而热血的人。他没忍住,—有谁愿意这么白白失去自己的产业呢?他告上了法庭。他一个人告的,其他人不敢。有人跑去告诉您祖父了,说彼得·奥夫西亚尼科夫把您给告啦,说您抢了他的地……您祖父立马就派了自家的猎长巴乌什带着队伍过来,把我父亲抓到你们领地上去了。我当时还是个娃娃,光着脚在后面追了好久。然后,把他带到您家跟前,在窗户下面狠狠抽了一顿。您祖父坐在阳台上看着,祖母也坐在窗边张望着。我父亲叫道:‘夫人,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您给说说情吧,您行行好吧!’可她只不过是抬起身望着。他们逼我父亲许诺让出土地,还得千恩万谢总算留了条活命。就这么着,那块地就是您家的了。您去问问您家的农民,这地叫啥。它叫‘棍棒地’,因为当初是靠拼棍棒打下来的。所以啊,我们这些小人物可不怀念那旧时的规矩哟!”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奥夫西亚尼科夫,连看也不好意思看他了。
“那会儿,我们还有个邻居,姓科莫夫,叫斯捷潘·尼克托波里昂内奇。他可是把我父亲折腾坏了。这家伙成天醉醺醺的,还喜欢请人喝酒。往往喝上几口,用法语说句‘不错’,舔舔嘴,然后便作起来,给所有邻居发邀请来喝酒。他家的三套马车往往都是备好的。你要是不肯去,他便亲自来请……就是这么个奇怪的人!酒醒的时候,他并不大说谎,一旦要是喝高了,就吹嘘说他在彼得堡的喷泉大街上买了三座屋子,一座红色的带一个烟囱,一座黄色的带两个烟囱,蓝色的则不带烟囱;还说自己有三个儿子(他连婚都没结过),一个是步兵,一个是骑兵,第三个单干……他说他的仨儿子就分别住在这三座屋子内。老大经常招待海军将军,老二的座上宾则是陆军将军,小儿子则和英国人交朋友!他经常就这么举着酒杯站起身说道:‘为我大儿子的健康干杯,他是我家最孝顺的!’然后就哭起来。要是有人不肯喝,那就糟了。他威胁道:‘把你毙了,然后连尸也不给你收!……’要不就是一边蹦着一边嚷嚷:‘我说诸位,跳起来吧!自己乐一乐,也叫我高兴!’不管咋地就是逼着你跳。他把自家的农奴女都折腾得够呛,有时候叫她们整夜大合唱,一直唱到清晨。谁声音响亮,他就奖励谁。要是人家唱累了,他便用手捂着头叹道:‘哎,我真是个可怜人哟!大家都不管我咯!’马夫只好给姑娘们鼓劲儿,好叫她们继续唱。他不知为何跟我父亲特别亲。能怎么办呢?差点没把我老父送进坟墓。他要是自己没死,准把我父亲送进坟墓。有次喝醉了,他从鸽棚里掉下来摔死了……您瞧瞧我们这些邻居哟!”
“现在可真是不一样啦!”我评论道。
“是,是呀,”奥夫西亚尼科夫表示同意,“不过呢,过去吧,贵族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些。那些豪门望族就更不必说了。我在莫斯科可算见识过了。据说莫斯科的望族也绝迹了。”
“您去过莫斯科?”
“很久以前去过。我这都快七十三啦。去莫斯科还是十六岁那年。”
奥夫西亚尼科夫叹了叹气。
“您在那儿都见谁了?”
“我见过形形色色不少大贵族。他们那日子过得可风光了。光是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奥尔洛夫-切斯缅斯基伯爵家里就去过不止一次。我常见到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我叔叔在他家当门卫。伯爵一家住在沙波罗夫卡大街,离卡卢加门很近。那可是真正的大贵族!那步伐体态,那仪容举止,简直难以想象,没法表达。他身材高壮,力大无穷,双目炯炯!跟他不熟悉、对他不了解的人,都怕他怕得不得了;了解了他的为人以后,简直就如沐春风。他什么人都肯见,大事小事都关心。他喜欢亲自跟人赛马。比赛的时候,不会一下子把别人超过,叫人难堪,而是快到终点了,才超过去;还总是安慰对手和马儿,特别和蔼。他养了一群优等的筋斗鸽。有时候,他走进院子,坐进椅子里,叫人把鸽子放出来。周围的房顶上,有持枪的人守着,防着老鹰。仆从把一只盛满水的硕大的银盆放在伯爵脚边,好让他看鸽子们的倒影。成群结队的乞丐依靠他的施舍度日……他捐了不少的钱!不过,要是生气起来,那可真是雷霆万钧,总把人吓得半死。可是呀,还没等回过神呢,他自己往往已经微笑了。他家要是请客,能把全莫斯科灌醉!……他可是个聪明人,土耳其人就是被他打跑的。他还喜欢搏击,专门叫人从图拉、哈尔科夫、坦波夫和其他地方请大力士来跟他比试。谁要是被他赢了,他就奖赏谁。要是有人能赢了他,不仅会得到重赏,还会被他激动地对着嘴亲……我在莫斯科那会儿,还见识过他举办的赛狗会。那是俄罗斯从没有过的。他邀请了全国各地的猎手,选定了日子,给了三个月时间。大家都带着狗儿、导猎来了,简直是一个军团!他先招待大伙儿好一顿吃喝,然后到城边开赛。这观看比赛的人哪,排山倒海!……您猜怎么着?您祖父的狗胜出啦。”
“是不是米洛维特卡?”我问。
“就是,就是米洛维特卡……伯爵非要把它买下来,跟您祖父说:‘把狗儿卖给我吧,要多少钱都成。’您祖父答:‘不行呀,伯爵,我不经商,不想做啥子交易。为了荣誉的话,我可以把妻子都让给您,不过米洛维特卡可不行……我还不如把自个儿卖给您呢。’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把您祖父一顿夸:‘好样的。’您祖父用马车把狗儿拉了回去。后来,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是叫人奏乐把它下葬的。把狗儿埋了以后,还在它坟上竖了墓碑呢。”
“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没欺负过谁吗?”我问道。
“事情其实往往是这样:小人被收拾都是自找的。”
“您刚才提到的巴乌什是个什么来头?”我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
“您都知道米洛维特卡,怎么没听说过巴乌什呢?……他是您祖父家的狩猎长和主要的驯犬师。您祖父对他宝贝得可不亚于米洛维特卡。这是个绝对忠诚的家伙,您祖父一句吩咐,他能上刀山下火海……他可真能指挥狗子们追赶猎物,能把整个林子闹个天翻地覆。可要是犯起脾气来,那就从马上跳下来,躺在地上不动了……狗儿们听不到他的指示,什么痕迹都不理不追了。您祖父可真是气坏了,嚷道:‘要不好好收拾收拾这个二流子,我就不活了!我把他皮扒下来,五脏六腑都给撕出来!’最后呢,还不是得派人去询问巴乌什要什么,为什么不指挥狗儿追猎了。这时候呢,巴乌什总是要酒喝。喝够了之后,他便上马吆喝起狗儿继续追个痛快。”
“路加·彼德罗维奇,您好像也挺爱打猎,对吧?”
“本来也是喜欢的……现在不行了,现在我已经上了岁数。本来呢,也有点不好意思,地位不够呀。我们其实算不上贵族。我们中有些好喝酒、没能耐的,还往往爱跟真正的地主家套近乎……这算个什么呢!只能叫自己受辱罢了。人家给他一匹老掉牙的马,还用鞭子把他的帽子给掀到地上,装作是赶马的时候把他给误打了。他还是憋出笑,不能惹了人家。我跟您说吧,人哪,越是地位低,越是得严格要求自己,否则就是要受辱。”
“没错,”奥夫西亚尼科夫接着说,“我在这世上活得挺长。现在这时代不同了。在贵族身上,我看到了很大变化。那些产业不大的,要不就是当了公务员,要不就是干点别的。有点产业的,更是跟先前不一样了。这大贵族们我也是见识得多了。就比如划分地界吧。我得承认,现在的情况叫人欣喜,他们比早前可周到礼貌多了。只是有一点真叫人惊奇。按理说,他们是有知识的人吧,说话头头是道,叫人心服口服。可对实情却没有了解,搞不清自身的利益。他们自己管事的农奴还总坑他们,把他们当傻子。您应该听说过科罗廖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吧?那可是个真正的贵族吧?英俊、富有,念过大学,在国外游历过,说话井井有条、彬彬有礼,跟我们大家都握手问好。您认识的吧?这不,上周,有个叫尼基弗尔·伊里奇的中间人把我们都请到了别廖佐夫卡。
“那中间人尼基弗尔·伊里奇说道:‘先生们。我们得把地界划清楚了。我们这地已经比别人都落后了,挺丢人的。大家开始吧!’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大家七嘴八舌讨价还价、争论起来,那位代理人呢,开始让步了。首先闹起来的是个叫奥夫契尼科夫·波尔菲利的家伙……他有什么可吵的呢,他自己一寸地也没有,是代他兄弟来讨价还价的。只听他嚷嚷着:‘不行,你们可蒙不了我!你们可找错人了!把图拿来给我瞧瞧!叫丈量官来!’
“‘您有什么要求呢?’
“‘你们把我当傻瓜啦?以为我就这么把自己的条件交代给你们了?你们先把地图拿来!’其实呢,自己正用手捶着那图呢。
“他把玛尔法·德米特里耶夫娜给气坏了。她叫着:‘您怎么敢这么败坏我的名声!’
“那位回道:‘您那名声啊,连我家的狗都不如。’大家按着他,给他灌了点马德拉酒,这才算安静下来。刚把他安抚住,其他人又闹起来了。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科罗廖夫就只好坐在角落里,啃着手杖的镶头,摇头叹气。我可真是羞愧呀,简直没有办法,就差钻地缝里去了。人家该怎么想我们呢?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起身,做出要说话的手势。中间人赶忙对大家道:‘大家请消停一会儿,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有话要说。’这贵族们,还真都安静了。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这就讲开了。他说,我们好像忘了为什么聚到这里。划定地界对地主们来说,自然是有利的,但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农民们过得轻松些,劳动起来更有动力,也能交得起租子。否则,他连自己的地都不知道在哪儿,常常跑到了老远的地方去,找也找不到。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还说,地主们不该不替农民们的福祉着想。农民们是上帝派来的,理性地想一想,他们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都是统一的。他们过得好,我们便也好;他们艰难度日,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呢,也就没有必要没头没脑地为了点鸡毛蒜皮的细节争吵……就这么讲啊讲!讲得倒是真好,直冲着人心坎里去了……老爷们都颇不以为然,我呀,倒在一旁听得眼泪汪汪。这要是在以前,可听不见人讲这些……可结果怎么样呢?自己连四俄亩沼泽地都不肯让、不肯卖。他说:‘我叫人把这块沼泽地抽干填平,盖一座制呢厂,配上现代设备。这块地我早就选好了,有了自己的打算的……’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不过,其实主要是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的邻居卡拉西科夫·安东抠门儿,不肯花个一百卢布打点一下科罗廖夫的管家罢了。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呢,至今觉得自己没啥不对,还在唠叨着建制呢厂,却是连沼泽地都还没开始填呢。”
“他自己的领地管理得如何?”
“他一直在引入一些新的规矩。他家的仆从们都不大满意。但下人们的意见也没啥可听的。我觉得亚历山大·弗拉基米雷奇做得对。”
“可是,路加·彼德罗维奇,您不是支持老规矩的吗?”
“我不算啥。我既不是贵族,也没有什么地。我有啥产业呢?……别的什么我也不会。我尽量按理依法行事,这就行啦!年轻的地主们不待见以前的规矩,我挺赞赏他们……是该好好用用脑子了。但问题就在于,青年人有时候太理想化,对待农民像对玩偶一样,玩弄两下子,搞坏了便扔下。那些管家们吧,不管是本地的农奴还是德国来的,对农民们总是压榨。哪怕能有一个年轻主子做个榜样也好呀,给大家看看,究竟应该怎么管理!……啥时候能到头呢?难不成到死我都见不到新规矩实行吗?……这可真是的,旧的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还没生出来呢!”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奥夫西亚尼科夫。他环顾了一下,移到我跟前,低声继续说:
“您听说过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柳波兹沃诺夫吗?”
“没,没听说过。”
“我来跟您讲讲他的那些新奇事吧。简直没法理解。这是他家的农民说的。不过我倒是并不十分相信。他挺年轻,前不久,母亲去世之后,得到一笔遗产。他来巡视自己的领地,农民们也都聚过来瞧瞧自己的新主子。大家一看,—这是啥子打扮哟!他们老爷穿着棉绒衬裤、红衬衫,披着车夫式的长褂子,脚着镶了滚边的靴子,留着长胡须,头上戴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整个脸也十分怪异,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精神出了问题。‘爷们儿,各位好!上帝会帮助你们的。’他说。大家弯腰致敬,不出一声,惊吓得不知说什么好。他自己呢,好像也有点胆怯,继续自己的发言:‘我是俄罗斯人,你们也是俄罗斯人。我热爱俄罗斯的一切……我的心是俄罗斯的,我身体里流淌着俄罗斯的血……’然后又突然发号施令起来:‘我说,孩子们,给我唱一首俄罗斯民歌吧!’大家简直呆若木鸡,动弹不得。有个胆子大点的开口唱了几句,然后立刻蹲到地上,躲到别人身后去了……
“我们这里的地主们哪,前前后后各色各样都有过的。有那怪脾气的、爱胡闹的,总是穿得跟车夫似的,成天歌舞升平,跟仆人们啦,农民啦,混在一起吃吃喝喝。可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可真是特别。他跟个大闺女似的,成天读读写写,要不就是朗读坎特歌子注16,跟谁都不打交道,就爱一个人在园子里逛,特别忧愁伤感的样子。
“之前的那个管家呢,一开始可是担心坏了。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来之前把农民家都跑了个遍,挨个作揖。他倒是也明白,平时没少欺负大家。农民们可都暗自乐呢:‘老兄,该到你遭报应的时候咯!你可算是折腾够了,你这个混蛋!……’可结果如何呢?这该怎么跟您说呢?这新来的老爷压根儿啥也不懂!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管家叫到跟前,自己反倒脸色通红,呼吸急促:‘你做人要公平,不要欺负任何人,听到没?’之后就再也没找过他了!他在自己的领地上跟个外人似的。管家自然也就放下心来。农民们有怨气也不敢找老爷,害怕呀!这可真是叫人惊奇。老爷平常跟他们问好,目光和善,他们见到老爷还是怕得浑身发抖。您说说,这都算是哪门子奇事呢?……难道是我自己又老又蠢?反正我搞不懂。”
我回答奥夫西亚尼科夫说,这位柳波兹沃诺夫先生大概得了什么病吧。
“哪儿有什么病哟!肥得不得了,脸也圆乎乎的,简直不像个年轻人……天知道咋回事!”(奥夫西亚尼科夫深深叹了口气。)
“讲到贵族的话,”我继续问,“路加·彼德罗维奇,您给我说说独院地主们的情况呗?”
“这您还是饶了我吧!”他急忙说道,“不过,就告诉您点儿啥吧!(奥夫西亚尼科夫挥了下手。)让我吃点茶点吧……这农民呀,就是农民。不过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他沉默了。茶点送了上来。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起身坐到了我们近前。整个晚上,她悄无声息地进出了几趟。沉默持续着。奥夫西亚尼科夫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茶。
“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轻声说道。
奥夫西亚尼科夫皱起眉头。
“他来干啥?”
“他是来道歉的。”
奥夫西亚尼科夫摇摇头。
“您看看,”他冲着我继续道,“这些亲戚该怎么办呢?也不能跟他们断绝往来……上帝这不也给了我一个侄儿。他那脑瓜子吧,没的说,倒是挺灵光,上学的时候成绩不错,但做事就是不着调。他本来给公家干过的,却把工作给辞了,说是没啥发展……他是把自己当贵族了还是咋的?就算是贵族,现在也不可能轻易就爬到高位。这不,现在失业着呢……这还不算,反倒成了个替别人打官司的家伙!给农民们写起诉状来……写申辩书、教训村警、揭发土地丈量官,成天光顾酒馆啦,旅店啦,跟些城市里的混混们搅和在一起。这不很快就得出事吗?区里的、县里的警察都已经警告过他了,他倒是挺会花言巧语,能把他们逗乐,蒙混过关,随后呢,又给他们找一堆麻烦……别提了!他是不是坐在你屋里呢?”他对妻子问道,“我可了解你。你最菩萨心肠了!你呀,就总护着他吧。”
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垂下头去,微笑了一下,脸红了。
“好吧,看来就是这样,”奥夫西亚尼科夫继续道,“你呀,就惯着他吧!你叫他进来!看来只好这样了,看在贵客的面子上,我就原谅这蠢孩子吧……叫他进来呀……”
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走到门边,喊了一句:“米佳!”
米佳看上去二十七八岁,又高又瘦,一头鬈发。他走进屋子,看到我之后又在门边停下来。他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不过肩部大得不自然的皱褶则说明这套衣服出自本国、而且只能是俄罗斯裁缝之手。
“过来呀,过来,”老头子道,“窘什么呢?你得谢谢你婶子,我就算原谅你了……老爷,给您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对我说,“亲侄子,我却怎么也管不住。这算是到了紧要关头了吧!(我们互相行了礼。)你来讲讲,究竟捅了什么娄子,为啥大家对你不满。说话呀!”
看来,米佳并不想当着我的面辩解什么。
“过会儿吧,叔叔。”他嘟囔着。
“什么过会儿,就现在,”老头子说,“我知道了,你是当着地主老爷的面良心发现了。这更好,你就认错吧。说话呀……我们听着呢。”
“我没什么可悔过的,”米佳激动地说道,甩了甩头,“叔叔,您自己想想看。列舍基洛夫镇的独院地主们来找我,说:‘替我们说说话吧,兄弟。’‘怎么了?’‘是这么回事:我们那儿的粮仓井井有条的,管理得不能再好了。突然,来了个当官的,说是要检查。他看了以后说:“你们这仓库里太乱了,很多管理不当的地方,我得跟上级汇报。”“哪里有问题?”“我心里可清楚着呢。”他说……本来吧,我们都商量过了:那就好好“感谢”一下那官员。结果普罗霍罗奇老爷子不干了,他说:这些人根本喂不饱。究竟该怎么办呢?难不成我们就一点辙也没有?……我们听了老爷子的。那位官员呢,恼怒之下写了份报告上去。这不,现在叫我们回复吗?’‘你们的粮仓的确没问题?’我问。‘老天有眼哪,真没问题。粮食数目合法的呀……’‘这样的话,你们也没啥可担惊受怕的。’这不,我就给他们写了份状子吗……这都还不清楚,谁能赢这官司呢……至于说有人在您这儿告我的状,那很好理解呀: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呀。”
“每个人……就除了你!”老头子低声道,“你怎么又和舒托莫洛夫村的农民们搅和在了一起?”
“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反正知道。”
“这事儿上,我也没啥不对的。您再仔细想想呀。舒托莫洛夫的农民被邻居别斯潘金占了四俄亩地。那家伙说,地是他的。舒托莫洛夫的那些农民是交代役的,他们的主子去了国外。谁能替他们说话呢?您想想看!那块地自古就是农奴耕种的,根本没啥可争的。他们找到我,求我写一张状子。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以后威胁道:‘我就是不把这个米佳的头卸下来,也把他的大腿打断……’我倒是要看看他怎么把我的头卸下来,到目前为止我还好好的呢。”
“你别得意,你那颗头不会有好下场,”老头子道,“我看你简直就是个疯子!”
“不过,叔叔,不正是您跟我说……”
“得了,我知道你要说啥,”老头打断他的话,“没错,人哪,是得有正义感,而且也应该帮助身边的人。有时候呢,不能总考虑自个儿……不过,难道你就这么无私?农民们不是请你去酒馆儿的吗?不是对你行礼,毕恭毕敬地说:‘德米特里·阿里克谢伊奇,帮帮我们吧,我们会好好感谢你的。’然后从地板下拿出藏着的一个银卢布或者五卢布纸币给你?难道没有过?你说说看!有没有?”
“这方面我的确不对,”米佳垂下头,答道,“不过,穷人那里我从来不昧着良心要钱的。”
“现在不要,等哪天过得紧巴了,你就会要了。不昧良心……哟呵!所以你这是帮的都是些圣人咯?……你忘了波尔卡·别列霍多夫了吗?……谁替他张罗来着?谁帮着他来着,啊?”
“别列霍多夫的确是因为自己犯了错才受罚的……”
“挪用公款……这是闹着玩儿的?”
“叔叔呀,您想呀,他多穷呀,还养着一家子人……”
“穷什么穷……他就是嗜酒好赌,这才是原因!”
“他这不是因为苦闷才喝起来的吗?”米佳放低声音说道。
“苦闷?!你既然如此心善,为何不帮帮他呢,为啥总和这醉汉在酒馆儿里瞎混呢?他倒是挺会说话!真是罕见!”
“他其实是个大好人……”
“你反正看谁都是好人……这个,”奥夫西亚尼科夫对着妻子说道,“给他送去了吗……那个,你知道的……”
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点点头。
“你前阵子怎么又消失了?”老头子又问道。
“进城去了。”
“该不是去打台球、吃茶点、玩儿吉他、混官府去了吧?还是又在什么鬼地方给人写状子,或是跟商人家的子弟们鬼混?是不是这样?你倒是说说看!”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米佳笑着道,“对了,差点忘了!安东·帕尔费恩内奇·弗恩吉科夫邀请您礼拜天去吃顿便饭。”
“我才不去这肥佬家呢!他家吃的鱼不便宜,放的奶油却是酸臭的。真有他的!”
“我还见到了费多西亚·米哈伊洛芙娜呢。”
“哪个费多西亚?”
“加尔佩恩琴科的地主家的,就是那个买下米库林诺村的地主。费多西亚是米库林诺人。她在莫斯科住的时候,干的是裁缝活儿,交的是代役,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一年呢……手也是挺巧。她在莫斯科接的都是好活。加尔佩恩琴科把她叫了回来,却不给她安排位置。她其实是想赎身出来的,都跟老爷说了。那家伙却啥回话也不给。叔叔,您不是认识加尔佩恩琴科吗?就帮着说句话呗?……费多西亚准备交一笔不菲的赎金呢。”
“该不是你给的钱吧,啊?好吧,我跟他说说。不过我可不敢保证啥,”老头子面带不满继续说道,“这个加尔佩恩琴科是个吝啬鬼,爱买债券、放贷、收购地产……他怎么会住到我们这儿来呢?这些个外来户!一时半会儿别指望他们能有什么回音。我们走着瞧吧。”
“叔叔,您就帮帮忙吧!”
“好,我试试看。你可给我听好了,别狡辩!老天保佑!你往长远点打算行不行!否则,米佳,你没啥好下场,肯定要栽跟头。我没法总帮着你呀……我又不是啥达官显贵。好吧,你去忙你的吧。”
米佳起身离开。塔季扬娜·伊里伊什娜跟了出去。
“惯孩子的那位,叫他吃点东西再走,”奥夫西亚尼科夫冲着她的背影叫道,“他脑子倒是还行,”老头继续说,“心眼儿也是好的,不过,我可真替他担心……好了,真是对不住,叫您听了这么些鸡毛蒜皮的事。”
前厅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身着丝绒长外套的人,个子不高、头发花白。
“是弗朗茨·伊万内奇呀!”奥夫西亚尼科夫叫道,“您好呀!最近怎么样?”
各位读者,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来者。
弗朗茨·伊万内奇·列如恩也是我的邻居,也是奥廖尔省的地主。他成为俄罗斯贵族的经历颇不寻常。他出生在奥尔良,父母均为法国人。他当年是跟着拿破仑来征讨俄罗斯的,是军乐队的鼓手。一开始,征途顺利,法国佬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莫斯科。不过,在溃逃的途中,可怜的列如恩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了,落到了斯莫棱斯克的农民手里。
斯莫棱斯克的汉子们在缩绒作坊里把他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拉到了水坝旁的冰窟窿边,叫“伟大军队”注17的鼓手赏个面子—也就是跳进冰窟窿里。列如恩先生没法答应此要求,还操着法国方言要斯莫棱斯克的汉子们放他回奥尔良去。“在那儿,”他说道,“住着我温柔的老母亲。”注18汉子们呢,估计是不知道奥尔良在何处,继续怂恿他沿着蜿蜒的格尼洛焦尔卡河顺流而下游过去,并鼓励着推搡他的后背和脖子。
令列如恩无比庆幸的是,就在此时,车铃声响起,坝上驶来一架巨大的雪橇,隆起的后座上垫着花毯子。雪橇由三匹褐色的维亚特卡大马拉着,上面坐着一位胖乎乎的、脸色红润的地主,身着狼皮袄子。
“你们这是做啥呢?”他问汉子们。
“把这法国佬给淹了,老爷。”
“这样啊。”地主冷漠地说着,回过身去。
“先生,先生!”注19可怜的法国佬叫起来。
“怎么?”穿狼皮袄的家伙不满地说道,“来犯俄罗斯,放火烧了莫斯科,该诅咒的,还把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卸了,现在叫‘先生,先生’注20了,夹起尾巴了!真是活该透顶……费尔卡,我们走!”
马儿们动了起来。
“不过,先停一下!”地主叫道,“我说,这位先生,你擅长音乐?”
“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好心的先生哪!”注21列如恩叨念着。
“这都是些什么人哪!没一个会说俄语!音乐,音乐!你懂不懂音乐?会不会?你倒是说话呀!听不懂吗?懂不懂音乐?会弹钢琴不?”
列如恩总算听懂了地主的话,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是的!我是乐手,我会所有的乐器。是的,先生……您救救我吧,先生!”注22
“你今天可是吉星高照了,”地主说道,“各位,把他给放了。这里有二十戈比,拿去喝酒吧!”
“谢谢您,老爷!您把他带走吧!”
列如恩上了雪橇。他幸福得几乎快要窒息,嚎哭着、颤抖着,不停地给地主行礼,对汉子们和车夫千恩万谢。天寒地冻的时节,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带粉色条纹的绿绒衣。地主看了看他冻得发青的手脚,二话不说,把皮袄给他裹上,把他带回了家。
仆人们叫法国佬暖和过来,叫他吃了饱饭,还给换了新衣。地主把他带到了女儿面前。
“孩子们,”他对她们说道,“我给你们找了一位老师。你们不是一直缠着我要学音乐和法语吗?这不,这位法国人会弹钢琴……我说,先生,”他指着五年前向一个贩卖花露水的犹太人买来的破琴说道,“请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水平,弹吧!”
列如恩坐在琴凳上,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从来就没摸过钢琴。
“弹呀!请弹呀!”地主催着。
心怀绝望,可怜的家伙敲击起琴键来,就像击鼓一样,勉强弹着……“我本以为吧,”他之后回忆道,“我的救命恩人肯定一把把我揪起来,扔出门外。”然而,令被迫的临时钢琴师万分惊奇的是,地主之后反倒是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不错,不错,”地主说,“你的确懂行。行了,去休息休息吧。”
两周之后,列如恩到了另外一位富有而有教养的地主家。主人很喜欢他乐观温和的性格,把养女嫁给了他。他当了公务员,成了贵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奥廖尔省的地主罗贝扎尼耶夫,一位擅长作诗的退伍骑兵。后来,他自己也搬来奥廖尔省居住了。
这不,我还在做客时,这位大家现在都称弗朗茨·伊万内奇的列如恩进了好友奥夫西亚尼科夫家……
不过,读者们大概已经听够了我在独院地主奥夫西亚尼科夫家做客的故事。我这就不再唠叨个没完了。
注15 古时俄罗斯及波兰贵族的一种外衣,无扣,无领,束腰,长袖。
注16 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诗歌,通常被朝圣者传颂。
注17 原文为法语。
注18 同上。
注19 原文为法语。
注20 同上。
注21 同上。
注22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