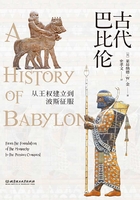
第一章 巴比伦在古代史中的地位
巴比伦之名意味着古代世界中影响其他族群的伟大文明中心之一。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从公元前第2千纪开始巴比伦人的文化在西亚大部分地区逐渐扩散。仅举一个表明这种影响的例子,我们发现在公元前15世纪末之前巴比伦语已经成为东方外交的语言。那么埃及国王用巴比伦的语言和书写方法来与巴比伦本国或亚述的统治者进行通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使用这种外国文字和语言向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属国的统治者发号施令,而且这些迦南官员也使用同样的书写媒介向他们的埃及主人发送报告。我们还发现,在同一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米坦尼王国的雅利安统治者用楔形文字
书写其所统治国家语言。几十年后,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除了纪念性的目的外已抛弃他们古老而笨拙的象形文字系统,借用同样的符号记录他们自己的语音,同时他们与埃及的条约是用巴比伦语订立的。公元前9世纪定居在凡湖周围亚美尼亚山区的强大的乌拉尔图种族采用亚述文字作为其国家的书写系统,而亚述文字又来自巴比伦。巴比伦最近的外国邻居埃兰在很早的时候就像后来的赫梯人一样,摒弃了他们粗鄙的象形文字和老旧的巴比伦字符,后来根据这一书写系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字符号。最后,我们发现到公元前6世纪时阿黑门尼德国王们创造出一套楔形文字符号表来表达古波斯语,以便他们讲的话能够出现在他们的巴比伦和苏萨行省的皇家公告和纪念碑上。
巴比伦语对异族的影响的这些例证仅限于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书写系统—但是其却有着广泛的内涵。因为当一种异国语言被使用和书写时,其文学中的某些知识必然成为预设假定。而且由于所有的早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宗教性质,所以对语言的研究必然伴随对其原来种族的传说、神话和宗教信仰的一定了解。因此,即使不考虑商业交流的明显作用,单是引用的例子也必然会对同时代的种族产生强烈的文化影响。
因此,这时可能会出现一种悖论,认为与巴比伦的名字相关的文明不是巴比伦人的。但事实是在这座城市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中心之前一千多年,由其传递出的文明便已经具备了所有其后期形态的要素了。实际上,就艺术上的卓越性而言,当时就已经达到了无法企及的高度,其标准从未被美索不达米亚的后世超越。虽然巴比伦人可能有更完备的立法制度,更多的文献,或许还有更烦琐的仪式和奢侈品,但其成就完全在早期模型的控制之下。如果排除诗歌和道德规范等,巴比伦人和其他地方的塞姆人一样,只能说是一个聪明的传承者,而不是创造者。他是苏美尔文化的倡导者,只是保持并吸收了其政治上所取代的种族的成就。因此,更为显著的是其个别城市本应有却很缓慢的文化演进。然而,在那些动荡的巴比伦只不过是一个省级城镇的数个世纪里,这种文化依然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城市里得以保留,漫长演进的结果在内部被慢慢吸收,并在后来的时代作为其所独具的文化原始来源呈现出来。在深入探寻其政治命运之前,不妨先简要了解一下其突然获得的地位得以保留的原因。
事实上,在其西塞姆诸王的统治下,巴比伦成为首都级别的城市其本身并不意味着地位永享。早期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历史中充满了类似的例子,城市突然崛起,接下来经过权力巅峰,又归于沉寂。政治重心不断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然而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旦落在巴比伦之后,便继续停留在那里。对于西方塞姆人来说,在3个世纪的政治存在之后,他们的城市似乎必将面临与其众多先辈一样的命运。
当赫梯袭击者洗劫了巴比伦并带走其守护神时,历史似乎注定要重演。假以时日,国家凭借其丰饶的物产从暂时的低谷中得以恢复,可能期待着在其他城市的支持下如前朝般再次争锋。然而,在巴比伦的古墙内建立大本营的却是加喜特征服者;埃及18王朝的法老和卡帕多西亚的赫梯王们纷纷向长期重建后再次强大的巴比伦寄来外交信函。在亚述与南方王国的长期斗争期间,巴比伦一直是主要角色,阿拉美亚人或迦勒底人部落的突袭从来都没有成功取代其地位。在亚述的权力巅峰时代,巴比伦依旧是其帝国扩张过程中的主要监控对象,而萨尔贡王朝对待这座城市时摇摆不定的政策充分证明了其在政治上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当尼尼微堕落时,正是巴比伦攫取了其在西亚的大部分地区。
这种单个城市的持续优势与早期都城的短暂权威形成了鲜明对比,只能说其国家普遍状况可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一个事实是极为明显的:巴比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必定赋予了其在这一时期战略和商业的重要性,从而能够在对其物质繁荣的破坏性冲击中生存下来。稍看一眼地图就知道该城市在巴比伦尼亚北部,正好位于下游两条大河汇合处的下方。最初该城建于幼发拉底河的左岸,河水可以保护其不受到沙漠部落突然袭击。与此同时,她与东南部广阔的运河交错的冲积平原直接相连。
但其位置的真正优势在于靠近陆上交通线。当从北方接近巴格达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收缩至大约35英里的宽度,虽然到巴比伦的纬度时横向再次扩张,但该城恰在两条河流的触及范围内。因此,该城处于两条商业要道的交汇点。幼发拉底河一线将巴比伦尼亚与北叙利亚和地中海联系起来,同时也是其与埃及的天然连接线;这一线还从西里西亚山口通过陶鲁斯山脉,沿着后来的皇家大道的轨迹与卡帕多西亚相接。自西通过安纳托利亚的主干道进一步向北,从黑海的各支线汇合,在上哈利斯河的锡瓦斯转向,越过群山中的幼发拉底河后,先在迪亚尔贝克(Diarbekr)抵达底格里斯河;然后离开底格里斯河进入平原,在尼尼微附近再次到达河边,然后再向南前往苏萨或巴比伦。巴比伦控制的第三条重要路线是向东通过扎格罗斯山口,这是穿越伊朗高原最容易的地方,也是北部埃兰的自然商业出口。因此,巴比伦位于国家间的交通枢纽,扼守入侵南部平原的必经之路。
巴比伦的重要性在于其战略位置,而不是其居民的任何特殊美德。这一点在后来的国家历史进程中显而易见。有人的确已经指出,地理条件注定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交汇处附近必然出现一个伟大的城市文明中心。巴比伦霸权时代过后都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些都城的相对位置都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都聚集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狭窄部分,而只是在很短的一段非常规时期统治中心被转移到南部城市。万变不离其宗,新都位置的选择总是在底格里斯河的旁边,有一
个明确的趋势是向左岸或东岸迁移。幼发拉底河应该以这种方式为其姊妹河让位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后者拥有更深的沟渠和更好的水道,而且一旦考虑到海上交流的可能性其意义就更加重要了。
在巴比伦称霸的整个时期,波斯湾与一些山脉一样是国际交通的一个巨大的障碍,远远谈不上国际商业通道。但一定数量的地方海岸交通无疑总还是存在的。早期的阿卡德国王那腊姆辛(Narâm-Sin)以及稍晚时期拉旮什的古迪亚(Gudea)从马干带到巴比伦尼亚的沉重的闪长岩石块,肯定通过水路而不是陆路运来的。传统也将征服迪勒蒙岛(Dilmun,今巴林)归于阿卡德的萨尔贡;但这已经是巴比伦向南渗透的极限了,这一场所谓征服必然仅仅是对阿拉伯海岸的一系列袭击之后的临时占领。事实上,两千年后,亚述的萨尔贡记录了他收到迪勒蒙王乌培瑞(Upêri)的礼物单时,估计到离巴比伦的海岸线的距离遥远,这表明那时波斯湾水路依然不被作为一种交通手段。基于此假设,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辛那赫瑞布(Sennacherib)在渡过海湾对阵埃兰的某些海岸城镇时遇到的困难以及为此建造特殊船只的必要性。
有证据表明,在新巴比伦时期,海湾运输的可能性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据说尼布甲尼撒II曾试图在三角洲口岸的沼泽地带建造港口,1但其动机必然仅限于鼓励沿海贸易。波斯湾和印度之间的海路极有可能是从亚历山大时期开始使用的,在5世纪之前肯定没有。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2希腊人卡利安达的西拉克斯(Scylax of Caryanda)从印度回来之后大流士开始开放海路进行考察探险行动,并以此为基础对其新领地进行评估。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必要怀疑这次航行的历史特性,可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西拉克斯曾在海岸迂回或甚进入过波斯湾。3此外,在波斯帝国的有效组织下巴比伦的国际贸易获得了极大的推动,但受益很明显的是陆上路线。底格里斯河上妨碍吃水更深船只通行的突出岩石或障碍物直到亚历山大才被移除。此时巴比伦海上交通首次成为一个显著问题,也是亚历山大在其生命中最后几个月致力于解决的。毫无疑问,这也是塞琉古选择底格里斯河作为其新都地点的因素之一。4
但这并不是巴比伦被废弃的唯一原因。在被居鲁士征服之后,新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促使其倾向于将都城向东部地区迁移。巴比伦的主要对手与宿敌在其历史早期就已经在她的东部边境一带活动。对早期的苏美尔城邦统治者来说,埃兰就曾经是“恐怖之山”。5接下来的时期,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城市永远无法知道一年中有哪个时期能够免于遭受侵袭。我们应该注意到,巴比伦的西塞姆人发现埃兰是其权威向南扩张的最主要障碍,而且在接下来的时期,只要出现内部虚弱或分歧的征兆便会遭到对方发动的新一轮攻击。的确有一段时间亚述人的威胁将这些宿敌凝聚到了一起,但即使阿舒尔巴尼帕(Ashur-bani-pal)洗劫了苏萨也没有停止他们之间的商业对抗。
在这些时间里,人们也曾试图将都城转移到强大的邻国不易于展开攻击的地方,向东需要获取外国控制下的通行许可,这样通往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幼发拉底河路线自然继续成为巴比伦商业的主要出路。但是,对波斯帝国的国内属地来说,所有阻碍东部贸易的危险都已不复存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巴比伦继续成为亚洲的首都,这证明其在过去历史上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居鲁士与亚历山大一样作为征服者进入了这座城市,却都被当作古代权利与特权的恢复者受到了民众和祭司们的欢迎。因此,试图进行激进创新的政策必将招致反对。除了夏季的几个月之外,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国王们都把巴比伦作为其行政官邸,这必将提升该城市所享有的声望以及其神庙和宫殿之宏伟壮丽。接下来早春的时候,他们搬到气候凉爽宜人的波斯波利斯或埃克巴塔纳,他们也可能搬到苏萨的王庭,但他们始终将巴比伦作为他们真正的首都。事实上,当统治中心转移到毗邻的塞琉西亚时,巴比伦才失去了其重要地位。商人们起初可能是迫于无奈,后来便是自愿跟随其统治者来到了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巴比伦便被削弱了。随着官方政策的导向,塞琉西亚继之迅速崛起。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对一座老城的影响力来说相对于新都位置的天然条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后来发生的事件进一步说明了巴比伦之所以伟大的秘密。泰西封在河的左岸崛起是东部地区商业趋势推动的结果。但它就在塞琉西亚的对岸,并不表明政治重心的新变化。该城原本在塞琉古王朝统治者的统治下无足轻重,到了安息王朝(Arsacidæ)时期却成为主要城市。当帕提亚帝国被阿尔达希尔I(Ardashir I)征服之后,继续作为该行省中的主要城市并成为萨珊王朝统治者的冬宫。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巴比伦城的废墟附近打败了波斯人,第二年又征服了泰西封。他们发现巴比伦和塞琉西亚的地理位置仍然像公元前3世纪时一样重要,将之统称为“马达因”城(Al-Madâin)。而接下来的125年时间与早期的巴比伦历史尤其具有比较意义。
阿拉伯半岛的塞姆人大规模移民,仔细考察一下历史就可以了解这一迁徙的过程和对被推翻的原有文明的影响。我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与巴比伦兴起之前的时代及其相似的综合经济环境。阿拉伯人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占领使得横贯大陆的商贸通道暂时关闭。此时国家的政治已经不再由萨珊王朝的都城统一控制,而是分成了几个区域。在阿拉伯军队的永久营地附近出现了一些新城镇。继征服美索不达米亚之后,最南端的莎特·埃勒-阿腊卜河(Shatt el-Arab)岸旁建立了巴士拉城。638年,库法在幼发拉底河的沙漠一侧的西北方被建立。65年后又增加了第三大城镇瓦西特(Wasiṭ)。这是出现在国家的中部位于底格里斯河两岸,其水域正沿着现在的莎特·埃勒-哈伊河(Shatt el-Hai)的河床流过。马达因
在地方的确依旧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在倭马亚哈里发期间,库法和巴士拉是伊拉克的双都。6
因此,国际联系的废弛立刻导致了巴比伦北部和南部地区之间的权力分散。两个首都的确都在同一政权控制下,但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想到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城邦时代。同样也没有外部因素来保持北方的重心。以力城(Erech)曾多次获得了霸权,而最稳定的是后来南端的乌尔城。我们应该注意到,巴比伦作为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唯一和永久的都城,其崛起可以追溯到西塞姆王朝建立后与叙利亚北部越来越密切的关系。7当阿拉伯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时统治中心转移到了巴格达。此时我们可能会看到历史重演。倭马亚王朝的垮台以及阿拔斯王朝首都从大马士革东迁,使得与叙利亚和西部的商业交往恢复了原有的基础。巴士拉和库法立即失去了应对变化的条件,一个新的行政中心呼之欲出。重要的是巴格达本应建在泰西封以北几英里的旧都圈内,8而且除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外,9该城应该一直是伊拉克的首都。因此,在哈里发统治下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对于研究与之类似的使得巴比伦在早前获得并保持巴比伦尼亚霸权的历史条件有很大启发。
从以上对历史事件的简要考察中可以看出,巴比伦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其国家历史的中期开始衰落。在此期间,这一原本传承自其他族群的文明又被传播出去。随着她时代的终结,她所传递的文化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上渐渐褪色。但是,她为我们传递的信息在其他族群保留至今的古代遗存之中留下了印记。我们应当注意到,其影响力明显超出国土的范围主要分三个阶段。这些对外联系阶段中最早的是其西塞姆统治者治下的第一王朝,但其影响的最明显证据通常要过几个世纪才显现出来。第二个阶段是一个间接的过程,其文化因亚述的扩张而被带到了北方和西方。最后一个阶段适逢新巴比伦国王统治时期,得益于其自然资源,不仅国家恢复了独立,而且在短时间内建立了一个远远超过其早期疆域的帝国。虽然在波斯治下巴比伦迅速回归到了行省地位,其外国影响力的确也每况愈下,但到了希腊时期这种影响力依然存在。
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巴比伦文明的某些特征及其对其他种族文化发展影响的程度。关于后者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对待其国家历史任何方面都不容忽视的主张。最近对亚述学研究做出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贡献无疑涉及思想的影响。早前的研究显示这些影响是源自巴比伦的。近年来,德国出现的一个学派强调巴比伦在西亚宗教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影响欧洲宗教发展的程度较小。以色列和希腊主要提供了巴比伦思想在整个古代世界传播的可靠依据。据称,希伯来宗教和希腊神话中的许多特征只能被解释为是受到了巴比伦风格的影响,追根溯源来自巴比伦。因此,有必要对支撑有关此主题的近期推测的理论进行简要讨论,并尽可能确定其可信程度从而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判断结论。
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该理论,必须使之依托于坚实的历史基础之上;反之亦然,对其可信度的质疑也都应该经过其国家历史的本身的检验。在详细确定了与其他种族实际接触的证据之后,才有可能对仅靠权衡可能性来解决的问题形成更自信的判断。因此,巴比伦对外影响的评估被放到本卷的最后一章。但在研究其朝代的历史顺序及其可能被归入的时期之前,最好先搞清这个曾经的巴比伦尼亚的永久之都的实际遗址上最新的考古发掘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