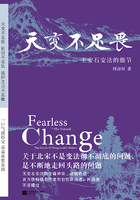
第5章 最初的试探
变法的序幕已经拉开,可是像北宋这样的大国,国事千头万绪,哪里都是问题,说要改变,要从哪里改?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最容易见效也最稳妥的突破点?
这是一个历代史书里都忽视了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王安石从均输法开始着手,与北宋的国情有关,与官场的安稳有关,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
说官场,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份之前,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意见,司马光说的是节约,必须节约才能有钱。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生活的官员们受罪。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加官场,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钱,会由他超凡脱俗、充满魔力的脑子里变出来。这是多么诱人啊,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
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的,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十倍地翻番增长。可郁闷的是,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均输法出台。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地避开了敏感的涉及立国根基的农业问题。
均输法很简单,它关系到开封百余万居民的生活。我们都知道,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农村的供给。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地供养它,才能把它养胖,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开封城也是这样,为了繁荣它,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名叫发运司。由发运司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运,把南方的柴、米、茶、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可是时间长了,就显出了它的弊端——权力不足。
真实地再现了大量的物资通过汴河运入汴梁的场景。
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运送某些东西,而决定运什么,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好,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很多时候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浪费吧,别急,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这种鸡毛蒜皮的事?
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具体做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利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其间朝廷要花钱,同时也要考虑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运费也要算进去。运回京城之后,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市民出售。大家看清楚了吗?等于朝廷开了个采买大公司。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也让宋王朝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
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没动官员们、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个目标。王安石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叫薛向。他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后,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五百万贯内藏钱、三百万石上供米为启动资金,把这个“采买公司”办得风生水起。
事办了,钱赚了,王安石仍免不了被朝堂上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荡得很有水平。熙宁二年,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十八年之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只有对王安石的责骂,王安石是小人,无事生非,残害百姓,像桑弘羊、商鞅那样赚钱,违背孔孟圣人之道。均输法到底有什么问题,一句没提。空洞无物,态度恶劣,他被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职务不大,可必须得认真应付,因为他是苏轼。苏轼已经名动天下,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这绝对不能小看,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文坛地位高了,足以让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苏轼的话真正说到点子上了,他明白其中奥义。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脱节了,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繁华呢?那就是商业的作用。宋朝商业非官方发起,它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国库的旁边流走,朝廷沾不到半毛钱关系。
苏轼说:“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均输法虽没明说是官办公司,可采买,必然会出售,一定会和商人们争利。苏轼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张。均输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商人们不敢动,不就证明了新法的成功吗。有人要说,这不是搞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已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活生生地扼杀了。
北宋之汴梁市井繁华,商铺林立,表面上为私人所开,非官办,实际上各种大买卖的背后老板都是朝廷官员。
对,这种说法也对。只是自由竞争、垄断主义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额的现代商业税。在宋朝时,不管商业怎样发达,都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比较的结果,在主体上它仍然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它的产出相符合吗?
更何况里面还有“猫腻”,大商人上多少税,怎样上税,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参考一下后来为什么在名义上与商业半点都不沾边的大臣,深宫后院里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们,也都为大商人说话,内幕就太简单了吧。
不收钱,谁干活儿?
说到底一句话,王安石是发现朝廷的问题,解决问题;而这些大商人和他们背后的同伙们,是发现了朝廷的问题,享受、利用这些问题。
苏轼之后,又有苏辙、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地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
对此神宗没什么好脸色,当着朝廷的官员,拿着赵家发的俸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地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里,还只是些小打小闹。新法实行之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大佬们还都没表态。也许他们在观望,也许他们在思考,设身处地地想,当时,处于均输法刚出台的一两个月时间内,没有谁会未卜先知地知道后来这些人的态度。
另一边,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人物,他们应该做的就是稳住脚步,借着打压反对派的势头,把均输法推广到全国。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到国库充足的状况,最重要的是,要给人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僵化平稳了一百多年的脑子能渐渐地适应改变。
王安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奏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变法的事,缓变会有利,急做害处多,大家要集思广益,慢慢地来。变法派内部也是这样做的,新法的第二条法令关系重大,它涉及国家之本农业。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个处理不当,就会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甚至改朝换代。”
有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农业垮了,百姓们吃不上饭才铤而走险,当了暴民。